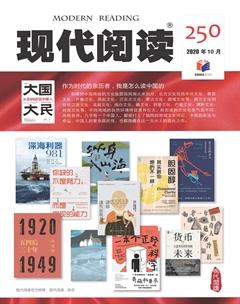关于书的挽歌
2020-11-16刘剑梅
刘剑梅
历史上有许多小說都把“书”当作故事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有一类小说特地让小说人物展示他们所读过的书,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知识和思想构筑了他们的心灵图景,比如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都很喜欢读书,比如索尔·贝娄的小说人物经常旁征博引,在各种哲学和文学经典中自由出入;还有一类小说则把写书当作小说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种小说,纯粹把“书”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来书写,比如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
赫拉巴尔是捷克的一位重量级作家,连昆德拉都很佩服他。赫拉巴尔自己是法学博士,可是却不喜欢法学,反而干了许多跟法学完全无关的工作,比如仓库管理员、列车调度员、保险公司职员、废纸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等,还曾经自愿报名到克拉德诺的钢铁厂参加两年的义务劳动。虽然自己是知识分子,可是他热爱底层人民,喜欢听他们的故事,欣赏他们的粗犷之美,认为他们的语言“就像是上帝的恩赐,现实的粗鲁和狂野之风直接冲我吹来”。他的大部分小说作品,如《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严密监视的列车》都深深地扎根在坚实沉重的生活中,并且加入幽默、调侃、揶揄的语调,结合了沸腾的生活气息和睿智的反讽。不过,他最打动我的一本小说,是他酝酿了将近20年的时间书写和反复修改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这真是一本可以传世之作,他自己甚至说:“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写它推迟了我的死亡。”这部小说并不长,但是非常有力量,用的并不是底层人民粗犷的语言,而是优美的书面语,完美地结合了抒情和叙述、思想和寓言,不仅是一部绵绵不断的“忧伤的叙事曲”,更是一部超越时代的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小说。
《过于喧嚣的孤独》其实是一部关于“书”和“书的命运”的小说,也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部关于文字、阅读和思考的小说,更是一部超越国界、涉及整个人类的人文精神衰败的小说。小说的通篇都是废品回收站打包工汉嘉的独白,是他自己讲述的对“书”的爱情故事。35年来,汉嘉的职业就是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但是在处理这些垃圾——“书”的过程中,他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无意中吸收了大量丰富的学识和思想,这些知识和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他的血液,渗透进他的大脑和心灵。作为废品回收站的打包工,汉嘉一边毁灭书一边吸收书中的精华——这一充满悖论的形象本身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隐喻。它暗指书对于人类的意义:是像垃圾一样,终将被人类所遗弃和淘汰?还是拥有神奇的力量,把人们从如同垃圾一样混乱不堪的现实中提升到美好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推开永恒的一扇门?一方面,汉嘉是“书”的屠夫,在到处爬满小耗子的肮脏的废品收购站里,亲手破坏人类的典籍,他开动机器去碾轧那些美丽的图书时,“我仿佛听到了人骨被碾碎的声音,古典名著在机器中被轧碎恰似头颅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样,我仿佛在轧碎犹太教法典中的词句: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另一方面,他日复一日地做这一工作时,每天都在读书,比如他读康德的《天国论》时,“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无边无涯,极为丰富,无尽的美从四面八方向我喷溅”。于是,书中的思想不知不觉地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美好起来,思想扑扇着翅膀在他的周围飞翔,如同灯油一样点亮他心中的那盏灯。
扎根于生活的赫拉巴尔,在废品回收站的打包工汉嘉身上看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书让汉嘉有了“心”,让他即使在臭味难闻的垃圾站工作,对希腊的美的观念一样会产生强烈的渴望,让他的头脑中“流动着生机勃勃的、活跃的、孕育着生命活力的思想”,让他生活在梦境中,生活在美丽的世界,生活在追求真理的思想花园里。汉嘉一边把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席勒的《唐·卡洛斯》、尼采的《看那个人!》像血淋淋的肉一样打包,做着“屠夫”一般的机械性的工作,一边思索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思索着耶稣和老子所代表的不同精神。赫拉巴尔在比较耶稣和老子时,用的是非常具象和生动的语言来表述深邃的思想,以轻驭重,包含着作者多年来的感悟,写得实在漂亮极了,短短的几段话就形象地概述出耶稣和老子的思想精华。汉嘉在苍蝇乱飞的恶劣条件下,按动着压力机的电钮,他似乎看到压力机旁站着一位举止优雅的年轻人,那是耶稣,随即又站了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那是老子:
我看见耶稣在不停地登山,而老子却早已高高站在山顶,我看见那位年轻人神情激动,一心想改变世界,而老先生却与世无争地环顾四境,以归真返璞勾勒他的永恒之道。我看见耶稣如何通过祈祷使现实出现奇迹,而老子则循着大道摸索自然法则,以达到博学的不知。
我看见耶稣信心十足地命令一座高山后退,那山便往后移动,老子却用一张网覆盖了我的地下室,是一张用难以捉摸的才智织成的网。我看见耶稣有如一个乐观的螺旋体,老子则是个没有口子的圆圈儿,耶稣置身在充满了冲突的戏剧性的处境中,老子则在安静的沉思中思考着无法解决的道德矛盾。
我看见耶稣像一个刚在温布尔登网球赛中取胜的冠军……老子则身穿布衣站在那里指着一块未经雕琢的粗木料。我看到耶稣是个花花公子,老子则是个腺体不全的老光棍。我看到耶稣举起一条手臂,以唯我是从的强有力的手势诅咒他的敌人,老子却逆来顺受地垂下双臂,仿佛垂着一双折断的翅膀。我看到耶稣是个浪漫主义者,老子则是古典主义的,耶稣有如涨潮,老子却似退潮,耶稣像春天,老子则是寒冬,耶稣体现的精神是爱邻居,老子则是空灵的最高境界,耶稣是朝着未来前进,老子则是退到本源……
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回收站,汉嘉一边轧碾着满载各种人类思想的书籍,一边思考着耶稣的前进的时间观,以及老子的向后看的返回本源的时间观,他梦想着让这两种观念结合,这何尝又不是赫拉巴尔的人生哲学观呢?他徘徊在进步和向后看的两种人生姿态之间,徘徊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在拯救和逍遥之间,内心充满了感伤和悲剧感,不停地思考着人类的出路等形而上的问题。即便汉嘉读了这么多的书,他并没有变成一个书呆子,而是常常感悟,把知识跟生命结合在一起;即便他常常重复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却懂得仁慈,懂得人要有善良慈悲的心,他为被盖世太保带走的茨冈小女孩感到悲伤,因为他知道比天道更可贵的是同情和爱,比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的理性要求更重要的是出自内心的同情和爱。也就是说,他无论读了多少书,都知道潜藏在书本之下最珍贵的东西,还是一颗心——那熠熠发光的人文精神是一颗仁慈的心。
汉嘉成天在苍蝇成堆、耗子成群、恶臭熏天的废品回收站工作,书像潺潺流进他身体中的清水,洗涤包围着他的尘世的污浊,净化他,养育他,所以他对书充满了感情。
在我心里有一盏小小的羯摩灯,瓦斯冷却器中的小火苗,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地从书籍中,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的书籍中读到的思想。因此,我走回家去有如一座燃烧的房子,有如燃烧的马厩,生命之光从火焰中升起,火焰又从木头的死亡中产生,含有敌意的悲痛藏在灰烬的下面。
汉嘉享受抚摸纸张的乐趣,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等的书籍漫游古希腊,漫游世界。他从没有度过假,却对人类世界有着充满智慧的清醒的认识,这一切都得益于他天天工作之余的阅读,正如老子所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然而,天道终究还是不仁慈的。可悲的是,科技的进步,巨型压力机的出现,把汉嘉的这点微小的快乐完全摧毁了。社会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小压力机很快就要被巨型的压力机所取代了,像汉嘉这样传统的打包工,还能在废书、废纸堆里无意中获得学识和思想,还会生活在西西弗斯情结中,体会生存的荒谬感,懂得停下脚步阅读,还能在阅读中感到幸福,在阅读中反观自己,提升自我,思考生命的意义,而操纵着巨型压力机的青年突击队员们,则如同机器人一般,虽然拥有强壮的身体,可是对自己要碾轧的书没有“情”,没有“心”,他们对一本书的产生和制作的复杂过程一无所知,不知道一本书要经过作者多久的酝酿思考才能写就,不知道一本书还要有多少人编辑、校订、插图、排字、看校样、改排、再看校样、再改排、印刷、装订、阅读、批评等,每一个程序都要人们倾注许多心血、时间和生命,他们对此没有亲身感受,所以面对将要被毁的书籍若无其事,无动于衷。那巨大的压力机,代表着新的时代、新的世界的来临,就像是后工业时代的象征,是不可阻挡的科技进步的象征,而那些操縱巨大机器的工人,对书极其“冷漠”“无情”“无心”,完全成了异化的人。
汉嘉看到那巨大的压力机——历史进步的车轮,滚滚向前,让人变得冷酷无情,对待书就像对待传送带上将要被宰割的鸡和鸭,撕开书本如同撕裂鸡和鸭的内脏一样野蛮,无视每本书的生命,无视艺术,无视美。天道不仁,汉嘉实在看不下去了。最后,他选择倒在自己的压力机里,跟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的书,一起被碾碎,像塞内加一样,像苏格拉底一样,从容对待死亡。他说:“我仿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他选择跟这些书同样的命运,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向新世界告别。汉嘉最后异常决绝地自杀,如同一件行为艺术,是一种“反潮流”的行为艺术姿态,对即将丧失人文精神的新时代不再留恋,对不珍视书的将来不再盼望。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我读过的对“书”抒发情感的最美的一个爱情故事,是一首优美而悲伤的叙事曲。赫拉巴尔喜欢在悖论中探求难以把握的真理:美与丑、高贵与低贱、新与旧、进步与保守、光明与黑暗、喧嚣与孤独、幸福与悲伤、耶稣和老子、思想的天堂和生活的地狱,全都并置在这本小说里,充满张力,既有抒情之美,又有思想之美。最可贵的是,虽然整部小说都是关于书和关于思考的故事,作者用卑微而高贵的心带着我们浏览从古至今的书籍中那些打动汉嘉的哲理和思想,但是作为读者的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干涩,反而能够感受到思想的灵动,感受到赫拉巴尔笔下“有情的思想”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
这部小说是对“书”的留恋与告别,对整个人类不可阻挡地走向“单面人”的工具理性统治的新时代的抗议。《过于喧嚣的孤独》完稿于1976年,由捷克官方出版社“Odeon”(奥迪欧)于1986年出版,然而,赫拉巴尔所表达的对整个新时代将丢失书、丢失人文精神、丢失情、丢失心的预言和警告,到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已然成为现实。汉嘉使用压力机的时代,还有空隙和缓冲的余地,他还能在工作之余阅读,还能在把“书”压成包之前,抚摸着书的温度,咀嚼和回味着书中的思想,与书依依不舍地告别,他还没有沦落成压力机的奴隶,还是有情之人。可是我们的时代,还有多少人对书仍旧怀有这样一份深刻厚重的感情?有多少人已经“被物所役”、爱手机远远超过爱书籍?老子所讲的返回本源,庄子所批评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其实珍视的都是不被外界所污染和奴役的心灵和本然本真的存在,这也是汉嘉读了这么多书后,得到的最高贵的领悟。他最后告别世界的姿态,就是选择了老子式的返回本源。
人们把劳心者、知识人等称作读书人。无论如何,书本确实跟精神紧密相连,或者说,书就是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一种产物。即使金钱世界或专制机构把它扔进垃圾堆,它与人类仍然息息相关。人类,除了本能地需要灌满胃肠,还本能地要求头脑思索、心肺灵动,也就是本能地需要书本。这恐怕正是写作者和读书人让书本变得有血有肉的缘故吧。书本是任何权力机器都无法碾碎的,再强大的机器也是徒劳——它们可以碾碎书的外壳和纸页,但是碾不碎书本中包含的充满智慧的思想和精神。
书,在“爱书人”汉嘉的手中,是有形、有情、有心的,在他的抚摸中不仅有温暖的体温,而且会散发思想的火花和灵魂的芬芳;书终会发黄,人终会逝去,但是书中的思想和精神是永恒的,永远都不会枯萎,不会变色。
2019年8月于香港清水湾
(摘自天地出版社《小说的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