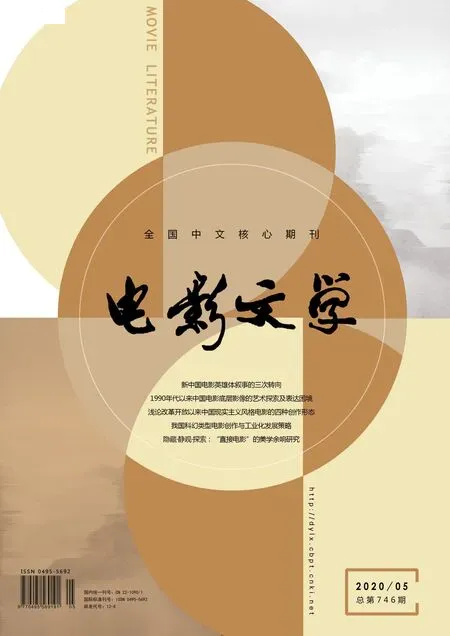《天上再见》:文学与电影的限阈
2020-11-14陈彧
陈 彧
(湖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文学和电影由于其自身独有的魅力而拥有大量的受众。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它们都生产了具有商品化色彩的作品,以应对市场需求以及大众口味。正因如此,在众多艺术门类当中,文学和电影成为两种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接受度的艺术形式。与此相应,由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在不断出现。在商品化浪潮下,改编之作经常展现出不俗的号召力,因为其受众不仅包括喜爱观影的“影迷”,也涵盖喜好原著小说的“书粉”。所以,无论是“改编剧”还是“改编电影”,在当今时代都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对这种现象在文学和影视理论层面进行独特的观照也显得颇为必要。
电影《天上再见》是文学改编电影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因为无论是改编电影,还是其原著小说,都可谓享有盛誉。原著小说由皮耶尔·勒梅特(Pierre Lemaitre)创作,作品曾于2013年荣获法国文学的至高荣誉——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电影由阿尔贝·杜邦泰尔(Albert Dupontel)改编并自导自演,影片在第43届法国凯撒电影奖(César Awards)中荣获包括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服装和最佳艺术指导在内的五项荣誉。在这部影片中,不少文学改编类电影的特点和症候都有所体现。本文以这一经典文本为个案,通过对原著小说和改编电影的对比研究,揭示和探寻文学与电影之间的限阈,以及两者在何种限度上能够实现有益的沟通。
一、虚实之间:可读性与可视性
文学和电影之间首要的界限,是两者艺术媒介的不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通过语言文字塑造形象。电影则是由视听语言构成的影像艺术。由于这种区别,两种艺术形式在接受上存在着天然的限阈:文学是可读的,而电影是可视的。文学中当然也隐含有“形象性”,但这种形象是通过接受者的阅读和想象内在地实现和完成的。电影则始终不会离开影像,否则将无所呈现。“可读性”与“可视性”的区别,既是由于两种艺术在媒介和语言层面的不同而造成的,同时也意味着它们在接受方面隐含着天然差异。
在电影《天上再见》中,可以看到导演的转化工作在三个方面较为显著。这些努力既是对差异的有限弥合,也是对限阈之存在的确证。
首先,对小说整体基调的“影像化”视听创造。电影《天上再见》对原著小说的主要情节进行提取,并进行影像化的呈现。在此过程中,影片对影像的总体色调进行了一种特殊的处理,以凸显和配合一战的时代背景,并增添了电影艺术所独有的影像风格与质感。小说《天上再见》的开篇,是篇幅很长的大段战争环境描写。影片则创造了一个流畅的长镜头影像对其进行表现。在镜头的推进和跟随下,一条绑着信件的狗在破败的荒地中前进,其间经过的荒凉景象暗示着战争的艰巨和残酷。狗最终来到了主角部队所在的低地,在不断穿过两侧的士兵后,停在了一个士兵跟前,士兵取走信件。整个镜头一镜到底而无间断,在交代故事背景和奠定影像基调的同时,自然地引出故事主角和其后发生的故事。这是从小说“可读性”到影像“可视性”的一个成功创造。
其次,对小说描绘的大量面具、纪念册里画作的“具象化”美术创作。在小说《天上再见》中,描绘了爱德华佩戴的大量面具,这些描绘有的细致入微,有的相对简略。对于爱德华的画作,无论是战争时期的手稿,还是战后的纪念册,在小说中都有相应的具体描写。这些美术书写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电影则“化虚为实”,使这些文字描绘变成可见的具象化实物。电影《天上再见》的美术十分杰出,影片中的面具和画作更是异彩纷呈。小说中具象描写生成的想象的精彩,被转化为电影中具象呈现的可见的惊喜。
最后,电影改编了小说中部分不宜影像化的内容。在《拉奥孔》中,莱辛发现文学中可读的那些情感充沛的描写,并不宜直接刻画在可视的雕塑上。对电影来说也是一样。在小说中合适的情节内容,到了电影里可能就显得不合时宜。在电影中,过于刺激的画面不宜频繁出现。所以,虽然小说《天上再见》里曾说:“和阿尔伯特在一起,他几乎就再也没有戴过面罩。”但是在电影中,并没有爱德华摘下面具的镜头,包括和阿尔伯特在一起的时候。这是由文学与电影两种媒介的差异所决定的。
二、节奏之辨:“章”与“幕”
除了可读与可视的基本差异,文学与电影在形式方面也有所不同。长篇小说通常从十几万字到几百万字不等,以“章”为基本分隔单位。电影通常为两个小时左右,以“三幕式”为经典结构范式,电视剧的体量有所扩展,但一般不过几十集。这其中隐含了文学与电影在形式和结构两方面的差异:其一,是内容体量上的差异;其二,是叙事节奏上的差异。对内容体量而言,文学改编电影一般都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删削和整合处理,以更加突出主线。这相对容易理解。但是由篇幅体裁的不同而导致的叙事节奏上的差异,却容易受到忽视。
在叙事节奏上,文学和电影在“章”与“幕”中的“节拍”是不同的。小说中的一些内容,在其整体的叙事节奏中是合理甚至必要的。但若照搬进电影,就有可能显得拖沓无聊。所以,针对两种艺术在形式方面的不同,电影《天上再见》在内容上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调整。
首先,是对情节的适度调整。梅林这一角色,在电影《天上再见》中的出场要比在原著小说中更晚。梅林是一个略显刻板的公务员,但正是由于他不随波逐流的性格和坚持正义的品质,使他不断追查反派人物普拉代勒的问题并与之无畏地斗争,才使得普拉代勒的罪行被揭发出来。在小说中,他从第29章开始登场。而在电影中,他的出场明显要更晚一些。这是为了使后面的剧情更加连贯,而对内容顺序所做的适度调整。电影中,类似这样对小说情节进行的微调还有很多。比如在小说中,阿尔伯特是在被路易斯找到后由她带到卢滕西亚酒店的,但在电影中,阿尔伯特则是看到了爱德华留下的字条后只身前往酒店。这种调整的依据,在于电影在内容体量上的限度和由此带来的叙事节奏上的差异。
其次,是对内容的必要删削。在小说《天上再见》中,普拉代勒曾在爱德华住院期间,对阿尔伯特进行威胁,这段情节在电影中被删掉了。因为在电影中,这段情节属于三幕结构中的第一幕,第一幕具有明确主角主要目标的作用,而目标的提出不宜太过推迟。在电影《天上再见》中,主角贯穿全片的明确目标是通过参加设计纪念册而报复大发战争财的人。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在影片第40分钟左右。如果第一幕中包含太多内容,目标的提出势必更加推迟。此外,在小说中,塞西尔是在电梯偶遇阿尔伯特的几天之后,才将戒指还给他。而在电影中,则是当时就还给了负责开电梯的阿尔伯特。不但如此,在小说中,这个戒指被阿尔伯特典当以换取金钱,而在电影中,则是在阿尔伯特回到爱德华的住处之后将其扔进垃圾桶,并引出随后的剧情。这样的删削处理,仍然是出于对文学和电影在内容体量和叙事节奏方面差异性的考量。
最后,是对叙事视角的变换。在电影《天上再见》中,阿尔伯特是一个贯穿全片的叙述者。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阿尔伯特在警察局中接受讯问的场景,这暗示了影片中的全部情节都是阿尔伯特对警察所做的交代,是在阿尔伯特视角下的主观叙述。而在原著小说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叙述角色。阿尔伯特这一叙事视角的意义,在于使小说中不在少数的人物形象和稍显分散的情节线索统摄在统一的视角之下,从而增强了影片的整体性。
三、内外之别:内在世界与影像空间
通过语言层和形式层,对文学和电影之间限阈的分析进入到更深的境界,涉及两者的艺术表现力及其所呈现的意蕴。对文学而言,小说天然具有心理描写的特长。在叙述语言的统摄之下,人物的动机、想法乃至潜在心理都能够经由语言的描绘直接加以呈现,部分小说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而得“心理小说”之名。这种心理刻画,伴随着环境的铺叙、情节的进展,甚至包括叙述者的评论,在整体的叙事“语流”之中最终综合化为一个完整的内在世界,弥漫着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意味和人生境界,而这正是文学所呈现的世界。
电影除旁白中的语言要素,主要是以影像来呈现意义和表现情感。如果说文学生成的世界是内在化的,那么电影则以创造视觉性的影像空间见长。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以不可视的媒介内在地营造一个可视的世界,电影则以可视的媒介抵达某种不可视的境界,这需要通过不断挖掘影像的潜力得以实现。小说《天上再见》中部分章节的内容呈现出某种文学意蕴的复杂性,在对其进行分析之后,探寻电影呈现复杂意蕴的影像可能。
(一)文学意蕴的复杂性
首先,是审美经验的复杂性。当阿尔伯特在电梯中看到塞西尔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时,他感到“除了被活埋在弹坑里,就从未有过这样漫长的时间,电梯里发生的事情就和弹坑里的情形惊人的相似,那种感觉难以言表”。战争中的活埋体验与战后生活中的无措感,都指向战争对人造成的一种内在相通的荒诞感受,深植于人类原初的基本生存体验。这样的类比及其意蕴,在文学的语言中被呈现出来。
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在小说《天上再见》中,爱德华的父亲佩里顾是一个复杂的形象,而这种复杂性在电影中被削弱了。在小说中,佩里顾展现出人性的多重侧面:“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知道佩里顾先生已经不太管他的生意了……和他擦肩而过的人都发现他老了很多……和以前相比,现在他更想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看爱德华的手稿时,小说写道:“左面那幅画里平躺着的死了的士兵以及那个向他投来的孤独胜利的眼神……佩里顾先生感到眼泪从心底涌了上来,他明白这些情感的出现是因为主角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现在,死亡的正是他自己。而胜利的那一方变成了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向自己的父亲投去了悲痛、忧愁、足以让你心碎的眼神。”在电影中,对这些侧面的呈现稍显不足。同时,在小说中,佩里顾始终未曾发觉爱德华的生存踪迹,直至意外地将他撞死之时。而电影中的处理,则更像是父子之间有意识的较量角逐。此外,小说中佩里顾撞死爱德华的结局,在电影中也被父子和解的场面所替代。在增添些许温情的同时,都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原著中对人类命运荒诞性的揭示。
(二)复杂意蕴的影像重构
文学作品中意蕴的复杂性,在电影中不能以等同的方式得到呈现,而需要对影像的深层潜力加以挖掘。比如,普拉代勒被埋入沙坑的场景,体现了电影在荒诞意味的呈现上所做的努力。在小说《天上再见》中,普拉代勒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在电影中,普拉代勒则是在和阿尔伯特的争辩过程中阴差阳错地掉入大坑而被沙土掩埋,场面诙谐而富有讽刺性。没有受到制裁和审判,暗示着像普拉代勒这样激进好战而又疯狂敛财的人,难以得到真正的制裁。在加大影片批判力度的同时,也为主题增添了荒诞意味。
卢滕西亚酒店的狂欢派对,是电影《天上再见》中重要且精彩的场景,实现了电影对文学中隐含的复杂性的影像重构。这一场景在原著小说中没有明确的对应部分,是电影的全新创造。随着阿尔伯特进入酒店大厅,出现巴黎的纨绔子弟们跳舞喝酒的热闹景象。大厅的上空到处飘着五颜六色的气球和彩纸彩带,男男女女跳着夸张乃至滑稽的舞步。灯光一暗,戴着审判面具的爱德华出现。在路易斯的主持下,一群挂着牌子戴着面具的“战犯”出现。在欢呼声中,人们用香槟将他们喷倒,还把蛋糕扣在他们的面具上,构成一场隐喻的审判仪式。这是一个电影而非文学的场景,狂欢之中隐含着孤独和反讽,以及法国整整一代青年的悲歌与挽歌。影像在此以自身的方式重构了文学对战争和人类处境及命运的复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