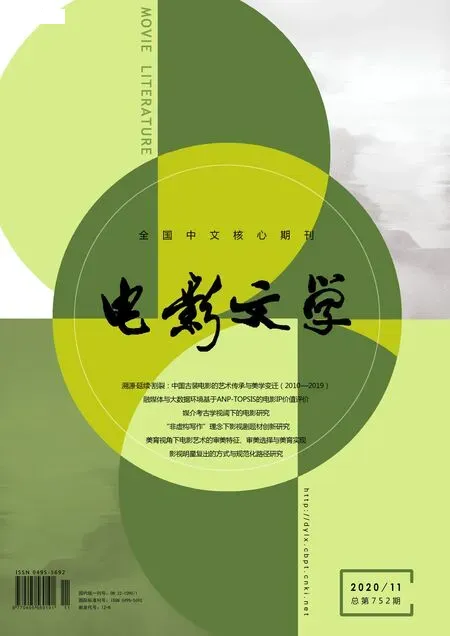《阳光普照》:台湾原生家庭生态的影像观照
2020-11-14高冬萌
高冬萌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2019年,由台湾资深导演钟孟宏指导的影片《阳光普照》获得了大众与媒体的热议,在台湾金马奖中接连斩获5项大奖,也是台湾电影近些年在书写本土原生家庭生态上比较具有深度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影片的英文名叫A
Sun
,是与A Son的同音互文,也是影片的叙事内核。“阳光”“儿子”的标题总是会提醒观者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影片,然而影片《阳光普照》却与这一直观印象完全背反,钟孟宏导演在接近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中呈现的是一个阴冷而现实的台湾原生家庭故事,影片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压力下,或是逃避,或是麻木。有的人本是阳光,最终却走进阴影永远躲藏;也有的人本是阴影,最终却迎来了阳光。影片借用阳光与阴影的隐喻,为几位角色赋予不同的人生属性,呈现出光影的强化对比,又以父与子的抵逆关系映射出当代社会的中国式家庭生存困境,而辩证修辞下善与恶的界限模糊呈现出伦理道德在社会复杂关系上的无力,透射出阴冷的现实主义观感。一、现实主义语境下阳光与阴影的影像对比
电影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存在于普遍的影片叙事上,然而在一些影片中,对比被置于一种特殊的位置,成为影片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借助对比在隐喻上与现实层面的多重潜在关联,不仅赋予了影片叙事深刻性的内涵,也为影片角色带来由表及里的特征强化。而其中隐喻性对比在影片中的作用亦可以作为其叙事内涵的暗示与指引,呈现出强化矛盾视觉关系的隐性作用,更是作为影片驱动叙事发展的动源。在电影中人物内心写照与行为动机的书写,往往不仅是直观性的镜头聚焦,隐喻的对比修辞潜在性的作用则更能透射出深度的复杂人性,成为影片深入解读的钥匙,在台湾导演钟孟宏指导的影片《阳光普照》中,对比的隐喻作用被强化,成为影片叙事的内驱力,使整个影片中暗含复杂的潜引指涉关系,“阳光与阴影”“希望与绝望”都与片中人物及情节推进具有极强的暗指,更使这种复杂关联背后蕴含着更加深刻的寓理。
透过电影《阳关普照》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是“阳光与阴影”的深刻寓指,在影片中凸显“阳光与阴影” 的三个孩子,“阳光”的哥哥阿豪是一家人的骄傲,是学校的优等生,是父亲阿文心中“唯一的儿子” ,父亲阿文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大儿子身上。阿豪身上呈现的是温暖与阳光,在这样一个善解人意、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的人身上,“阳光”几乎永远照耀着他,也正是因为无法承受难以躲避的阳光照耀,这个永远被“阳光普照”的孩子在不经意的一刻选择了永远地藏在阴影中再也不出来。阿豪的“阳光”凸显出与另外两个孩子阿和与菜头的强烈反差对比,对比之下的阿和与菜头则是台湾原生家庭中“阴影”的现实写照。 稍显不同的是,菜头这个人物自始至终是活在“阴影”之中,从缺少父母关爱,由奶奶独自抚养大所缺少的成长陪伴,到失足少年叛逆期为了帮兄弟阿和而犯罪,再到从少年辅育院出来走向歧途最终殒命,菜头的世界是完全没有“阳光”的。阿豪与菜头更像是阳光与阴影的两极,一个永远阳光,一个永远阴影。在二者之间,阿和成为既承载着“阴影”,又承载着“阳光”的中间部分,阿和与哥哥阿豪之间的背反是各自阴阳的反向,从生下来就“阳光”照耀下的哥哥阿豪最终躲进阴影,到从小不被重视走向歧途的弟弟阿和走向“阳光”。二者的互逆性最终转变为各自原质态的反面,而“阳光”与“阴影”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影片传达出在这对立的二元中,也有一部分是对立下的转变,而同时也透射出台湾原生家庭“中国式”伦理教育所产生的畸形心理。“阳光”是过度的关爱,“阴影”则是不被重视的心灵缺失,然而影片中“阳光”的哥哥阿豪最终承受不住,想躲起来,而待在少年辅育院的弟弟阿和却更渴望迎接“阳光”。这也形成了影片传达给观者的悖论,得到与得不到之间的困惑与挣扎。哥哥阿豪得到的关爱与优越的环境是弟弟阿和从小就缺失的,弟弟阿和无法得到的却是哥哥阿豪想逃避的,而反过来在阿和看来难以承受的“阴影”也是哥哥最想得到的。 “阳光与阴影”的寓指不仅体现在人物身上,也体现在影片叙事的推进上,片头部分菜头用开山刀砍掉了黑轮的手,阿和与菜头双双进入少年辅育院,影片用血淋淋的镜头将阴影笼罩在阿文一家。而“阳光”在阿和进入辅育院开始逐渐渗入,影片前半部分阿和逐渐反省,是从“阴影”中走出,而作为“阳光”指涉的哥哥阿豪却最终挺不住刺眼的阳光永堕黑暗。当阿豪离开之后,前半部分的“阳光”突然消失,菜头的出狱暗示着黑暗的阴影来临,已经走向“阳光”的阿和也即将被菜头的“阴影”笼罩,而这个“阴影”最终由父亲阿文彻底毁灭,阿和最终走向了“阳光”,换来的却是父亲阿文去承担更大的“阴影”。影片围绕着“阳光与阴影”的渐进渐出将叙事推向高潮,也在其中赋予了“光明与黑暗”更加深刻的体悟。台湾原生家庭之痛,痛在无法面对的现实,每个人都挣扎在“求而不得”的困境中无法自拔,写实的影像呈现出阴冷的多面人性,镜头下的平凡众生生活在不平凡的坎坷人生中。
二、“父与子”:观照植根于中国式家庭的伦理困局
当代电影中涉及家庭生态关系与伦理道德的影片比较多,普遍热衷于描述父辈与子女之间无法填平的隔代沟壑,从认知理念到行为举止再到伦理道德,家庭代沟往往是最深沉、最难以释怀的痛处,而当代电影中不只是本土电影,甚至在亚洲许多地区的影片中对此类题材亦颇多观照。台湾电影中涉及这种伦理困局的影片近些年也屡屡有佳作问世。在此类影片中,平凡家庭的世俗伦理往往能够唤起观者心中的共情,由于影片叙事是贴近于平民生活的底层,更容易使影片呈现出贴近真实生活的实际代入感,影片中的人物与生活也会成为自身的映照,从而获得触动内心的体悟。这类影片取材于真实的家庭故事,在生存生态的角度述说平实家庭的艰辛与不幸,艰难的挣扎与困惑下的无奈,以写实影像观照难解的家庭困局。其中,“父与子”的关系书写尤为呈现出植根于传统观念与父权延续的社会现状,父与子之间无交流、无沟通的“中国式”关系,成为当代社会普遍性的家庭写照。影片《阳光普照》的深刻,正是对这种台湾现实家庭生态的观照,而父与子之间产生的裂隙与矛盾,也成为影片中恶化的成因,最终一个家庭也由此走向破碎。
在影片《阳光普照》中,父子关系是相对泛化的,在华夏民族的传统家庭中是具有普遍性的,父亲阿文差别对待大儿子阿豪和小儿子阿和,优秀的大儿子阿豪成为父亲阿文心中的骄傲,于是阿文也把所有心思与爱都给了大儿子,而对比之下叛逆的小儿子阿和在其眼里变得微不足道,在他心中只承认一个儿子,就是优秀的大儿子阿豪,而差别对待引发的结果是与小儿子阿和的无沟通,父子相视漠然,也最终将完整的一个家庭彻底肢解。父亲阿文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期望是密不透气的,这也让大儿子阿豪无法承受,背负着希望,将所有阳光赠予他人的阿豪最终永远地逃避在阴影里。而小儿子阿和的沉默寡言与叛逆也是由父亲阿文一手造成的,阿文的漠视直接导致了小儿子阿和走向了哥哥阿豪的反面,最终因为怂恿伤人被送进少年辅育院,甚至当小儿子出狱回家二人见面后两人也毫无交流。父亲阿文与儿子阿和的关系冷漠,是当代普遍家庭父子关系的缩影,中国式的父权中心的俗成观念已然浸入血脉延续,成为父子关系难以支撑的情感裂隙,也最终走向无法预知的结局。影片中所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无法预知的态势,当大儿子阿豪跳楼自杀后,沉痛中的父亲阿文逐渐将目光转向了自己曾经漠视的小儿子阿和,因为现在他只剩下了一个儿子,可是曾经已经铸成的错最终已经演变成一个无法收拾的局面。被漠视的小儿子阿和虽然从“阴影”走向“阳光”,但阿和随时还会被“阴影”吞噬。菜头回来了,这是小儿子阿和无法摆脱的噩梦,也是父亲阿文亲手酿成的苦果,阿文的漠视与不管不问使叛逆的阿和曾经走向歧途,纵使现在改邪归正也依然无法逃脱曾经的“阴影”。菜头是小儿子阿和回归“阳光”生活最大的麻烦,也是基于此,影片开始向无法预知的方向延伸。父亲阿文为了拯救陷入“麻烦”的儿子阿和,毅然将菜头杀死,用自己的罪恶换给小儿子阿和“光明”的人生。而在这里,影片所呈现的伦理困局并未结束,父亲阿文最后为儿子杀了菜头,究竟是父爱的驱使还是为了彻底的解脱,影片最后用“阳光”收尾,然而却是用残忍换来的“阳光”。父亲阿文的“父爱”是模糊的,不可否认其中血浓于水的骨肉关系会驱使他这么做,然而一直以来的冷漠与忽视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式父子关系的普遍性痛感与困局最终体现在麻木地继续走下去,卑微平凡的原生家庭在救赎与解脱中疲于奔命。影片观照于植根中国式家庭纠缠不清的伦理关系,也为这一社会现状书写出扣人心弦的阴冷现实。
三、辩证修辞下模糊的善恶界限
“善与恶”是对立的两极,体现在电影的诸多题材中。家庭伦理影片中的善恶界限往往语义模糊,很难做出清楚的形式判定,这也体现了在家庭伦理影片中因为血缘与亲情骨肉的特殊关系而凸显出的复杂性,在此类影片中没有快意恩仇与惩恶扬善,更多的是因为亲情牵扯而呈现的错综矛盾体,为生存、为生活而能够麻木于“善恶”。在影片《阳光普照》中,“善与恶”是复杂矛盾的,体现在影片中各个人物的活动中,如影片中作为“恶”形象的菜头,在影片的片头部分,手拿开山刀去砍掉了黑轮的手。在这一点上他的“恶”无可厚非,然而矛盾的是祸源不是他,惹起事端的是阿和,他只是为了兄弟义气去出头,使他真正走向“恶”的是阿和将所有罪过推到他身上,换来的是五年的监禁劳教与家庭赔偿150万,而出狱后阿和已经忘了为他砍人的兄弟菜头,阿和的父亲更是甩手推开剩下的烂摊子,菜头为别人出头的结果是他成为牺牲品,这也使菜头产生了恨,最终走向了“恶”的深渊,荒唐的是最后结束他生命的竟是兄弟阿和的父亲阿文。菜头为兄弟阿和付出了砍人的代价,结果自己被以“恶”惩罚,而他的“好兄弟”阿和,走向“阳光”洗心革面却并未记得曾经为他砍人的兄弟菜头,不再认识菜头的行为尤显出阿和的冷血无情,菜头不再是保护伞而成为阿和心中的麻烦,是自己爬向“阳光”的绊脚石,殊不知,这不仅将菜头推向“恶”的深渊,也更将自己的家庭置入困境中,阿和奔向的“阳光”并不是正常的,在影片中自始至终阿和也未曾拉一把兄弟菜头,哪怕是劝他改邪归正,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和可怕的冷酷人性,而所谓的“阳光”是用无情抛弃与自私逃避换来的。再以父亲阿文亲手杀死菜头这件事来看,除掉麻烦的心理更大于所谓的“父爱如山”,是用更大的罪恶换取家庭“阳光”的生活。
近年来,台湾电影导演在发掘自身独特语境上立足本土人文,以现实镜语观照底层家庭的生存境遇,导演钟孟宏用现实的镜头光感叙述了一个阴冷的家庭故事,展现台湾原生家庭的生存状态与纠葛的亲情关系,也为观者提供了一个解读台湾民生的深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