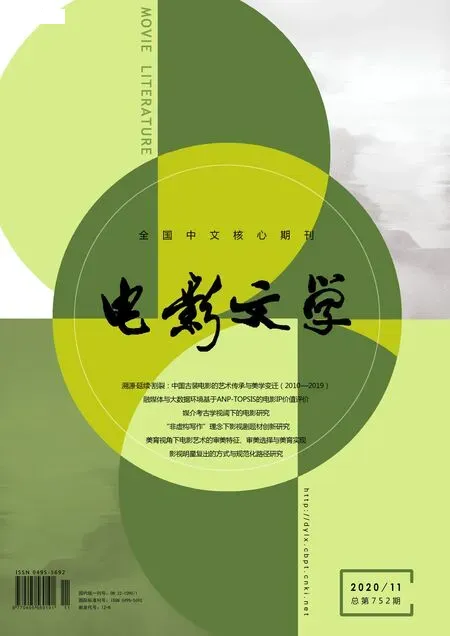现实·记忆·时间:纪录电影《零零后》的叙事研究
2020-11-14刘文卓庚钟银
刘文卓 庚钟银
(1.贺州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2.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一、从“直接电影”到“第一人称画外音”
纪录电影《零零后》是导演张同道在《小人国》的基础上,继续跟拍“零零后”这个群体并完成的一部力作。从2006年起,像很多“直接电影”的作品一样,《小人国》也选择了在机构日复一日地记录,花费了3年的时间去观察幼儿园里2~4岁的孩子。后来,他们当中的两位主人公早年的一些影像被当作历史素材运用到了《零零后》中,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处理。其中影片有两处,相隔十余年且极具“现场感”的事件都采取了相似镜头的转场技巧,这一切让观众感受到了时间跨度所带来的震撼:15岁那年,身穿中国队队服的池亦洋站在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场上高唱国歌,接着画面一下子切换到了10年前,5岁的池亦洋在幼儿园的国旗下与小朋友们一起唱国歌;另一幕,在武汉的橄榄球比赛场上,一个飞速映入视野的橄榄球突然变得缓慢,随后画面变成了5岁的池亦洋用手拦住了正在飞驰的足球,时光便穿梭到了池亦洋的幼儿园时光。这样的剪辑除了帮助影片完成时空的构建和连贯的转场,也体现出了在“直接电影”的工作方法下影像所获得的“现场感”——它总能亲历正在发生的事件。正如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中对电影时间的描述,电影的时间即时间的过程:过去好像从前的现在。因此,无论12年前池亦洋在幼儿园过去的“现在”还是高中时在橄榄球赛场的“现在”,都无法逃脱正在发生的“现在”,这都是“眼睛”的到场,留下了他成长的印记。
“直接电影”技巧下的拍摄,起初可能源于某种兴趣,通常是带有“非预设”性质的一种探索。面对媒体导演阐述自己创作的初衷时,总会提及早年与自己“零零后”孩子发生的一段故事,并且认为“很难给这一代人贴标签”,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这代人的想法和感受。出于对这个群体的好奇,导演开始了对他们的探索,并不断地回答起初内心的疑问。在作品《小人国》中,导演通过“直接电影”的工作方法给出了这个群体的画像,当然随着这种观察的深入,画像中的每个个体又逐渐展露出自己的个性。在长期的跟拍中,池亦洋和王思柔逐渐从众多孩子中“脱颖而出”。按导演的说法,由于影片并不是一部社会学家的作品,更在意有故事的个体,自然也不必像《人生七年》去覆盖不同的阶层。于是,影片的创作视角发生了转变——逐步放弃群体的画像而不断地漂移至个体的成长故事,与此同时电影的创作手法也有了相应调整,当然这种调整还可能与拍摄的环境变化有关系。相对于纪录片的其他创作方法,通常“直接电影”的技巧会与扎根于机构拍摄群体联系在一起,因此当幼儿园的“零零后”升入小学后,原有封闭且固定的拍摄场域被打破,“静壁苍蝇”也失去了观察的那面墙。
“因为他们分散了,去了北京的不同学校或是到外地去。再长大一点,他们可能就跨出国门了……第一年,我们确实是不分节假日全部在拍,拍了200多天。后来就是重点人物,重点事件,我们才集中拍摄。”
另外,这些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地觉醒。正如执行导演喻溟所认为的:纪录片必须考虑到拍摄的伦理问题,并不是每个时期孩子都同意拍摄,纪录片再重要也没有孩子的成长重要。另外,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拍摄关系也有过这样的描述:出于对自我隐私的保护,被拍摄对象往往排斥深度地跟拍;有时候导演越想接近那些吸引到他的人物,那些人却越不愿意把自我展现出来。在主人公漫长的成长岁月中,因遭到拍摄对象拒绝而造成事件的遗漏会时有发生,并对影像的表意造成不小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源于“直接电影”创作方法的某些特点,即擅长展示某一确定情境下发生的事件却拙于解释和概括事件的含义。随着“零零后”不断地长大,影片的创作方法上开始避免了“直接电影”技巧带来的长时间跟拍,并突出了“让·鲁什”的工作方式,即通过对人物的深度访谈去回顾他们的经历——可能是消逝的“现场”,这主要源于摄影机对某些事件的缺席。另外,电影还将人物的自述以一种隐藏在画外的方式作为人物的内心独白。于是电影逐渐从“直接电影”下的观察视角转向了“第一人称画外音”的人物视角。提及第一人称的纪录片,通常认为作者或者导演会“显身”作为讲述者参与到影片的叙事中去,比如电影《巴黎居民》(The
Inhabitants
of
Paris
),让·洛克(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不仅出现在了影片中,而且评论了电影本身,甚至包括他们的电影制作能力;迈克尔·特罗在影片《等待菲德尔》(Waiting
for
Fidel
)中有过相类似的评论。当然,《零零后》的导演并没有“显身”成为一个讲述者,而是通过“第一人称画外音”,让池亦洋和王思柔作为双主人公分别成为电影故事的讲述者,形成了主观化、内聚焦的人物视角;影片中通过“直接电影”创作的内容,则可视为客观化、外聚焦的群像视角。因此,在杂糅了不同类型的创作方法后,《零零后》呈现出了一种混合聚焦、多元化的叙事视角。二、记忆的“不稳定”与历史的现实
除了依靠主人公的口述去追忆过往的历史,《零零后》还尝试加入动画元素,通过“拟像”和“仿像”(鲍德里亚语)去视觉化人物的心理世界,并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描述了这种记忆。影片中女主人公回忆当年在“A+学习中心”学习数学时的种种感受,被导演制作成了一段类似于童话故事的动画片。影片中“拟像”的选择并非对真实事件的搬演,而是与类仿某种可能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有关,因此可以将这类叙事视为拒绝了包括“真实”在内的纪录片传统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然而这一切对于秉持“传统纪录片理念”的电影人来说,他们总会力图寻求证据去支持“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说法,比如可能会去王思柔所在的“A+学习中心”了解更多的事实。另外,影片通过“第一人称画外音”表现回忆时,还总会将一些“事实”与似乎是“幻觉”或类似于梦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影片中幼儿园时期的王思柔用稚嫩的声音朗读童话故事“她想,有一天我会多么小”,紧接着一个青年时期的女性画外音(内心独白)突然响起“当我遇到挫折以后,我会回到我的童话世界中,我会有无尽的想象”,但是画面仍旧停留在幼儿园的时空里,这是一组所指暧昧的画面并与王思柔在早期的个体活动有关:她独自一人坐在幼儿园教室的地板上,此时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打在她的身上。这种对历史模糊的回忆直到一段清晰的现实描述——王思柔出现在同学聚会上,才得以结束。而小学的池亦洋则被塑造成一个“学习困难户”的形象,影片中一个青年男性的画外音诉说着他对于小学的记忆:“我人生什么目标也没有,这个世界没有需要我的地方。”影片中个体在讲述记忆与历史对话时,总会表现出某种对“现实”的逃离、记忆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是一种更加超现实主义的表达。
不过,影片并不愿意放弃历史的现实。一方面,由于《小人国》是一部主要以“直接电影”技巧完成的电影,当它被穿插在《零零后》作为对照文本时,所表现出来的是历史记忆的稳固性。另一方面,影片在表现男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时,不能单纯依靠碎片化的片段作为“表征”“拟像”去完成个体的某种记忆,同样需要“直接电影”技巧去记录一些正在发生的“现场”,从而获得历史的现实。这种历史的现实往往与主人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接受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有关,因为电影需要借助这种现实去讨论教育的问题,拓展纪录片的教育功能。正如格里尔逊所描述的纪录电影的教化功能:“我把电影看作讲堂,用作宣传……一个简单的说法可以在一夜里被重复成千上万次,如果这种说法有说服力的话,就会传播给更多的人。”解说词和人物访谈都是极为高效的传播观点的方式,不过《零零后》并非如此急功近利,影片主要是以一种“非预设”的方式进行观点的表现。电影在主人公成长过程中采用“直接电影”技巧去捕捉教育话题所引发的讨论,并在探讨中让人物秉持的教育观点得到呈现。比如,大李老师在家长座谈会上阐述自己对“孩子王”池亦洋的教育观点;池亦洋的父母探讨了对孩子青春期早恋的看法;王思柔的父母因孩子学习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等。电影里的人物在表达观点时,没有反复地啰唆,因为导演总能在人物对话之间找到间隙作为剪辑点,将时空跨度较大的事件进行压缩,让观众既可以快速了解事件的发生,又能收获较为完整的教育观点。面对历史的现实,除了通过“直接电影”的技巧表达教育理念,影片也尝试对现实的素材进行创造性处理,并表现出先验性和戏剧化的美学特征。池亦洋的小学阶段:学校老师训斥“不像个男子汉”,家长不厌其烦地唠叨“每个老师都愿意你越来越好”,写不出作业的他委屈地哭诉“我什么也不会写了”;当几组镜头在加速蒙太奇和快旋律的音乐处理后,放大了池亦洋在小学教育下的无助和不快。而读小学的王思柔,则受到来自数学的困扰:在数学课堂上,老师不断启发和王思柔绞尽脑汁思考答案的画面被剪辑到一起。随着镜头越切越快,观众最后只能看到王思柔眨着迷惘的双眼和银幕不断浮现的一连串数字,这是一个极具“电影眼”(Kino-eye)的创作方法。
三、“逆流”的时间与“命运的自转”
从经典的时间观念出发,通常时间被认为只有单一的向度,即“从历史、现在到将来”,这种线性的时间叙事方式也被多数时间跨度较长的人物纪录片所采纳,如韩国的纪录电影《牛铃之声》、国内的纪录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都通过光阴的流逝去展示人物的变化,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直接时间的“绵延”(柏格森语)。不过,《零零后》并没有按照线性的方式去逐一展示主人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去体现人物心路历程,而是在两位主人公当下的“现实”时间和回忆的过去时间中来回穿梭,让影片经常表现为一种从现实向回追溯的电影时间。
《零零后》中,幼儿园就像一面镜子,主人公成长的每个重要阶段都会去孩童时期寻找某种相似性。2015年的武汉,身体健壮的池亦洋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橄榄球比赛,他期盼与对方球员对抗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不过影片在这里并没有展开池亦洋在比赛中的表现,而是通过相似转场,让时光回到了幼儿园的足球场。影片接下来重点呈现了池亦洋在球场上与大李老师的争吵以及后来他又踢哭了同学佳佳的事件,一连串的遭遇让池亦洋成为家长老师关注的焦点。这里插入《小人国》的素材似乎是在探究池亦洋幼儿园时期的“孩子王”性格,与他后来成为橄榄球运动员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关联。遭遇了种种的不快之后,一天中午,池亦洋独自一人躲到了园内的大土坑中。接下来的镜头延续了这种情绪和动作,不过画面是高中时期的池亦洋,此时他正因申请学校失败而感到烦恼。2016年,来美留学的王思柔担心自己难以融入新的生活,“我很怕被欺负,因为我从幼儿园时就被欺负”,这时一个稚嫩的声音闯了进来,“我没有,我没有骗人”,于是电影时间被拉回了王思柔幼儿园生活,可怜的柔柔正在面对集体对她的排斥。当电影再次回到王思柔的叙事线索上,她正在为自己无论怎样努力和优秀,仍然没有得到寄宿家庭的接纳而哭泣。此后,影片的时空又开始随着人物的意识不断地向过去流动。中学时期的池亦洋因为早恋的问题让他的父亲开始反思,“可能小时候我对他管得也少吧”,于是影片随即切到了2011年,展开了池亦洋失意的小学生活。读中学的王思柔因晚归和卫生问题不断遭到美国住家妈妈的否定,在挫折与迷茫面前,她的思绪开始向记忆探索,“我经常会想我12岁、11岁的时候”,于是影片开始展示王思柔与大多数孩子不一样的“私塾小学”经历。
《零零后》的电影时间,除了随着人物不断向过去找寻记忆,也有过去的记忆向前流动找到了主人公的现在时态。根据柏格森的倒锥平面图的理论,倒锥代表过去的记忆,平面代表现在时态。当回忆(或过去)经由圆锥体下降到与平面相交的那个点,便是晶体。影片中有一处“时间晶体”发生在王思柔回芭学园做义工的时候:王思柔碰到了一个不太合群的小朋友,“当我见到一个淘气的小孩子时候,我就想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不仅让王思柔看到了那个曾经在幼儿园被大家“排挤”的自己,也促使了她开始反思过去的自己。过去那个经常被群体孤立的柔柔就代表一种过去时态,而王思柔眼前这个难以合群的小朋友则是一种现在时态,当王思柔遇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刻,是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形成的一个时态上“不可辨别的点”。德勒兹在描述“时间晶体”时,认为“不可辨别的点”是一种双面影像,包括实际影像和潜在影像。具体到影片中,实际影像即芭学园里这个“另类”的小朋友在重复王思柔小时候走过的路,潜在影像即一种必然的过程——教育工作者面对“问题”儿童所必须做的付出,就像大李老师对王思柔所说的,“当年我就是这样(像你现在跟着这个小朋友一样)跟在你后面三个月”。这种循环反复,也就是德勒兹所描述的“命运的自转”。这种“自转”或者“轮回”根植于导演的创作理念中:导演希望可以继续拍摄“零零后”的这个群体,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看到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幼儿园,这个项目才算彻底完成。
纪录电影《零零后》作为2019年为数不多的审美型纪录片,通过探讨教育话题,拓展了纪录电影的表现版图,注入了新的形象。从《小人国》到《零零后》,历经十余年的打磨,作品在叙事技巧以及创作方法上的嬗变也体现了国内近二十年里纪实美学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正如导演黎小锋所提到,20世纪90年代末,怀斯曼给中国纪录片人补上了“直接电影”这一课,此后国内导演便将这种美学理念贯穿在实践中并产生了大量作品,《小人国》也正是那段时期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零零后》最终呈现出来多元、杂糅的创作理念和美学风格。这部电影也正像孙红云所描述的西方“新纪录”的那些作品一样,它们既不秉持一致的美学主张,也不坚持统一的创作方法,并且总在有意打破各种电影文体的壁垒,画外叙述、多元的叙事视角、动画特效、时空的错乱、素材的拼贴、梦境等“后现代”的美学样式都交织在一起,这一切都在《零零后》中有迹可寻。除了对国产纪录电影美学上的贡献,《零零后》还不忘拓展纪录片的功能——影片通过“直接电影”技巧展示不同人物的教育观点,以及通过巧妙的叙事结构去强调人物在成长中某些状态之间的对比,无论相似还是反差,重要的是体现出人物是如何受到来自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影响,最终《零零后》正是要突出纪录片教育公众的功能。当然,从影片中多元创作方法到丰富的电影时间构建技巧来看,《零零后》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影视专业的学习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