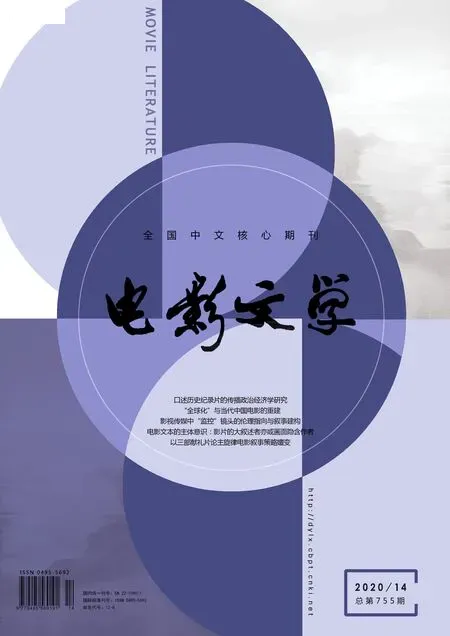基于后现代美学视角下“新女性”的凝视
2020-11-14黄磊
黄 磊
(绥化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黑龙江 绥化 152061)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流行的文化不仅是对现实主义思潮的反叛,而且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思潮的审美逻辑变革,在现实中人类审美能力的不信任和社会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怀旧感,这似乎对现在社会劳动意识和审美情感来说是虚妄的,但这是社会审美在劳动实践中不断革新的过程。在中国后现代审美文化中,实质上是多种综合审美思想与实践相提并论的体现,包括叔本华的生殖意识论、伯格森的生命进化论、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波普尔的理性批判主义等,在后现代的审美文化中共同铸就多元的审美文化,对整体的反叛性与同一性同时在社会中诞生,一种审美思维在社会中不可能长时间地占据主导地位,在后现代审美中看来,整体性不是社会本质的回归,而是对审美文化在逻辑上的一种批判,无论社会多么有秩序,差异性一直都存在于社会中,成为社会审美中一个审美逻辑的起点,一旦这个社会在整体性上不平稳,这个起点就成为社会审美中进行改革的重要基点。在后现代主流思想中,由于改革开放思想潮流的影响,各种思想在社会中思想现象和思想结果同时作用于社会人,对传统的审美逻辑叙事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女性不再是男权思想下的附庸,她们积极在社会中寻求一种与男权平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流批判思想,希望能够在社会中与男性共同承担责任,成为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另一半,女性思想的觉醒与自由思想的追求从另一种程度上讲也是中国社会在当代中主流文化的转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相夫教子思想在社会中已经失语,“新女性”思想逐渐在后现代社会中形成。
一、后现代审美中的“新女性”思想认识依据
在认识论中我们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认识一个客观世界进行审美劳动实践之时面对的自然呈现都是同一个世界,但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审美认识是不同的,每一个客观的认识在审美活动中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的审美实践就是通过多个感性的审美认识活动在现实中进行审美实践,通过审美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感性认识,通过理性思维和工具对现实社会中形成的多个感性进行逻辑推理,形成存在于社会中的理性认识得以传承。我们不难发现,在审美实践认识中主要有两个多变性因素:一个是个性的审美个体,一个是审美时代。个性的审美个体让每一次审美劳动都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既定审美标准来进行,通过这个审美标准来进行实践劳动和感性审美判断,可以说,多个感性的审美活动可以得到多个感性的认识,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体现之一。同样在审美活动中要将审美活动归类为社会实践活动,人的每一次实践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进行的,无论多少审美的综合都不会超越这个社会审美之外的认识。例如我们在原始社会中进行劳动实践就不会得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审美认识,无论怎样超前都不会逾越这个审美认识,不会超越它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是一种审美思维在社会上现代性的体现,不会超越这个认识。由此可见,社会中的认识是不断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女性”审美意识的觉醒实质上是社会中审美性在现实社会中的转向。在后现代社会中,物质文化和网络科技的进步让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生活中男性的优势逐渐在减小,女性积极参与到社会中来想表达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利。从女性审美方面看,社会无疑是进步的,但从男性角度看,男性权利与审美逐渐在社会中消解,女性的审美意识强大,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不平衡感。人们只能通过差异性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深刻的认识,以此来感受这个社会的变化,这使得男女在审美上都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希望自己的审美权力能够在社会中得以体现,社会审美从整体上看就必然是多元的且充满个体差异。
在后现代审美中,公众的审美认识无疑就是在“一”还是“多”层面上。传统的审美认识在实践上是遵循社会审美中一种整体性认识,在男权思想主导下的男性主流社会思想,“父为子纲”与“夫为妻纲”的意识有着雄厚的存在土壤。但西方的多种主流思想涌入中国之后,多种思想与结果综合呈现在观众眼前,公众只有被动地接受,不能加以逻辑判断,这对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带来严重的冲击。女性在社会意识中逐渐觉醒,渴望追求“自由”和“权利”,特别是后现代物质的发展让女性介入社会中逐渐形成物质基础,精神意识的独立成为女性表达自我意识的强有力武器,她们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可惜中国目前并没有女性文化雄厚的生存土壤,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两种状态:一是生存在男性意识下的独立女性形象,多表现为妻子获得生活的权利但依然要遵循丈夫的领导;另一种是城市的独立女性,表现为虽然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在精神上仍然是空虚的,依附于男性的。她们渴望独立,但在事实上仍然没有突破男权主导的社会意识层面,男权思想仍然是社会中主导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前面提到,审美社会已经走向了意识形态的逐渐独立,是由“一”走向“多”,女性意识觉醒追求精神独立,实质上是中国后现代审美女性主流思想的体现,她们不再甘于男权审美思维的影响,追求自我价值,存在于社会中的多样性才是社会本来审美的真实面目,多元的思想主导对社会生产并不是洪水猛兽。
二、底层叙事后殖民视角的觉醒
在传统审美视角上,女性形象与殖民主义实质上是底层叙事,女性、黑人、穷人等这些身份标签出现在社会层面上,将他们归类为底层人民或殖民下的,这些人群在社会中没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存活的唯一意义就是为这些统治阶级提供服务和生产价值,一旦失去了自身的价值,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成为被杀或遗弃的对象。从生产价值来看,她们的劳动生产就是一种机器化的劳动,这些人就是机器的视角,他们在劳动中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自由精神换取生活的必需品,生产性消失则一切价值随之消失。“新女性”意识审美思想的觉醒,实质上代表着底层叙事的觉醒,他们从底层劳动中从逆来顺受到开始反抗,这种意识的转变是现代文化转型的典型显现,他们渴望在现代文化中获得平等和自由。在后现代文化中他们渴望能够实现自己的审美权力,在审美性上已经通过一种审美趣味的塑造和转移,让每一个地区和不同的人都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价值,让他们似乎看到公平和自由,实质上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和自由就是一个幌子,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价值被剥夺,他们带着满心愉悦的感觉进入后现代消费体系,成为这种消费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消费体系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互联网进入公众生活中,便利的网络秩序已经逐渐深入每一个人心中,消费的方式开始进入多元化,在虚拟的网络时代中底层人物也通过虚拟的镜像进入网络中进行交流和消费,在虚拟的网络经济中去除了身份化和媒介化,信息的传递更加多元,在虚拟中人与人的交往实质上是最公平的。由此,他们在公平的消费和审美中获得了意识的觉醒,开始逐渐构建自己为中心的价值交易体系,逐渐生长出了很多的精英利己主义者,在这种同质性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生长成剩余劳动价值,资本的获取和平稳导致社会中的组织结构开始逐渐重新构建,女性意识在社会中的觉醒从这方面看就是资本在社会中的觉醒,他们需要一种更加合理的组织结构来合理分配资本。
黑格尔认为:底层叙事群体是一个没有自主性的群体,是一个狂想和敏感的区域,他们一直处在“精神”的梦寐之中,无法自己从梦游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在现实社会,底层叙事群体一直都是被动地接受,从来没有主动地进行自我表达,如在中国清朝时期,女性以小脚为美,女性都要裹脚,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违背了生活中的常理,但在当时小脚就是美的,女性就是为男性服务的,女性就是男权影响下的一种媒介群体,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尊严和自由,对社会生活之中的事情永远只是承受,在意识表达和建设方面依靠男性,从根本上讲女性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而在今天,女性进行自我物质创造的方式很多,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为女性的精神独立提供了保障,在社会中女性才开始表达自己的权力和欲望,她们通过不断的努力来解放自己的思想,要求与男性和平相处,现代社会中在具有相同义务时要求具有相同权利,这体现了现代性在当代社会中的扩张。由此看来,后现代中的女性形象在社会中能否独立其关键因素是物质构建能否得到保障。
三、告别男权:现代性思想解放的双重召唤
在今天,现代性话语权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从公众的审美接受上看,现代性的发展将之划分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显然有着很大的弊端。后现代虽然是对现代性的反叛,但从本质上来讲,后现代仍然是一种审美化的倾向,并没有完善的审美体系,整个划分是以现代性为基础提出来的;就时间层面讲,它构建了一种线性的时间发展轴,按照箭头的方向从左到右一直是进步的、现代的和高雅的,反之就是落后的、低劣的,这种划分方式在真实的社会中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艺术的发展都有一个高潮与回落的时候,并不是按照线性的叙事逻辑展开的。但有一种是除外的——男权主导的社会现状,虽然在很早之前是女性主导的社会群体,但是在最近的两千多年中依然是男性主导的,男性主流的思想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审美价值体系,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在现实社会中,则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女性就是为男性服务的。如电影《白毛女》中,喜儿虽然年轻漂亮,有着自己所喜欢的对象,但是地主老头拿租赁土地来威胁喜儿父亲,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同意这种荒唐的婚事,而目的只是能够在社会中存活下去。又如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面的主人公有多房姨太太,女人似乎只是男性用来生孩子的机器,她们离开男性就似乎已经失去任何的情感支撑和生活支柱,同时拥有多少女人是这个男人社会地位的象征。以男性为社会中心,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但在后现代社会中,互联网经济与西方主流思想对男权中心论进行强烈冲击,倡导女性独立,从女性独立中追求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告别男权,是现代性思想解放的双重召唤。
在现代大多数人群之上进行谈论“自我觉醒”实质上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是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社会审美意识变化的同时引起人们内心意识形态的审美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整体性的,而是多元的,每个个体根据自己内心的审美标准进行自我觉醒,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不同,其自我觉醒的意识就不同。如生活在农村中的妇女希望自己能够勤俭持家并且能够当家做主,城市当代女性希望自己能够爱情与事业双成,能够实现经济完全自由,当官的女性希望自己能够当民官匡扶正义,商人女性希望能够发家致富造福一方等,这些女性都在各自的领域进行革新,实现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但在具体呈现方式上是不同的。因此在后现代时期,“新女性”形象虽然整体上追求精神独立和个性自由,渴望社会公众身份的不同表达,但在具体呈现方式上仍然是非整体性的“多元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