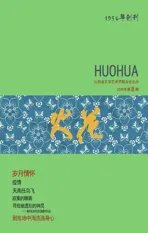老院
2020-11-12牛俊卿
牛俊卿
人到中年,风吹雨打,风雨兼程,常常乱梦纷纭。暗夜沉沉,从梦中醒来,便会回忆一些往事,往往泪湿枕畔。我也是如此,经常梦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老院。每当我梦到老院的时候,它的大门总是我童年时见到的那个样子,虽然老院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梦中的大门却从来没有变过,简朴的门楣,连一个像常见的“耕读”“勤俭”之类的砖雕小门匾都没有,两扇用许多木板拼成的门上,那些零碎的木板早已是沧桑的颜色。右边的这扇总是关着,门后顶了一个大树杈。这个大树杈有胳膊粗,它不仅仅用于固定这扇门。记不清童年时有一次我做错了什么事,妈妈追着要打我,当我跑到大门口时,顿时停住了脚步,拿起了这个大树杈,妈妈一看,赶紧退回到了院子里。从此我“难斗”的名声在外,几乎没有人再敢欺负我。左边的这扇门常年闭着,但一般都是虚掩着,一推就开。常年的磨合,使得两扇门早已配合默契,这扇门一碰那扇门,那扇门自动就会让一下,两扇门马上合二为一,根本不费力气。每次推开左边的门扇,一定会听到它碰触高处那个铁铃铛发出的清脆的叮当声,随即就会听到奶奶的问询:“是谁来了?”
老院是一个简易的四合院,而不是一个规整的四合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不是经过规划设计一步到位修建而成的,而是由不同时期的建筑东拼西凑成的:有明清时期的,有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有全砖瓦的,有外砖里坯的,还有全是土坯的墙壁。看一圈房子,就看到了前人为这个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往往是用尽气力盖好一座,过若干年又积蓄了点钱财,再盖一座或者翻新一座。这就使得堂屋没有耳房,而只能依据地形修了两个简易的风口,甚至它的部分前檐插在东屋的屋顶里,使我暗自佩服匠人的技艺,却又感叹前人的艰辛。母亲冬季在城里的时候,我过些天要回来看看。每当我看到院子里风吹落的枯枝败叶,总是涌起难言的悲凉。这些年,我走过了许多的荒村。见过许多的老院和老院里风烛残年的老人。有老人在,老院还整整齐齐像个样子,像个家。没有了老人的老院,长满了蒿草,有的干脆长成了杂乱的树林,老屋子塌的塌,漏的漏,成为鬼屋狐窟,令人不敢久留。一辈辈人的心血,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亡了。
我家的老院子原先并没有堂屋,或者说是有堂屋而早已倾倒,只剩一堵前墙,撑了一个门面。妈妈曾经告诉我,她嫁到我家的第二天,从东屋窗前看到堂屋的前墙吃了一惊,因为我爸爸告诉她家里没有堂屋,而眼前分明是有堂屋的。当她走过去才发现是一座假屋:墙后面的废墟上长了一棵很大的紫藤一类的植物,每年会开出一树特别香的花来。我对这株花没有任何印象,我出生时它早已被砍掉了。伴我成长的是老院里的另外的四棵大树。一棵是西屋的北窗下的石榴树。它有着盘曲的枝干,像大蛇一样扭曲。在一人多高的地方一分为二成两根主干,每年五月开着火红的石榴花,之后结出很多大大的石榴,我记得好几次把枝条压断了。中秋节的时候,石榴会长得裂开,露出红红的水晶般的牙齿,成为中秋夜向月亮奶奶进献的祭品。据说院子里原先经常有蛇出没,经过法师作法,把蛇精供奉到了石榴树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每次烧香的时候,我要在树下为蛇精老爷烧一炷香。而院子里也的确再没有出现过蛇。我只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黄昏上厕所时,分明看到一条白蛇缓缓从我眼前爬过。一棵树是南屋门前的苹果树。它结的苹果有一种特殊的清香,白里透红,脆生生的,奶奶说它叫“红玉”。我觉得它极易落下来,因为在它们成熟的时候,每天早上我上学时,推开门,先要在院子里逡巡一番,总能捡起两三个夜里落下来的苹果。如果正巧晚上下了雨,落得更多。妹妹似乎也盯着这些苹果。她曾经告诉我,小时候她也忧心着能早起捡苹果吃,而总无法比我早起,在她童年的记忆里,更多的是捡不到苹果的遗憾。苹果树为小院贡献了大部分的绿荫,患病后的奶奶常常坐在树下,沐浴在早晨的丝丝缕缕的阳光中。另外两棵树栽在大门的门道的东墙边。一棵是香椿树,它由两根相同粗细的枝干缠着长大。另一棵是臭椿树,比香椿树长得更粗。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奶奶让我抱着这棵树,念念有词:“椿树娘娘,椿树娘娘,你往粗长,我往高长”。也许,我念反过多次,使得它长得更高,而我越长越粗壮。我抱着椿树,学会了爬树的本领,以至于后来我不借助任何工具而能飞快地爬上很高的电线杆。这是院子里最重要的植物,其它的花花草草,似乎没有太多的记忆。只记得有两棵夹竹桃,忽然传说有毒,被扔了出去。还有几盆万年青,会结出红红的花生米大小的浆果,听说也不能吃。但我的老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婆婆,在晚年时,神智不太清楚,常常趁家里没人,把它们吃光。还有一种花,会结出鸡蛋一样的果来。
小院里的最初的结构就是这样,堂屋是假的,西屋是楼房,东屋和南屋是平房,大门原先也不在东南方,而在西南方。西屋无疑是院子里最古老的屋子。它有两层,门和窗户上面是拱形的结构,这是我们这个地区明末的典型构造之一。我后来也找到了确证:在西屋的楼上,发现了一个沧桑的木盒子,里面装满了买卖这个院子里所有房屋的契约。而西屋最早的一张卖契是康熙五十六年,足以证明它建于明末清初或者更早一些。这些契约从康熙到民国,详实地记录了西屋、东屋、南屋几易其手的经过,也使我大致了解了几位祖宗的姓名。西屋的二楼高度比一层还要高,足以使人居住。事实上那时候的房屋楼上也的确不是只供储放粮食与杂物,对于贫困而人口众多的家庭来说,二楼也是理想的居住之所。但是对于我的祖宗来说,似乎没有到二楼居住的必要。因为即便在旧社会,我的可追溯的祖宗历史上,人丁稀少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代代单传,流传下来两代孀妇担不动水而用小饭锅打水的艰难传说。在我的高祖父那一代,没有了子嗣。据说我的曾祖父是捡来的,他很聪明,能预知何时下雨,人称“小诸葛”。但他也只生育了我的两个老姑,最后从邻村庞家抱回了我的爷爷。爷爷和奶奶起初生的孩子也都没有存活,这种现象延续到我父亲降生后,全家人仍束手无策,只能在战战兢兢的恐惧中祈求神灵保佑。直到有一天路过一个算命先生,仔细看过我父亲的八字后,告诉我爷爷:“这个孩子是四奶奶踏破铁鞋从西藏送来的,不会有事,你放心养吧。”爷爷奶奶松了一口气,接着又生育了我的叔叔。
事实也果真如此,我父亲成为家庭中的重要人物。但在他的童年,也依然是不尽如人意的:在四岁之前,他一直不会说话,也不太走路,沉默寡言。曾祖父以为他是个傻子,气得他老人家把供奉祖先的牌位扔到了东屋的房顶上,西屋的房顶太高,他扔不上去。我的父亲和叔叔长得高大英俊,是远近闻名的一对帅哥。母亲告诉我,当年她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就决意要嫁给他。父亲当时是一个小医生,在一次为新兵体检时,被带兵的军官看中,一再动员他入伍,他到天津成为一名军医。而我的叔叔,则延续了家族可怕的印记:婚后不久,在为村里架设电线的过程中,他人还在电线上,有人无意中合上了电闸,他从上面跌落,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新婚,没有子嗣,几经周折,我的婶婶外嫁到了邻村。而我则被作为叔叔的继承人,从此跟着奶奶生活。对于家庭长久以来这种人丁稀少的命运,我不知道祖辈们是否进行过深思。如果从迷信的角度来说,是院子的风水问题吧?祖祖辈辈没有搬离这个院子,也许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另起新居,只能修残补缺,东腾西挪。如果说是人的问题,小户人家,可能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后来我听说我姥姥娘家祖上也曾经有着和我家一样的命运。到了我姥姥的大伯这一辈,他不甘于这样的命,奋力一挣,跑到西口,娶了个内蒙古女人。生了几个孩子,高额大鼻,从此改变了家族的基因。我见过的几个老舅都健健康康活到九十多岁。由此可见,人不甘于命运,奋力去抗争,往往就闯出了一条新路来。
奶奶居住在南屋。这是一个三加二共五间的平房。能看出修建时下了功夫。因为临街,修建时为了抵御雨季的洪水,后墙垒了很高的石条。在西墙上,出于风水的考虑,还安放了一个很大的抱着小狮子的大石狮。这尊石狮后来在翻新房屋时被安放在大门口。奶奶是一个极其爱干净的女人。我们居住在那个三间的房屋中,所有的器具一尘不染。房内有一盘大炕,还有一张画有花鸟的大床。幼小的我随着奶奶每年两次迁徙:秋冬时我们回到炕上休息,春夏时我们到床上休息。中间的红色的桌椅则伴随我度过了小学到初中的读书生涯。在我三、四岁时,奶奶总是抱着我,她有做花馍的好手艺,经常被人请去蒸馍。每当她抱着我去到一户人家,幼小的我总是对一屋子的奶奶夸赞我的奶奶:“奶奶天天抱着我,把鞋都磨破了”。一屋子的人就开始夸赞我懂事。虽然衣食无忧,但我和奶奶颇有相依为命的意味。奶奶做的拉面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食物。每当到了饭时,大门口就想起奶奶的喊声:“军肉,吃饭来”。以至于我恋爱时,对恋人的唯一要求,就是会做拉面。而几十年过去,我对拉面依然百吃不厌。
南屋的另外两间作为厨房,也有一盘大炕。每次放学后,我玩耍归来,就在炕上坐着看奶奶做饭。炕头有一个纸箱,里面放着我能搜集到的全部书籍。奶奶节俭,饭后关了灯去大门外与邻居闲聊,我往往就着通红的炉火读书。在炉火的映射中,我读完了《马本斋传奇》《汾水长流》《射雕英雄传》《三国演义》等等书籍,也从那时候迈入近视的行列。但当时并不知道近视是怎么回事,直到上了初中,和哥哥进城去检查了一下,才配上人生第一副眼镜。奶奶性格强盛,瘫痪了7年,挣扎了7年,最后终于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康复了。她认了命,也很快就走了。在去世前,她把我叫到跟前,流着泪看了又看,说了三句话:“只恨养育你这么大,看不上你成家!”“不管走到哪,要勤谨!”“不要惹人,惹人不好!”我跪在地上哭着,也把这几句话哭到了心里。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我上学还是上班,我总是告诉自己要勤勤恳恳;不管我的脾气如何暴躁,对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礼敬有加。奶奶去世后,我保存了南屋中奶奶用过的所有的家具,我想着将来退休后,回到老家,把这些家具原样摆放。可是,我现在明白了,人不如物,纵然家具都在,我的奶奶是永不在了呀。
使这个院子发生巨变的是我的父亲。他是我们这个家庭中脊梁式的人物。作为当时责无旁贷的唯一的男人,他可能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转业回来后,他担任过一个县里小厂的党支部书记,乡镇卫生院的院长。为了能回到家乡,他宁肯不当院长,主动申请回到家乡的卫生院担任副院长。他的人生越走越近。很长时间内我认为他的事业是失败的。好男儿志在四方,而他志在回家。这使少年的我对他颇有微词。而父亲也对不安分的我并不认可。起初,我能体谅到父亲的节约、积蓄,在我结婚前,我的工资除了留点零花钱外,全部上交给父亲。但我慢慢认识到,理财无非开源节流。不开源,只节流,终归不行。那时候,我正年轻,工作也不是太忙,就老是想着做个什么生意赚点钱,来来回回的折腾。而父亲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终于有一次我们爆发了冲突。我计划办一个小厂,当我试探着和他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他反应激烈,声称如果我要敢做这件事,他就搬出老院子,另租房子住,与我势不两立。我同样被激怒了,告诉他,只要他不嫌丢人显眼,我无所谓。我觉得我花自己的钱,不过出于礼貌和他商量一下,他不应当这么阻挠我。当然,父亲并没有搬走,直到几年以后的一个傍晚,父亲忽然理解了我,和我说,你这几年单枪匹马,也不容易。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也慢慢理解了父亲,在这个家庭中,他正如他的属相一样,是一匹忠诚的马。他安葬了他的祖母,他的父母,他的弟弟,他的头一个女儿。他承担了太多的责任,流过太多的泪水。在修房盖屋上,他像诸葛亮六出祁山一样一次又一次做着努力。第一次是在我出生前几年,由于叔叔的去世,可能请风水先生看了,认为没有堂屋不好,他和祖父决计修起堂屋来。正值文革末期,他们请了村里的许多人上山砍檩条和椽子,终于修好了堂屋,代价是拆除了东屋。因为东屋挡了堂屋的一个窗户。这样子,东屋又成了一个堆放煤堆土堆、养鸡养兔的地方,打了一堵低矮的围墙,上面摆放了几盆花。而大门也由西南方改到了东南方,成为标准四合院的模样。第二次是父亲雇人修建了一个砖窑,请人做砖,为哥哥修建了一排新屋。第三次是为了给我娶媳妇,又开始对老院子进行改造,翻新了南屋,修复了东屋。这次改造,由于我当时还小,父亲并没有和我商量,但随着岁月的增长,我很后悔当时没有阻止父亲,特别是对于南屋的翻修。前面说过,南屋其实修建得很坚牢,不需要重新修建。更重要的是翻修后,我和奶奶居住时的环境完全破坏了,那些老家具只有在原来的老屋子里才有那些古朴、和谐的氛围。这次改造也把院子里的树木都砍掉了,院子的地面也由青砖铺地变成了水磨石地面,以我现在的审美观,我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改造,我明白父亲的苦心,但这是我非常后悔的事情。
对于父亲来说,经过前前后后的努力,整个院子的房子都齐全了。他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终于松了口气。他没有想到,他很快就要走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当你肩负重担,累不可言,有时候恨不得早点死去,却能一直苟延残喘,健康没有大碍。当你觉得完成任务、从此可以安度余年,往往匆匆而去。父亲就是这样,一辈子的负重,在他刚刚退休的时候,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扶着父亲的棺椁送往墓地的路上,我哭了一路,我觉得父亲此生过得太委屈。他完全能有更好的前程,却为了这个家,让自己的事业黯淡无光。那些日子,每当我进到西屋,看到父亲的遗像和爷爷奶奶的牌位放在一起,我就忍不住痛哭。生前,他一直认为乡镇的党委秘书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多次表达出我以后能当个党委秘书就好。而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担任了家乡的党委秘书。我当时已经借调在外,可以不用再担任这个职务,但于我而言,哪怕当一天,我也要去当。宣读任命的那天早上,我在赶往机关的车上,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
老院子里只剩下我的老母亲了。每年冬季,妹妹都要接她进城过冬。但她始终认为,老院子才是她的家。一过五一,她就给我打电话吵着要回去。带着她那四五个大包小包。而我也分明看到,每当我送母亲回到老院子里,灰头土脸的老院,忽然就焕发了青春,堂屋的门吱呀一声,就笑着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