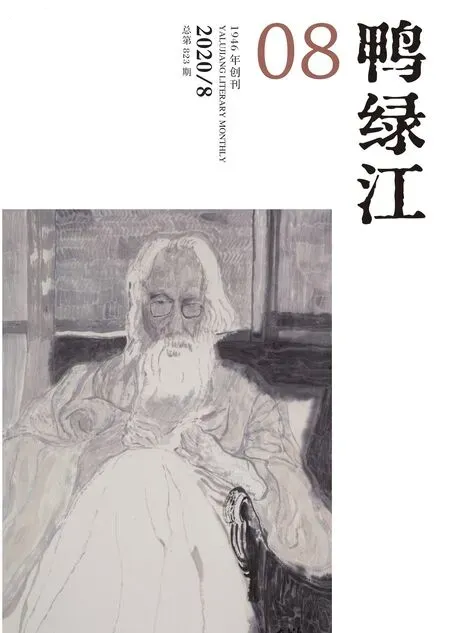鲁迅小说的艺术创新
——以《故事新编》为例
2020-11-12苏文洁
苏文洁
一、话语结构
在《故事新编》中有两个话语系统,一是包含作者自己主体意识的主体话语;二是被描述了的客体话语,也就是“他者言语”。
第一类话语不言自明,它表达了作者对于周围世界的主体性体验以及评介,它只属于作者自己。作者对世界的观点都包含在了这一话语之中。主体话语反映的其实是作者与世界的关系,它表达了在作者眼中,世界的图景到底为何。作家通过自己独特的想法和感受,将自己特殊的情感体现在语言和语句中,更重要的是要将自己观察世界、观察生活的感受和方式也表达出来,所以语言一定会带有他自身的独创性和自由性。写作的意义也在于此,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于世界的看法,如《奔月》《理水》《铸剑》中的话语。
《故事新编》的第二类话语是“他者话语”。既然是“故事”的新编,必然是对那些已经存在的神话、传说以及史实中存在的旧事进行重新描述。而描述的范围不仅包括故事本身,同时也包括对故事人物的言语与行为更加细致的虚构。我们关注的“他者话语”,其实就是故事中人物的言语。通观《故事新编》,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对其中人物的语言表现出了极大的描摹兴趣,甚至可以这样说,《故事新编》中对话语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故事本身。这些众多不同的“他者话语”成了《故事新编》中真正的主角。文本中出现了多少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在文本中发言,话语成了鲁迅关注的重心。每一个仔细阅读《故事新编》的读者,都能感到这些“他者话语”被作者推到了前台,如《补天》《采薇》《起死》《出关》等。
二、叙事特点
世俗化叙事是鲁迅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方法的创新,已有研究多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古与今的对照互动”,即通过现代反观古代,揭示古代人与事中某些被掩盖的真相;第二个常见的研究维度是“虚与实的糅合”,即将现实性细节有意识地融入历史小说之中,直接影射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具体现象。
对《故事新编》来说,世俗化叙事具有形式和思想上的双重意义。在“古今杂陈”和“虚实结合”之外的第三个维度是“神圣与世俗”的关系角度——既表现在原始文本与新编文本之间,又体现在新编文本内部。《故事新编》的“试验性”和“先锋性”特质表现为作者向早期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规范(以《呐喊》《彷徨》等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为代表)寻求突破的艺术诉求。现实与历史本身就有一种回望性,但是历史与现实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这就需要一种超脱俗常的、具有独特表达效果的叙述方式。文本中主要人物身份经过语境的变化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意义,即主要人物本身所代表的文化、历史意义与新编语境之间形成冲突磨合导致意义的指向性模糊化,多种类型的文本形态的化用使文本意义呈现出多层次性。因此,世俗化叙事形态下的《故事新编》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阐释角度和结论。《故事新编》中的世俗化叙事主要表现为“英雄形象”的日常生活呈现,也就是将“英雄”与“日常生活”两个元素形成一个“错位”的组合,表现英雄的日常性一面,或者说描写日常生活形态下的英雄形象。这样一种“陌生化”的表现策略,不仅具有题材上的创新性,更有创作指向上的独特思考。体现虚构文本对神话传说文本的世俗化作用的篇目有《补天》《理水》《起死》等,体现历史文献文本叙述重点的转移的篇目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等,体现民间故事对神话文本的世俗化作用的篇目有《奔月》和《铸剑》。
《故事新编》的多种文本类型之间并不是简单地拼凑相加,作者在各个层面上使不同文本类型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新编故事文本的戏剧冲突,使得以神圣叙事为主的历史文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既有历史文献本身的“言必有据”,又有民间故事的戏谑和滑稽色彩。
三、审美趣味
《故事新编》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民间”表达,即走向现实与反思的历史。出现了圣贤回归大地后的各种姿态,就是《补天》中的仙女嫦娥每天也得吃炸酱面,而后羿更是将吃表现到了极致,正像是人们常说的“吃饱才有力气干活儿”。就算是要赴天追回嫦娥,也要好好吃顿饱饭。而《非攻》中的墨子,也一改理性刻板的智者形象,他的出行方式有一种“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的感觉,必须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行路干粮。同样,在《起死》《理水》中也有相似的表达。这种描写的背后不仅是“圣贤”与世俗文化的抗争,也是“物质”与“世界”的对抗。所以羿吃完晚餐、休息好之后依然还是要上天追月。
《故事新编》还表现出了对自由的探索。鲁迅在《序言》中解释历史小说的创作规范时,提到了文体语言的自由和“随意点染”。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的确是新文体的创造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充满着古今交融、想象虚构的《故事新编》以一种独立的小说体例类型而存在。鲁迅对他的“自由”的使用效果是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他无意于对着古书照着讲,而是在中心情节发生之前或之后接着讲,在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新编。因此《故事新编》我们看到作者想探寻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同时,又让现代元素自由出入古代文本,为古今共有的一些普遍性现象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样一来,编年史的求“事实”被思想史的求“解释”所代替。文本中的女娲的“造人”和“补天”、嫦娥的“奔月”、三个头颅的“鼎中互噬”、庄生“起死之术”这些玄幻荒诞的情节的真实性被悬置起来。鲁迅并不为这些玄幻荒诞的情节做某些合理化、科学化的解释,似乎它们成为一种已然成立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