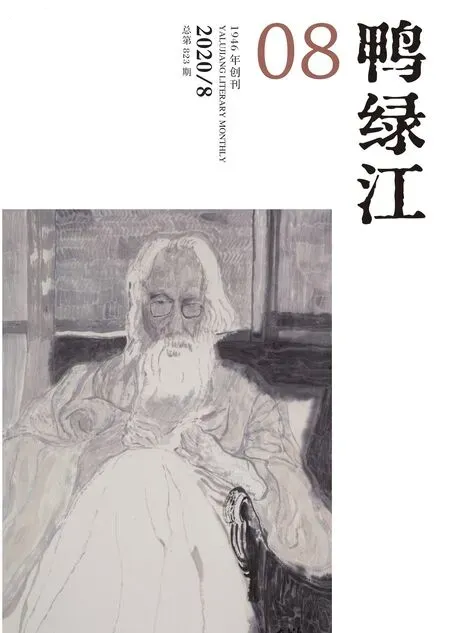莞城街灯·2016
2020-11-12熊流明
熊流明
习惯了把额头靠在窗的玻璃上看莞城静夜的街灯。
街灯细又长,正如人的孤独——细长。
人的孤独,只为寻找另一种孤独,有时候昼思夜想,绵延千里,百转千回。但有一种孤独,却是悄悄饲养,让其渐渐长,待时机成熟,嵌入另一只,独霸心地,然后绝尘而去。
我想,街灯比部分孤独的人好多了。它款款站着,在夜里一动不动于莞城街道。它等候所有沉重的、开心的、疲惫的、已老的和正寻找的孤独。当孤独从工厂与公司出来,帮他们褪去工衣,重组被服装缝纫机、惠普复印机碾碎的青春,牵紧被流水线、客服热线麻木的手,温暖地送他们回到租房,从不停歇。
街灯也孤独,也是孤独的结晶。在静夜,你摸摸它的身,寒冷至髓。那是种于街头待久了,风刮雨淋日晒霜寒之后,身心俱疲的标志。可是,它依旧笔立鞠躬,像谦逊的书生,一只挨一只保持距离,不说悄悄话不换岗,像静谧等待一位知音解读它的端庄、瞌睡与无奈。
上帝赋予街灯泸沽湖一般温顺的性格及宽阔的情怀——那种温顺与宽阔,就如你捏一片枫叶,扬进风的身体,叶子随风的心情卷到哪儿便是哪儿。但上帝却忘记赋予它同人一样灵便的肢体与美感的语言——它永远无法像人一样走在泸沽湖岸,双手拱形,呐喊对生活的热爱及美的向往,就如一位民谣歌手站在泸沽湖岸,看到随湖水漂来的是木头,随风吹来的是种子,歌手巴适的眼睛眯成一线,深情地唱出《泸沽湖情歌》。
这是街灯的遗憾。就在此刻,我为它们的遗憾而遗憾。
时间,离一个年字越走越近。
年,是单字,但时间把它延伸成一组词,再由几组词告一段落,由几段落顺势淌成某篇丰厚动人的文,比如鲁迅先生的《故乡》。
年,开始催促流客由街灯熟悉的每个角落走出,把包裹提、拉、扛,不分昼夜,无惧冬寒,行色匆匆穿过街道,最后淹没在夜的本质里。街灯,望着流客像水粒般从地球光亮之处蒸发而去,心不由自主地释放生痛,几乎哭出来。这震颤全身的难过,不是流客不辞而别,而是街灯已经接受莞城习惯性降予它关于聚散一词的重复演绎。它的难过,又是突然想到我的故乡在哪儿,我不知要怎样翻过这浓郁的林脉,渡过怎样的波涛海洋,方可抵达我的故乡。“哦!我没有故乡,我没有故乡可回,这就是我的故乡!”街灯好像明白了命里的生活真相。
“原来,我是孤儿!”街灯悲横痛肆地说。
街灯看着越来越空的莞城,眼泪像风摇李子花簌簌脱枝。泪花化作一道道柔意肆起的明亮,随街流淌,硕成涌洪。
情绪高昂的流客,一边走一边高谈:“今晚的灯光好洁净哈!简直美呆了!只可惜没月亮,莞城总是不见月亮!走哇……快点走哇……去东莞东搭最早的绿皮车回家哦!回家过年哦!”
……
年字末梢过去,循环至年字伊始,像时间的沙漏。
依然伫立的街灯,首先看见三三两两的流客,由蒸发之地凸现。随后,一群一群人头攒动像风吹麦浪般涌现。
他们,一样的包裹,一样的淳朴,一样高声阔谈及情绪高昂。他们像往年一样,在莞城街道消失又重逢,身后拖着细长的尾巴。那尾巴,也如街灯常年的温顺与孤独一样,一直温顺和孤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