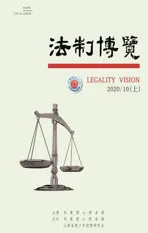社区矫正用警制度研究*
2020-11-03唐彦
唐 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2
社区矫正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它借鉴西方国家刑事执行制度,充分结合我国国情,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到2020年,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开展已逾十七年,在矫正刑事罪犯帮助罪犯回归社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根据司法部社区矫正司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达到了478万人。社区矫正服刑犯人约占全国罪犯总数的40%,重新犯罪率为0.2%左右,国家用于每个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经费约为1500元,不到监狱行刑成本的1/10。①社区矫正在全国施行,有效地节约了刑罚行刑成本,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在预防犯罪方面,社区矫正起到了标本兼治的作用,促进了社会和谐,提升了司法文明的水平,推进了我国的法治进程。
借鉴西方经验,创制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刑事执行制度,必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其间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问题。在众多问题中,社区矫正用警问题是困扰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构建社区矫正用警制度问题的提出
构建社区矫正用警制度是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执法环节设立社区矫正警察承担相关执法任务,从而避免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具有强制执法权,用警必须向公安机关求助或报警这一做法带来的种种弊端。当前我国承担社区矫正一线工作的主要是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他们属于公务员身份,不具有执法身份,也基本不具备专业执法能力,而社区矫正工作对象是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刑事罪犯,有些工作需要由警察这样的专业执法人员来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缺乏警察参与,也会弱化刑罚执行工作应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此外,全国多个省市多年以来都采取了借调监狱、劳教、戒毒民警等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方法。以北京市为例,借调监狱、劳教民警的做法始于2003年,借调这种临时性做法已经有长达17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建立社区矫正警察制度,将借调这种做法予以规范化与制度化。
笔者于2019年调研了北京市和成都市部分社区矫正机构。各级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能否建立社区矫正警察制度,如何构建社区矫正警察制度,普遍比较关心。我们不能忽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与实务界的呼声,应当对此做出必要的研究与回应。
二、构建社区矫正警察制度的必要性
(一)从理论上,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决定了需要警察强制力的参与
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社区矫正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论,即对社区矫正是否属于“刑罚执行”存在肯定和反对两种学说。在立法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将第一条立法目的由送审稿的“正确执行刑罚”修改为“正确执行刑事判决、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实质上是回避了学界一直以来对社区矫正性质的争论。
社区矫正性质之争的本质在于对“刑罚”一词外延的界定。否定社区矫正性质属于刑罚执行的学者们主要认为刑罚的执行应当是对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的执行,而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尤其是缓刑的执行不属于刑罚执行的性质。肯定说则认为凡是依据国家刑法对犯罪人的惩罚与制裁,对犯罪人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的相关制度都是刑罚制度。社区矫正定性为刑罚执行能较好地反映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才能有利于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②笔者认为,对社区矫正的定性应当从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实际需要出发,明确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这样才不会混淆人们对社区矫正的基本认识,将社区矫正误认为是一种安置帮教或社会福利工作,从而削弱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工作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我们不宜将“刑罚”含义的外延仅限于《刑法》第三章规定的五种主刑与四种附加刑。缓刑、假释、减刑、暂予监外执行等制度都是建立在主刑或附加刑执行基础上的刑罚附条件不执行制度或刑罚变更执行制度,前三者规定在我国《刑法》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中,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刑罚执行部分。从广义的角度界定“刑罚”一词,明确我国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才能促进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和完善。
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是刑罚执行,是与监狱行刑方式相对的非监禁性刑罚执行工作。刑罚执行自然蕴含国家强制力的运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社区矫正对象”这一不太符合法律规范的称谓来称呼社区服刑人员,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是受到国家刑罚制裁的刑事罪犯的身份。军队、警察、法庭与监狱是一个国家强制力的主要体现,国家强制力和国家制裁紧密相连,是法律权威存在的政治基础。在社区矫正中设立警察制度,以警察力量作为刑罚执行的后盾,配合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社区矫正志愿者等其他社区矫正力量同时开展工作,才能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二)实践上,社区矫正工作的风险性与实际工作执法环节需要构建用警制度
无论理论界是否将社区矫正定性为刑罚执行,实务界的工作人员面对的都是受到国家刑罚制裁具有一定人身危险的刑事犯罪人。社区矫正工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目前,我国在社区接受矫正的社区服刑人员绝大多数是缓刑犯。而假释犯的人身危险性明显大于缓刑犯,随着国家未来扩大适用假释,假释犯进入社区矫正的人数必将逐步增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风险也随之增大。
我国目前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人身攻击与伤害,还缺乏调查与研究。根据美国已有研究结果,社区矫正面对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刑事罪犯,属于高风险刑事执行工作。美国联邦缓刑与审前工作者协会(Federal Probation and Pretrial Officers Association)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做了一项关于缓刑官职业风险性的专门研究,该研究主要调查了十年内美国缓刑官在执行矫正工作中遇到的人身危险案件,统计数据如下:

谋杀或企图谋杀 16起 强奸或企图强奸 7起其他性侵犯或企图其他性侵犯 100起 枪击或企图枪击 32起钝器袭击或企图钝器袭击 60起 用刀刺砍或者企图用刀刺砍 28起开车撞击或者企图开车撞击 12起 肘击、脚踢、掐喉或其他身体攻击 1396起

(资料来源:Probation,Parole and Community Corrections③)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案发数量还是人身攻击类型都足以反映缓刑官这一职业的高风险性。美国绝大多数州的缓刑官与假释官都须接受一定的警务训练,在工作中穿着制服、佩戴专门标识、携带武器与手铐等警械装置,对社区服刑罪犯形成一定震慑力,经过一定专业警务训练也使得他们面对突发情况时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身份,没有执法权,缺乏执法能力,不能携带警械,在工作中遇到突发紧急情况需要像普通公民一样求助公安司法的力量。因此,我国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职业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根据笔者在北京市和成都市两地社区矫正机构的调研结果,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普遍认为社区矫正机构需要配备一定的警察力量。基本理由如下:
第一,在审前调查评估中有警察参与,便于了解犯人的真实情况,如是否吸毒、是否有犯罪记录、是否有赌博记录、家庭情况等。警察参与工作有威慑力,家属会更加配合,从而有利于调查评估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入矫宣告工作需要警察。警察身着制服对社区服刑人员宣告入矫,有仪式感与严肃性,有利于震慑服刑人员,使他们回到社区后能够遵纪守法,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的规定。目前,已经借调监狱民警或劳教民警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地区,一般都让借调民警主持入矫宣告工作。在未借调监狱或劳教民警的地区,各地司法局为强调入矫宣告的严肃性,做法不一。有的地区是与公安局协调请公安民警到场参与入矫宣告,有的地区是让司法局工作人员身着辅警制服,还有的地区是自行定做类似警服的制服,这些做法都反映出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对用警的实际需要。
第三,基层社区矫正机构需要一定数量的警察应对紧急情况的处置。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对象是刑事犯罪人员,具有一定人身危险。当前,各地司法所中服刑人员威胁工作人员或者家属到司法所闹事的情况屡见不鲜,尽管服刑人员伤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还未见诸报端,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面对一些性格极端的社区服刑人员时的确心存顾虑和担心。笔者在成都市某区社区矫正中心调研时,该中心正式编制工作人员为五名女性,面对每天进出社矫中心的刑事犯罪人,特别是面对一些性格极端或者有吸毒行为的社区服刑人员,工作人员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比较担心。为增加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威慑,增强工作人员的安全感,该中心无奈之下只能让招聘的三名男性专职社矫工作者身着无警徽警号的学员警服从事工作。
第四,在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审前调查和违规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中,警察一般受过专业训练,具有更丰富的调查取证经验与技能。特别是在社区服刑人员违规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方面,在调查现场、讯问违规违法人员、制作笔录、搜查扣押书证物证等方面,警察的专业能力明显比公务员身份的司法助理员更有优势。
第五,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收监工作,往往靠司法所工作人员与公安机关的个人交情,才能有公安警察的及时配合。当前我国公安机关承担的工作本来就繁重,警力往往有限。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公安出警的工作一般比较紧急,在协作过程中需要多种手续,程序流程复杂,很容易贻误工作时机,造成疏漏。如果设立社区矫正警察,由法律赋予执法权,对服刑人员的收监工作就有制度可循,不用再靠人情面子进行正常工作。
此外,鉴于社区矫正工作中必须应对的刑罚执行工作,我国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均以借调的方式从监狱、劳教、戒毒警察中抽调民警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实践证明,借调监狱、劳教与戒毒民警的做法有利于增强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监狱劳教部门警察长期与在押犯接触,有一定监管与矫正工作经验,能够较好地履行社区矫正工作。但是,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狱矫正相对的刑事执行方式,具有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借调的民警没有法律赋予的执法权力,不配备武器与警械,遇到紧急情况,执法无据。笔者在调研中访谈过部分借调民警,其戏谑借调民警是衙门前的石狮子,主要起威慑作用,难以发挥实际执法的功能。加之,借调警察的编制和实际管理仍在原单位,在晋升、管理、考核等方面均无制度保障,经常轮换也影响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稳定性。借调只是探索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的过渡做法,我们理应在社会条件成熟之际建立社区矫正警察制度,将社区矫正用警予以规范化与制度化。
(三)我国未来扩大适用假释的发展趋势需要构建社区矫正用警制度
假释作为一种为世界各国广泛适用的行刑社会化措施,它在帮助罪犯回归社会、预防再犯罪方面有显著的功能。西方各国假释适用率都比较高,尤其以英国的假释适用最为广泛,英国目前对判处定期刑期在12个月以上的罪犯,在监狱服刑时间只要达到刑期的一半,即可自动假释回到社区接受社区矫正,无须经假释委员会审核。④假释为罪犯在监狱与社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帮助在押犯尽快适应社会,避免因在监狱长期服刑脱离社会,出狱后居无定所无经济来源,而再次犯罪。
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管制犯、缓刑犯、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然而,实践中绝大多数社区服刑人员都是缓刑犯,假释犯极少。这一现状是由我国多年来极低的假释率决定的。2020年6月3日,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李静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假释适用率低,比例仅为1%左右,今后将加强研究,推进假释的适用。⑤我国假释适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罪犯假释期间再犯罪的追责机制导致办案人员不愿适用假释,而宁可适用风险低的减刑。要想提高假释的适用率,除了改变假释追责机制,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也是必需的条件。监狱能把假释犯“放出来”,社区矫正部门还得“管得住、管得好”,这样才能降低假释犯再犯罪危害社会的风险,保障他们在监外遵纪守法回归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设计,基本上是受过去十七年社区服刑犯人以低风险的缓刑犯为主的状况影响,缺乏一定的前瞻性考虑。如果将来假释率逐步提高,人身危险性较高的假释犯人进入社区矫正数量增多,必然会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风险与难度。2013年7月,北京大兴发生的假释犯韩某摔死两岁女童案就是假释犯在社区再犯重罪的典型案例。因此,构建社区矫正用警制度是适应我国扩大适用假释的需要。只有赋予社区矫正工作中部分人员强制执法权,彰显社区矫正工作的刑罚执行特点,才能为将来更多的假释犯罪人回归社区进入社区矫正做好准备。
三、构建我国社区警察制度的路径
《社区矫正法》出台之前,实务界要求司法助理员集体转为警察的呼声普遍很高。部分学者也认为西方国家在社区矫正制度中一般都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官,担任矫正工作,行使刑事执法权。由于我国目前不具备设立社区矫正官的社会条件,有必要赋予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司法警察的执法身份和执法主体资格,将其纳入警察编制。⑥然而,司法助理员全员转警势必造成我国警察数量过多,人浮于事的状况,同时也容易让我国有“警察国家”之嫌,从而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目前,这种路径已经由立法机关在《社区矫正法》中予以否认。我们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应当根据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察制度。
(一)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设立社区矫正警察
社区矫正警察执法工作既不同于监狱警察矫正工作,也不同于治安警察执法工作,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设立社区矫正警察,培养和训练专门的社区矫正警察队伍,有利于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2013年12月劳教制度废除后,劳教警察实现了分流转岗,《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的劳教警察已经不存在。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修订《人民警察法》,设立社区矫正警察。由于监狱警察、社区矫正警察与戒毒警察的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相似性,都具有对不法行为或犯罪行为的“矫正”性质,可以将社区矫正警察与已有的监狱警察、戒毒警察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新警种,统称为“矫正警察”,作为与公安警察、国家安全警察、司法警察并列的独立警种。
从社区矫正工作实践来看,劳教废止以后,已有部分地区的劳教民警转入社区矫正或戒毒工作,而有的地区长期借调监狱警察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因此,设立社区矫正警察,这一做法符合我国在社区矫正工作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二)社区矫正用警数量的配置
构建社区矫正警察制度,需要我们探索如何在社区矫正机构中配置警察的问题。我国国情复杂,东部发达地区社区服刑人员较多,而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地广人稀,社区服刑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按照每个司法所“一刀切”的配置模式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我们可以按照每个县(区、市)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人民警察,建立社区矫正警察支队,直接由县或区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统一管理,配备一定的武器、警械、交通、通信设备。司法所负责日常社区矫正工作,出现需要用警情况时,由县(区)司法局社区矫正警察出警,对社区服刑人员行使刑事执法权,体现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严肃性。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每个县(区、市)应当配备多少名社区矫正警察。笔者建议以该县(区、市)一年内社区矫正服刑人数作为社区矫正工作量依据,测算配置社区矫正警察的人数,通盘考虑全国的情况,权衡东西部地区矫正工作量与财政能力的差异,在充分的社会调研基础上,再做出科学决策。
(三)社区矫正的用警环节
如何划分社区矫正警察与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需要我们逐步明确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哪些环节的工作需要由社区矫正警察来承担,是构建社区矫正警察制度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社区矫正警察执法工作基本应当包括以下事项: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社区服刑人员接收与入矫宣告、脱管人员查找追捕、奖惩调查取证、禁止令的执行、违规违法以及再犯罪行为管控制止、收监执行人员送交执行等方面。在矫正工作的审前调查环节,由社区矫正警察组织实施才会更顺利地得到被调查者及其亲属的信任和配合。在矫正工作交付接收和入矫宣告环节,由社区矫正警察承担有利于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严厉性。在监督管理过程中,当发现社区服刑人员有擅自外出、脱离监管、违反禁止令等举动时,社区矫正警察应当承担调查取证与管理执法工作。在提请撤销缓刑、假释等执行变更环节,相关调查取证、法律文书制作与法律建议提交可由社区矫正机构人民警察来完成。在收监执行环节,由社区矫正警察处置可以确保执法的严肃性与时效性,避免求助公安派出所民警贻误收监时机,以及繁文缛节加大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四、结语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开展了十七年,探索与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发现社区矫正用警问题是影响和阻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社区矫正法》规定用警环节由公安机关承担相关工作,但从长远来看,构建社区矫正警察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当前社区矫正执法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公安机关治安工作压力,共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实践证明,社区矫正工作执法工作由公安民警代为行使问题较多,而从其他部门借调抽调警察协助工作只是权宜之计,借调抽调的形式必须予以规范化与制度化。从我国社区矫正更为长远的发展之路来看,构建社区矫正警察制度可能仍是一种过渡的做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官制度才是我国社区矫正事业的最终发展方向。
注释:
①《司法部: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已达478万》[EB/O L].中国新闻网,2019-12-28/2020-08-18.http://www.chinanew s.com/gn/2019/12-28/9045849.shtml.
②刘强.论社区矫正的社区刑罚执行性质[J].社会科学战线,2015(8):224-234.
③ Dean John Champion,Probation,Parole and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5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5),p.410.
④唐彦.英国刑事执行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152.
⑤我国罪犯假释比例仅1%,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将推进假释 适 用[EB/OL].2020-6-3/2020-8-18.https://www.sohu.com/a/399456060_116237.
⑥但未丽.社区矫正官执法身份的实然和应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