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之一)
2020-10-23黄荭
黄 荭
南京大学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是一部别样的传记,展现的不仅仅是杜拉斯自身的传奇,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纠葛,也是,或者说更是一个朴素的、关于写作的故事,看女作家如何用文字构筑起自身的神话,一点点垒起抵挡时间侵蚀的堤坝。这部传记着力还原的,是印度支那湄公河畔的玛格丽特如何“生成”纸上的“杜拉斯”的过程,就像在暗房里洗照片,胶卷在黑暗中慢慢发生化学反应,慢慢显影,生活的“负片(底片)”最终变成了黑白或彩色的相片,在时间或记忆的长河中漂浮。
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龚古尔奖失之交臂;1961年,《长别离》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64年,《劳儿之劫》出版,拉康撰文“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1974年,《印度之歌》获戛纳电影节艺术和实验电影奖;1984年,《情人》荣膺龚古尔奖;1992年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同名电影海报贴得满大街满世界都是,梁家辉和珍·玛琪演绎的情爱在欲望都市泛滥成灾,小众、先锋和知识分子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终于成了一个“通俗作家”……
2006年,杜拉斯辞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已然有种强烈的感受:杜拉斯的作品正在被经典化。那一年,《音乐》《痛苦》《广场》《死亡的疾病》《夏雨》《广岛之恋》被再次改编搬上舞台,巴黎电影影像中心(Forum des images)举办了杜拉斯电影回顾展,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她的手稿展和系列讲座,冈城(Caen)的现代出版档案馆(IMEC)推出“关于爱”的展览,特鲁维尔的黑岩旅店举办一年一度的“杜拉斯日”……与此同时,法国各大报纸杂志也纷纷推出纪念专号或刊登大篇幅的纪念文章,如《欧罗巴》《文学杂志》《读书》《新观察家》《观点》《解放报》《世界报》《费加罗报》等等。据杜拉斯作品最主要的两家法国出版社:伽利马出版社和午夜出版社透露,杜拉斯的大部分作品不仅是畅销书,而且还是“长销书”。同年4月,法国《费加罗报》对杜拉斯作品在法国的发行做过一个统计:自《平静的生活》(1944)出版以来,杜拉斯的作品单在伽利马出版社一家就已经累计卖掉了400多万册,每年Folio丛书售出杜拉斯作品的口袋本就有10万册。《广岛之恋》1972年以来已经卖出60万册口袋本;《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78年以来已卖出62万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年以来已卖出16万册。在午夜出版社,《琴声如诉》从1958年出版以来卖出96.7万册,现在每年还保持着1.1万册的销量;《情人》1984年以来在书店卖出140万册,在读书俱乐部卖出240万册,现在还保持每年1.8万册的销量。随着《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于2011年、三四卷于2014年在“七星文库”出版,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学先贤祠的标准姿态:不朽。
2014年杜拉斯百年诞辰之际,国内外各种出版、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电影回顾展、戏剧演出、作品朗诵会更是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单说国内,从4月4日作家生日那天开始,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报刊媒体掀起了一阵铺天盖地的“杜拉斯风”,《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文艺报》《东方早报》《社会科学报》《外滩画报》《东方卫报》《南都周刊》《深圳特区报》做了杜拉斯专题,《经济观察报》《上海壹周》《南京晨报》《晶报》《广州文艺》等大小报纸都或严肃或矫情地向法国女作家致敬、缅怀和抒情。从发表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来看,“情人”和“爱情”无疑是杜拉斯的关键词,加上“欲望”的发酵,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整个中国文坛都在如痴如狂地爱着杜拉斯那“备受摧残”的容颜。
黑色大陆,“没完没了的童年”
“玛格丽特·杜拉斯生在印度支那,在那里她父亲是数学老师,母亲是小学教员。除了童年时代在法国有过一次短暂的逗留,她直到十八岁才离开西贡。”这是杜拉斯用在很多书前面的一段简短的自我介绍。第三人称,很奇怪的概括。仿佛“我”已经变成了书上的“她”,整个人生都还滞留在那个已经逝去的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回不去的童年,而她在出生以后只有一个寓意深远、矛盾但决绝的动作和姿态:“离开”。东方,那一片隐没在遗忘海上的黑色大陆,它既是虚构的原点、也是解构的症结,无所不在的缺席,犹如20世纪“已死的”上帝。
劳拉·阿德莱尔在《杜拉斯传》的开篇引用了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书信集》中意味深长的几句话:“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梦游一般,弄不懂什么是故事,什么是生活。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影子的生活;我觉得我不再是在地面上行走,而是在飘,没有重量,四周也不是空气,而是阴影。”[1]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拉斯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每当她写作的时候她都会回到那里,回到童年。东方内化为“内心影子”,再转化为文字得到纾解和释怀,换言之,“我”成了文本,“我发现书就是我。书唯一的主题,就是写作。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2]。
的确,仔细阅读杜拉斯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不管是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系列还是印度系列,杜拉斯作品并不是孤立散落的,而是一个藕断丝连、盘根错节的互文本[3],爱情故事并非这个网络的结点和主题,爱情常常是表象和素材,主题一直都是写作,孜孜不倦对写作方式的探索,“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4]。玄机就在“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我”如何在孤独、绝望、乃至酒精中沉淀、迷失、转化为文本,最终与“我”无关。
1914年4月4日,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交趾支那(现为越南南部)嘉定市。除了童年时代在法国度过两次短暂的假期,18岁前她都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长大。“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这份一成不变、无法逃避的炎热从此滞留在杜拉斯的血脉里,热情、疯狂又绝望;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成了她的精神故乡,深入到她的思想、她的灵魂,“成了她生命的底片,西贡那散发着毒气的灿烂令她沉迷,神秘的中国城酝酿着种种被禁止的罪恶,小路上种着罗望子树,掺杂着干枯玫瑰的花毯……”[5]
2.Saussure,Ferdinand de.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M].La Salle:OpenCourt,1989:68.
童年的玛格丽特
那是混沌初开的场景:“一直以来,甚至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看到地球上的生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一个巨大的沼泽地,表面上毫无生气,突然,一个气泡破裂了,发出臭气,唯一的一个,然后——几千年过去了,又出现一个。同时这些气泡,这些生命的泡沫终于从底部冒出来,光线变了,潮湿渐渐消失,光到了水的表面。创世纪的水,对我而言,就是这样,沉重像液体的钢铁,但在雾气中很浑浊,没有光的照耀。”[6]这种创世纪的水就是世界“印入”小玛格丽特的图景,对日后的作家而言既是生命的开始,也是她日后写作最重要的素材,太平洋每年泛滥摧毁母亲堤坝的黑水,这一象征了这片遥远的原法国殖民地上的不公正、穷困和绝望的沉重的海水成了她创作的灵感之泉。
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风景和画面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湄公河三角洲上强烈的阳光、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穿透了城市乡村的安南方言、洒在对着暹罗森林的平房游廊上的月光……在这片原本不属于法国的土地上,在这片他者的土地上,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于是这片土地于她是“母亲的土地,故土和精神的栖居”[7]。她对朋友米歇尔·芒索说过:“我,我有过森林,雨水,有过我的出发点。我的根在越南的土地上。”[8]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让她沉迷,东方的神秘开启了她创作的灵感,和她个人经历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东方也充满了“沧桑”、“耻辱”和“身不由己”。殖民地凄凉、麻木的痛苦生活成了她以“毁灭”“绝望”“荒凉”为主题的小说理想的温床。
一切都始于童年:生命、爱情、绝望和写作。处在一个侨民、普通白人、安南人和中国人混居的世界,多纳迪厄一家既不属于白人殖民资产者阶层,也不属于被殖民的黄种民众。肤色是第一次划分,象征了尊卑;财富是第二次划分,代表了贵贱。堤坝的故事、母亲的疯狂和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极度的穷困占据了童年最初也是唯一的梦境。杜拉斯的身份一开始就是特殊的:出生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一个贫穷的白人家庭,不被有钱的白人认同,同样也不被有钱的当地人和中国人认同,所以小玛格丽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于她既是异地又是故乡。东方幽灵成了她所谓的“内心的影子”,渐渐酝酿成她日后充满毁灭意味的写作。“人们受到自身经历的纠缠,必须听之任之。”[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拉斯任由童年潜伏在记忆的黑夜,没有道路,她只是偶然谈及少年时代故事某些“明亮的部分”。

童年的玛格丽特
虽然在杜拉斯的语汇里,读者轻轻松松就能找到许多亚洲的地名和河流名:印度、加尔各答、拉合尔、恒河、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交趾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暹罗、西贡、永隆、沙沥、湄公河、中国、抚顺、广岛……但总体的指称“东方”(Orient)一词却极其罕见。玛德莱娜·博格马诺在《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问题》一文中指出杜拉斯曾在两处使用了“东方”一词。
一是在发表于1964年那本谜一样开启了“印度系列”的小说《劳儿之劫》[10],雅克·霍德和塔佳娜·卡尔在森林旅馆房间幽会,雅克·霍德说着情意绵绵的话,嘴里喊着塔佳娜的名字,心里不自觉想的却是那个在爱中迷失的劳儿。塔佳娜先是陶醉,之后突然意识到了,愣在那里,“面对着这些话的不良指向”[11](Tout d’abord dans le plaisir qu’elle aime de voir dans quelle liberté on était auprès d’elle puis, tout à coup, interdite, dans l’orient pernicieux des mots.[12])。中文翻译已经湮灭了“orient”的本义,的确杜拉斯这里的orient(orientation?)用得令人费解,甚至十分可疑。一点启示是前几段里出现过的另一个意思相近的表述,塔佳娜表示对雅克·霍德话中的“所指目标没有把握”[13](incertaine de la destination des mots)。如果杜拉斯用orient是故意留了一个线索,那我们不妨做一个杜拉斯喜欢的文字游戏,“l’orient pernicieux des mots”(词语恶意的指向,但脱离原文本的语境,这个词组完全可以译成“词语[建构]的能毒害人的东方”)调换一下词序可以得到“des mots pernicieux de l’Orient (discours sur l’Orient)”就变成了“关于东方的能毒害人的词语(话语)”。前一种语序排列似乎可以这样解读:东方被认定能毒害人的危险特性是由词语建构起来的,是近代西方对东方一种日趋定势的想象,随着东方文明的衰败,东方也成了贫穷落后、疫病流行的受难之地。后一种排列似乎更多地可以理解为关于东方的词语(描述)常常是带有欺骗性、能毒害、蒙蔽人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父母不就是受到殖民地宣传画和“皮埃尔·洛蒂的一些阴郁神秘作品”[14]的蛊惑才毅然决然地抛下让人“厌烦得要命”的法国北方乡村来到那个预示着财富、冒险和梦想的远方?而等待他们的却是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幻灭。

《劳儿之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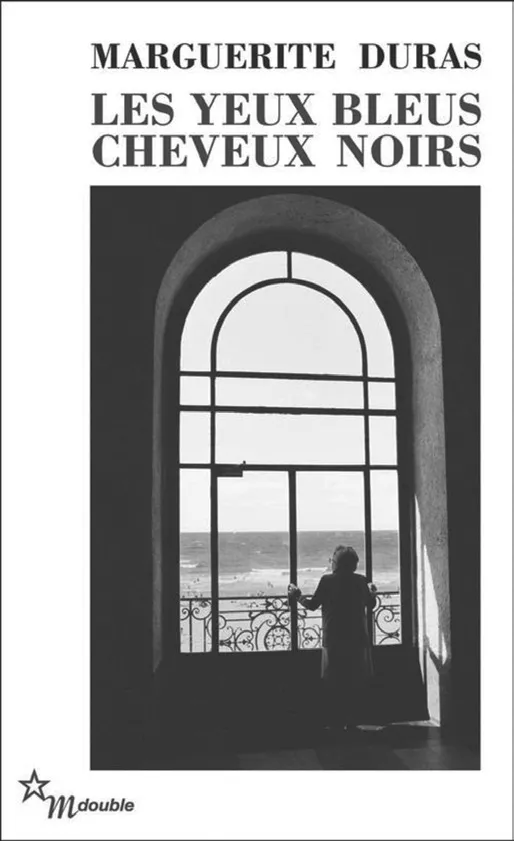
《乌发碧眼》
另一处是在《乌发碧眼》中:
事情随着死亡的突然降临而发生。
她用很低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呼唤着一个人,仿佛那人就在这里,她似乎在呼喊一个死去的生命,就在大海的那一头大陆的另一侧,她用所有的名字呼唤着同一个男人,回声中带着东方国度呜咽般的元音……[15]
意象加深了,东方[16]是那滴眼泪闪烁的珠光,被文本诗化的痛苦和绝望,在对立于西方的“大海的那一头大陆的另一侧”呜咽(沉默)。而那一个人是死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战场上的小哥哥保尔,是杜拉斯无处告别、始终无法被彻底埋葬的童年,和童年的一切。用所有的名字朝同一个方向(东方)呼唤“无名的”东方,呼唤“永失我爱”。
(待续)
注释:
[1]【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Libération, 13 novembre 1984.
[3]户思社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有一章专门分析杜拉斯文本的互文性问题。
[4]【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5]【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第1页。
[6] Marguerite Duras,Les Parleuses, entretiens avec Xavière Gauthier, Éditions de Minuit, 1974, p. 239.
[7] Laure Adler,Marguerite Duras, Gallimard, 1998, p. 17.
[8] Michèle Manceaux,L’Amie, Albin Michel, 1997, p. 142.
[9] Aliette Armel,Marguerite Duras, les trois lieux de l’écrit, Christian Pirot, 1998, p. 13.
[10]这本书不仅对“印度系列”很关键,对杜拉斯全部的创作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文本,掀开文字表达表面的晦涩,其实杜拉斯给读者很多解读其人生和创作的钥匙。
[11][1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劳儿之劫》,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126页。
[12]Marguerite Duras,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inDuras, romans, cinéma, théâtre un parcours 1943-1993, Gallimard, 1997, p. 806.
[14]【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谭立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5]【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乌发碧眼》,王道乾、南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16]在法语中,orient也有“珍珠的光泽”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