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乡愁以及回望
2020-10-23程玥
程 玥
我便是那蜡烛,在盛宴中消亡,天明后请收拾一地的烛泪,从中读取什么值得哀悼,什么值得颂扬。
我们奉上最后一丝愉悦,如何能换来平静的死亡……
——《乡愁》

他是诗人的儿子,天生拥有一双悲剧演员的眼睛,电影是其一生的信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镜头语言深深根植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虽背离了安常守固的线性叙事,却具有庄严的文学感。在表层的故事背后,有着关于整个历史进程复杂性的深刻见解,传递出一种独特的诗性与宏大的悲悯。
亲爱的安德烈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年4月4日出生在俄罗斯伊万诺沃州札弗洛塞镇,他的父亲阿尔谢尼伊·亚历山德罗维奇·塔可夫斯基是知名的诗人、翻译家,母亲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维申雅科娃在出版社做校对员,家庭成员中还有一个名叫玛丽娜·塔可夫斯卡娅的妹妹。
阿尔谢尼伊才华横溢、仪表堂堂,早年即与多位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作家交往甚密,同时也是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和安娜·阿赫玛托娃非主流文学思想圈的重要成员,他在文学表达上始终恪守自己的立场,对纷繁芜杂的社会时局和大肆盛行的日丹诺夫主义漠然置之。1935年,他抛弃了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很快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缺席了塔可夫斯基的童年,但其堆积在案牍上未经发表的诗作却慰藉了他的内心,成为了最佳的艺术启蒙。敏感、孱弱的少年在佩列杰利基诺乡间宅邸的午后,花费大量时间反复阅读、咀嚼这些文字,逐渐增进了关于父亲对文学热忱和土地情怀的理解。无论这个男人亏欠家庭与否,但作为诗人,无疑他是杰出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塔可夫斯基一家搬回了莫斯科。坚韧、顽强的母亲在艰苦的环境下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同时照料着年迈多病的祖母。难以置信的是,尽管生活拮据,母亲仍然支持塔可夫斯基利用课外时间学习了绘画和雕塑,推荐他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艺术品位和审美能力。19岁那年,塔可夫斯基被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录取,在那里学习阿拉伯语。两年后,个性散漫、热爱嬉皮士文化的他选择了退学。在母亲的鼓励下,他以地质考察员的身份加入了一支探险队,远赴西伯利亚东部淘金。
或许在近三年的游历中,西伯利亚广袤的原野与密林,令塔可夫斯基深刻地体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完善了他对未来人生道路的真正判断——做一名电影导演。回归莫斯科生活后的他很快进入了国立电影学院,师从米哈伊尔·罗姆。得益于米哈伊尔高超的艺术造诣和教学水平(他也是塔可夫斯基坚定的支持者),塔可夫斯基的导演课程进展十分顺利,并结识了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亚历山大·戈尔东、瓦西里·马卡罗维奇·舒克申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热衷于谈论英格玛·伯格曼、罗伯特·布列松等欧洲电影巨匠的创作和风格,洋溢着学院派年轻电影人的活力与激情。在导师的鼓励下,他们先后拍摄完成了两部试验色彩浓重的短片——《杀手》和《今天不离去》,虽然反响一般,但是在剧本改编、拍摄调度甚至表演探索方面却收获了重要的经验。
1957年,塔可夫斯基和19岁的女演员伊尔玛·拉乌什结婚,她的身影曾出现在塔可夫斯基早期的电影作品当中。塔可夫斯基对女性的态度是矛盾的,从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对母亲长久以来的养育满怀感激,失意时曾不断向她祷告,流露出不为人知的脆弱一面。但有时他又非常大男子主义,将女性定义为“以爱之名的屈服和忍辱”。
随着阅历的增长,塔可夫斯基的性格越发深沉,充满忧疑,看待事物的观点令人无从琢磨,这也导致了他与最初在创作上紧密合作的一些挚友分道扬镳。
三类导演
完成全部的学业后,塔可夫斯基进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从事助理导演工作,虽然他的毕业作品《压马路和小提琴》获得了纽约大学生电影节一等奖,但仍未引起制片厂的足够重视,在当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三类导演”。
1961年夏天,命运向塔可夫斯基投来了第一枚迎来转折的橄榄枝——他临危受命,接手一部陷入僵局的电影。《伊万的童年》根据弗拉基米尔·博戈莫洛夫的短篇小说改编,讲述双亲被德国纳粹杀害的少年伊万,怀着对纳粹的仇恨,投身革命为国效力的故事。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初衷是将其打造成另一部《雁南飞》式的标杆之作,前期已经为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原导演爱德华·阿巴洛夫拍摄出来的效果却极其不尽人意,最终迫于压力退出了剧组。
整部影片只剩下一半的制作经费,可塔可夫斯基向制片厂提出的条件更像是把自己逼入了死角:重写剧本,同时拒绝观看或使用之前已经拍摄的素材,哪怕一米胶片也不行。再者,为了重新开始,更换演员和技术班底。制片厂的领导们对塔可夫斯基显然并没抱有太大的期望,但在后面几个月的工作中,塔可夫斯基的效率和才华令他们刮目相看,除了对影片中具有象征色彩的梦境场景颇有微词外,绝大部分的拍摄成果不乏情感冲击力,这些都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伊万的童年》呈现了塔可夫斯基强烈的反战意识和少年情怀,主人公伊万置身于残酷而坚硬的现实,他的创伤首先来自于家庭的破裂,但在战争对其心理和生理的长期影响下,善恶认知的界限逐渐模糊,孩子、英雄、魔鬼、殉道者的多重身份最终产生了毁灭性的错位,交融成为悲剧的根源。
1962年4月,该片在莫斯科中央影院举行了首映,随后官方将其作为儿童电影广泛发行。同年8月,第2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将金狮奖颁给了这部影片,欧洲电影界人士纷纷认为《伊万的童年》标志着当代电影一位伟大形式主义者的到来。影评人乔治·杜萨尔曾这样评价道:“如果想要认识新一代苏联导演,那就去看这部作品吧!”法国存在主义哲学领袖让-保罗·萨特则在给《团结报》编辑的回信中表示:《伊万的童年》是他近年来看过的最为出色的电影,优秀的年轻作者身上兼具戈达尔快速又简略到晦涩的节奏以及安东尼奥尼般自然原生的悠缓,但他同时指出了影片主旨的深刻内涵:每一次动荡中,历史都需要英雄,它创造他们,并且通过他们在自己所塑造的社会中受尽磨难,来毁灭他们,这是一种巨大的荒谬。萨特带有批判性的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为了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塔可夫斯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在媒体访谈中多次提醒人们应从非历史角度看待、欣赏这部电影,不要过度解读,尽可能地去淡化影片的政治色彩。
30岁的塔可夫斯基,因为一部曾不被看好的处女作所取得的声望已经远超他的前辈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等人。盛名之下,却危如累卵。是擎起苏联电影众望所归的复兴旗帜,还是跳出藩篱,成为萨特口中的超现实主义大师?殊不知他已悄然踏上崎岖的苦旅……

电影《伊万的童年》海报
固执的天才
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曾说过:一些电影主管者嫉妒塔可夫斯基和他的天赋,就像性无能的人对性能力的嫉恨一样,致命且难以消除……
1963年2月,塔可夫斯基加入了苏联电影工作者工会,《伊万的童年》所取得的成功,令他不再像新人导演一样为电影的制作预算而发愁,他开始雄心勃勃地筹备史诗传记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制作,讲述了传奇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跌宕起伏、为追寻信仰而苦苦求索的一生。这个有着东正教僧侣和艺术家双重身份的人物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是官方也无法否认的。同时,凭借充足的预算,塔可夫斯基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如果他能够识时务地在影片中表达出官方所期望的民族反抗精神,那么本片极有可能奠定其新一代电影领袖的地位。
年轻的塔可夫斯基过分坚持自我,他试图从安德烈·卢布廖夫的创作心理层面切入,研究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和非宗教情感是如何创造出永恒的精神价值的。这种剑走偏锋的拍摄思路加上漫长的制作周期令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大为光火。直至1966年年底本片小范围上映时已经耗费了四年的时间,成片的效果也让电影主管部门无法接受,他们猛烈批判整部电影晦涩难懂,出现了过多残酷和裸露的镜头,卢布廖夫被刻画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结局带有一种自然主义的残忍。他们认为塔可夫斯基变得忘乎所以,失去了一些创作上的“良好品质”。即使后来塔可夫斯基试图通过剪辑进行补救,影片仍无法摆脱当时被禁映的命运。
四年的心血未能得到肯定,塔可夫斯基只能投入全新的项目来消解沮丧的情绪和债务的压力,他完成了电影《镜子》的剧本初稿,并将目光瞄向了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小说《索拉里斯星》。主管部门对后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这部科幻题材的影片能够打开国际商业市场,因此顺利通过了该片的拍摄计划。
1970年,《索拉里斯星》正式开机。鉴于《安德烈·卢布廖夫》的“前科”,整个剧组的人员配备完全由制片厂掌控决定,塔可夫斯基怀着极为郁闷的心情完成了影片。拍摄过程中,他曾远赴日本取景,回国后却时刻处于疲惫、焦虑、愤懑的状态,甚至觉得委派下来的制片主任就是个干涉他创作的草包。同年夏天,塔可夫斯基和妻子离婚,迎娶在拍摄《安德烈·卢布廖夫》时结识的拉里莎·帕夫洛夫娜·基齐罗瓦。在此期间,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阿里克谢·罗曼诺夫召集了邦达尔丘克、格拉西莫夫、库利赞诺夫等一批业内专家对《安德烈·卢布廖夫》提出修改意见,塔可夫斯基只能被动接受,这部电影最终在秋天迎来了解禁。
两年后,《索拉里斯星》同样在经历反复修改后取得了发行许可,制片厂厂长尼古拉·西佐夫在罗曼诺夫少将的授意下,明智地将其送到了第25届戛纳电影节上,最终影片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大奖。这符合众人的预期,也让塔可夫斯基与主管部门原本焦灼的关系得以缓释。很快,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将他列为“一类导演”。更值得庆幸的是,《索拉里斯星》的成功将原本夭折的《镜子》挽救回来,塔可夫斯基终于被允许开拍这部带有半自传色彩的作品。
1973年,《索拉里斯星》在莫斯科正式上映后,仍不乏批评和反对之声。这是一部披着科幻片外衣的“塔式电影”,充满玩味且意义模糊,然而又不时朝着理性智识的方向发展,其所表现的星际科考之旅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思维和灵魂的执着求索。显然,塔可夫斯基没有放弃带给他荣耀的哲思与深沉,以及对传统叙事手法一再的轻蔑。
审视与追寻
《镜子》是一部极其私人化的电影作品,记忆中的农庄、阴霾、田野、树丛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它是塔可夫斯基对自我的一次重要寻找。影片回顾了他的童年和少年阶段,对于父亲不辞而别的原因、母亲隐忍多年的理由,塔可夫斯基在历经现实的沧桑之后,深刻理解了别无选择的环境和忧愁困苦的人生,他在电影里将那些充满情感的画面排列出来,给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1974年7月,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的官员们在观看完《镜子》的样片后,一头雾水,但是他们仍旧给出了冠冕堂皇的评价:不知所云的电影,素材散架,没有整体性可言,也未表现出人物与国家的联系,总之无可救药。塔可夫斯基写信给他们表示拒绝修改该片。同年年底,《镜子》只被允许在电影工会小范围放映。
因为创作上与上级的对峙,塔可夫斯基的生活更加困顿,他梦见自己死了,并开始有了记账单的习惯。为了负担起生活开支,他更加努力地寻求其他的工作机会:在亚美尼亚电影《酸葡萄》中担任艺术顾问,还与哈萨克斯坦作家穆赫塔尔·奥耶佐夫一起担任了两部电影的编剧。此外,他心底有一个念念不忘的拍摄项目——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小说中主人公感化他人的方式有一种殉道者式的悲壮和决绝,这与塔可夫斯基关于道德拯救的情怀不谋而合,为此他专门完成了一个剧本大纲。
塔可夫斯基的第五部电影《潜行者》的主题标志着他彻底走上了行而上学的道路,影片改编自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小说《路边野餐》。在想象的维度里,人类文明奄奄一息,三个不同身份的普通人通过穿越一片危机四伏的末世禁区,试图找到欲望神秘的本源,因此这注定是一场奥德修斯之旅。在这部影片中,塔可夫斯基的审视发生了距离的变化,从个体延伸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对现代文明的丑陋和无序表现出深刻、积蓄已久的悲观情绪。

电影《镜子》剧照

电影《潜行者》剧照
《潜行者》的拍摄过程不乏困难险阻,第一个拍摄版本因为技术问题无法放映,促使塔可夫斯基解雇了摄影师格奥尔基·雷贝格。1978年4月,创作上的劳累与挣扎引起心肌梗塞,直至一年后,逐渐恢复状态的塔可夫斯基才得以完成二次拍摄的工作,他坚信比之以往作品中流露出的“太多琐碎、短浅与虚假”,《潜行者》会是自己最好的一部电影。然而,这部影片的生存空间遭到了邦达尔丘克新作的无情挤压,甚至好友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同期作品《西伯利亚颂》都因题材优势引起了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而《潜行者》则被简单粗暴地归入第三等级,导致拷贝低于正常数量,大部分城市都无法放映,观众和媒体在电影院里根本看不到这部作品的踪影……
1979年秋,对塔可夫斯基影响巨大的是母亲去世,他感觉各方面的运气都与自己背道而驰,人生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至暗时刻。
乡愁
一面是声名远扬,一面是债台高筑。
即使选择出走西方,受集体主义影响深重的塔可夫斯基对苏联电影体系自始至终都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真正地承认他,让他和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他曾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像个孩子般喋喋不休地抱怨道:“我只是一个为苏联电影作出了贡献的艺术家。我现在都怀疑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是最后一个。事实上,我在国外为苏联电影界赚到的钱,比一群邦达尔丘克加在一起都多……”

塔可夫斯基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电影界将塔可夫斯基视作苏联新浪潮电影的独子,推崇他、拥戴他、爱护他,塔可夫斯基所行之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1980年,意大利影人对塔可夫斯基一部极为重要的电影——《乡愁》施以援手,意大利国宝级编剧托尼诺·乔艾拉和塔可夫斯基共同创作该片的剧本。在他乡的日子里,托尼诺始终陪伴其左右,他们在罗马、米兰、都灵、那不勒斯等地采风,闲暇时在托尼诺的别墅露台上谈论诗歌、摄影和建筑艺术,并热情地回复影迷来信中的提问。另一位电影巨擘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得知塔可夫斯基在意大利本土后专程致电问候,邀请其探班自己的电影。这段旅居海外的创作经历美妙、纯粹,充满了来自同行的善意,它被全部拍摄下来,并被剪辑成一个小时的纪录片《旅途时光》,而托尼诺的诗作也从侧面印证了两位电影大师惺惺相惜的深厚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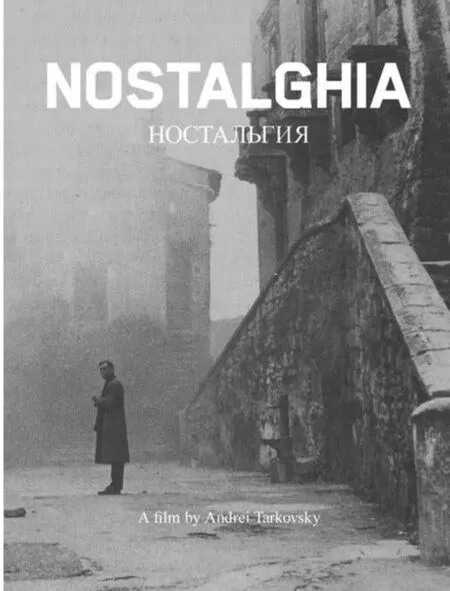
电影《乡愁》海报
我不知道房子是什么/是一件外套吗/或是雨天的一把伞/我用瓶子、抹布、木人、窗帘、扇子填满它/似乎我从未想要离开它/那么它是个笼子/监禁经过的任何人/甚至像你一样的一只鸟/飘雪的天气/但是我们互相所诉说的/是如此明亮/以致抑制不住
当然,创作上的愉悦并不能完全打消塔可夫斯基远在故土的忧虑:年仅11岁的小儿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滞留在国内,当局没有通过孩子的签证。直至1982年年底,妻子拉里莎才先行来到意大利与他会合。
《乡愁》制作完成后,在戛纳影展选片总监吉尔·雅各布的力邀下,塔可夫斯基参加了第3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乡愁》最终与金棕榈奖失之交臂,但它仍为塔可夫斯基赢得了主竞赛单元的最佳导演奖。

塔可夫斯基在电影拍摄现场
《乡愁》的观影体验就像在穿越一座迷宫,时间与空间任意绵延着,虚幻与真实也不再有任何界限,相互交叠在了一起。电影里的俄国诗人、女翻译、疯子站在各自命运的孤岛上,现实迫使他们无法更进一步。塔可夫斯基将无法自拔的思乡情怀和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全部投射其中。影片中,不被世人理解的疯子多米尼克即将自焚前出现了这样一句念白:“我们这时代再无伟大的大师留存,这正是真正的邪恶……”这句念白印证了塔可夫斯基对自己艺术创作命途多舛的无声控诉。现实中更为恶劣的是,戛纳电影节结束不久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以塔可夫斯基长期不在本土工作、无视纪律的理由解雇了他。
1984年夏,当留在国内的家人签证申请彻底无望后,身心俱疲的塔可夫斯基在米兰宣布不再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怎能预料,拍摄《乡愁》时,那种弥漫整个银幕的如鲠在喉的忧伤,会成为我余生的归宿?
我怎能想到,从今往后直至生命的尽头我都要承受着沉疴……
就这样,他成为了一个影像之外真实的流亡者。
时光不朽
昨晚我做了个很悲伤的梦。我又梦到俄国北方某处的湖泊;那是拂晓,远处的湖滨有两座东正教修道院,教堂和围墙异常美丽。我好悲伤!我好痛苦!
背井离乡后的塔可夫斯基奔走于伦敦、柏林、斯德哥尔摩多地,为未来的生活和创作积极寻求转机。他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制片人、出版商、政客、教授……甚至冰岛总统也给他发来了入籍邀请,但他的内心仍然充斥着苦闷和郁结,更多的是为孩子的无辜受苦而感到自责,为把孩子接回到自己的身边,他做出了各种努力与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牺牲》是塔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在瑞典电影界的支持下于1985年的春天开拍。影片拍摄期间,他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病痛严重折磨着他,他只能频繁地穿梭于片场和医院之间。幸有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老搭档——摄影师史文·纽克维斯特的帮助,影片在1986年年底得以拍摄完成。
在《牺牲》上映的前半个月,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技术灾难发生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产生的辐射量相当于400颗原子弹,整个欧洲都被笼罩在核污染的恐怖阴霾之中……巧合的是,《牺牲》所讲述的内容正是以全球性核毁灭为背景,主人公亚历山大通过向上帝献祭阻止核灾难发生的故事。
塔可夫斯基不是先知,没有刻意增添光影里任何不安的底色。肉体上的病痛,生活中的徘徊与不堪促使他更加清醒。在这部寓言般的作品中他耗尽了自己全部的能量,对影片中的人物灌注了真实而忧郁的情感。亚历山大似乎就是他的化身,不曾背叛豕突狼奔的土地,且以世人所不能理解和容忍的受难方式对抗人类即将到来的厄运,即使被抛弃和放弃,他仍然将坚实的爱和善回报给了人间,电影诗人的塔可夫斯基亦是如此。
1986年1月,塔可夫斯基的儿子安德烈终于获准离开苏联,他漂泊的家庭迎来了久违的团聚。同年5月19日,在第3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牺牲》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大奖。此时的塔可夫斯基,身体已经极为虚弱,这个奖项由小安德烈代其领取。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他在巴黎的一家诊所接受化疗,直至12月29日夜晚去世。
一周后,塔可夫斯基的葬礼在巴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举行,乐手们在葬礼上一曲接一曲地演奏着巴赫的曲子,告慰塔可夫斯基的灵魂,因为他生前坚信“能够把永恒献给上帝的只有巴赫一人”。
葬礼结束后,他被安葬于巴黎郊区圣热纳维耶芙-戴布瓦的俄罗斯人公墓。
追溯其一生,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旷世之才在苏联电影界似乎成为了一种令人敬畏的异彩,因而无法摆脱“被涂污的鸟”的宿命,但他最终穿越了现实的衣衫褴褛与历史的愁云密布,抵达了电影之诗的不朽本真。纵然时光荏苒,但对于观众而言,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依旧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精神掩体,它们的存在让脆弱的人类灵魂得以接受到光影圣堂最后的庇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