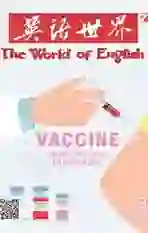这个人是谁
2020-10-09金圣华
金圣华
这个人是谁?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看起来似近而远、似亲犹疏、似熟还生?何以一个年轻女孩当年的一念一息、一举一动,竟会决定了今时今日的我毕生的命运?
面对着一大堆微微泛黄的书信,按照信封的邮戳一封封打开细看,一个尘封遥远的世界在记忆深处慢慢浮现出来,似塘中泛起的涟漪、窗外飘来的飞絮,一串串、一片片展示眼前,接连的惊喜,不断的追寻——这个人是我吗?她见过的人、欠过的情、尝过的乐、受过的苦、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为什么有的记忆犹新、有的遗忘殆尽?原来记忆真是不知不觉经过筛选的,在追忆所及星光灿烂的亮点之后,竟然还有这么一大片朦胧暗淡、没入忘乡的夜空!
这批信,是我1963年至1965年负笈美国时写给爸妈的家书。记得老爸老妈九十出头那年,他们住所还经过一次大装修,二老忙着清理杂物,把多余衣物送的送、丢的丢,旧信账单撕的撕、毁的毁。还以为我的信早已不知去向,谁知道他们去世后,在遗物中竟然发现这批信还整整齐齐原封不动地珍藏着。当时未及细看,就一大包拿回家来束之高阁。多年过去了,平日里忙忙碌碌,哪会有闲情去翻阅这些陈年旧函呢?
疫情肆虐期间,幽居斗室,百无聊赖,一日在家中东翻翻西看看,打开柜子,瞥见这批函件和爸妈的回邮,当下如获至宝,忍不住细阅起来。一开始,便停不了,那厚厚一迭信一封封追看下去,时光倒流,旧梦重温。霎那间,仿佛又回到了早已失落的国度,再次经历了青春时代的喜与忧、乐与怒、憧憬与期盼、忐忑与烦愁。
那年头风气使然,大学毕业了都想出国,然而出国留学谈何容易,那一大笔旅费学费生活费可难以对付。当年在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进入亚细亚石油公司工作,一年之后获得美国大学的助学金,就摒挡一切,执意上路了。
其实,那时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可靠的男友,原本可以留在香港,安享父母的庇佑、爱侣的守护,却不知是上进心强还是好胜心切,竟然宁愿抛开一切远涉重洋去只身闯天涯。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国可是件大事,事前父母努力打点张罗,筹备行装;临行亲朋戚友都赶到启德机场去送别。记得那天第一次坐飞机出远门,孤零零瘦削削一个,左手拿着打字机,右手挽着化妆箱(如今回想,这又要来何用?是为了女儿家出门以壮行色吗?),身上背着一个大手袋,腋下夹着一件呢大衣,浑身沉甸甸勉力往前行,还没走到机舱口,眼泪已经扑簌簌往下流。此去经年,那时候谁都不会隔三五个月就轻松回家度个假,也付不起昂贵费用打长途电话,倘若思家心切,唯有靠鸿雁往返万里传书了。
那批信,历时两年,一共有好几百封。原本自以为这辈子毫无理财观念,翻看旧函,才发现那时涉世未深的自己居然很会撙节用度,时常在信里提到省钱之道。也难怪,一开始,飘飘然来大学报到,老爸的说法在耳旁回荡:“你去金元王国(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念书,跟你的名字息息相关,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于是,一切似乎都染上了玫瑰金色的浪漫幻彩。没多久,却尝到了独立生活必须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的滋味了。带去的300美元,付了135元宿舍按金,加上每天的膳食费、日用品费、书籍文具及邮费,不出几天已经所剩无几。当时有个中国台湾来念化工系的女孩石,她出身富裕,性情开朗,兴冲冲指点我说:“在美国,身上是不必带钱的,钱都存在银行里,要用时开张支票就行了。”她竭力怂恿我像她一般去银行开个上千元存款的账户,我只好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转头把用剩的几十美元悄悄塞在枕头下,静待一个月后助学金出粮的时候。
留美两载,第一年住宿舍,为了学好英文,跟两个美国女孩同房。第二年,宿舍需要整修,也为了省钱,于是就跟两位中国台湾来的女孩——念化工的石和念卫生工程的廖,一起搬到学校附近的公寓居住。三个女生,同住一层楼,每逢月初,各放90美元在一个铁罐里,每星期上超市买菜,就从罐头里掏钱。上超市,当然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大事,在美国没有汽车是寸步难行的,所幸隔壁住了两位大姐黄与张,她们已经来美数年了,拥有一辆后座踩脚地方有个窟窿的老爷车,每次出行恰好带上我们这三个毛丫头,只要我们上车后小心翼翼不把脚伸到洞里去就行了。从超市回来,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当时我们住在三楼,要把战利品搬回公寓,重的牛奶、罐头之类由两位理工科高材生全力包办,轻的如纸张、胶布则由手无缚鸡之力的我拉扯上楼。
跟石、廖两位室友同住,一星期六天三人轮流做饭,每逢星期日,则因她们要去教堂礼拜,午饭甚至晚餐常由我独立操持。多年后,我们每逢長途电话聊天叙旧,她俩坚持不信我当年竟有此能耐,如今翻看旧信,才发现证据确凿,有书为凭。原本在家时,因老爸思想前卫,举措新潮,一向重女轻男;老妈则笃信女儿当自强,读书最要紧,从来不让我进厨房,不需我做家务。没想到来了美国,因生活所需,竟会不时凭记忆胡乱凑出四菜一汤,偶尔还够胆请老外来作客品尝。“拿手好菜是干烧明虾”,我在信里洋洋自得向父母吹嘘,并宣称日后回家要克尽孝道,为他们下厨分劳。话虽如此,学成返港之后又故态复萌,一头钻进教书工作,自此与厨房绝缘。多年后,自己儿女成长,绝不相信我能做菜,并时常调侃说,从小到大尝过老妈厨艺的次数,不用十根手指就数得完。
烹饪如是,缝纫又是另一个故事。中学时北一女的劳作,不论刺绣编织,都是妈妈代劳蒙混过关的。来了美国,发现饭堂里的牛奶一开笼头就哗啦啦溢出,任喝无妨,简直比香港的自来水还流得畅快,谁叫香港当时还在制水呢?于是,在那仍未崇尚唯瘦为美的时代,日饮鲜奶三杯,体重由初到美国的88磅暴升到102磅,带去衣裙都无法再穿,那11件旗袍更撑不下了。由于不舍得花钱,1964年暑假去科罗拉多打暑期工教中文时,除了把旧衣修改放大,居然还从圣路易斯公寓中带去旧窗帘一幅,请商教授夫人代为剪裁,自己亲力亲为缝了一件衣服!看到这封信的内容,除了马上想起《乱世佳人》中郝思嘉色诱白瑞德那经典一幕之外,不由得也大吃一惊!这个人难道是自己吗?不但如此,当年的我更曾大发宏愿,在课余到处向人讨教,千辛万苦完成了一件生平唯一手织的毛衣,献给妈妈当作生日礼物。多年后翻译《傅雷家书》和《海隅逐客》等名著时,译了又改,改了再译,十次八次,不厌其烦,那过程,每每使我想起当年在圣路易秘密练兵,悄悄为妈妈编织毛衣拆了又改、改了又拆的情景。
人的际遇,十分玄妙,当年若不是邂逅好友石与廖,我的留学生活不会如此单纯——每日里除了念书就是念书。我们同进同出,彼此扶持,不知道寂寞孤单为何物。当年的旅美学界,多的是各式各类的派对聚会,我们每次出席,都由张、黄两位大姐领队,她俩如母鸡守护小鸡般照看我们,晚饭一过,就五人同行,全身以退,连一次舞会都没有参加过。廖当年也已有固定男友在瑞士攻读,因此我们立意固守阵地、坚壁清野,不让任何诱惑近身。
两年过去,该是学成返港的时候了。亚洲学系的主任与教授竭力挽留,说是只要我点头,就可以让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独当一面当讲师,每年约有7000多美元薪水,这个优渥的待遇对别人来说可是求之不得,对我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但我当时去意已决,辜负了系方一番美意,让他们大失所望,觉得我不识好歹、不堪造就。那一批信里,充满了彷徨与忧虑、烦躁与不安,深恐因此得罪教授,拿不到硕士学位无功而返,白白让两年光阴化作东流水。
如今回想,当年的一个坚持、一个决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假如选择留下了,不知道是祸是福,多半会成为於梨华小说中另一个角色吧!(执笔至此,恰好传来这位早年旅美文学代言者在美染疫身亡的消息,令人唏嘘!)但是这个人绝不会是现在的我——一个和睦家庭里的受宠者、一个漫长译道上的拓荒人!
展信细阅,竟然看得累眼昏花了,那批信当年是写给爸妈的,为什么毫不体恤,为了省点邮费,写的都是蝇头小字?转念一想,以年龄来说,那时的爸妈,比起我现在的子女,也实在大不了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