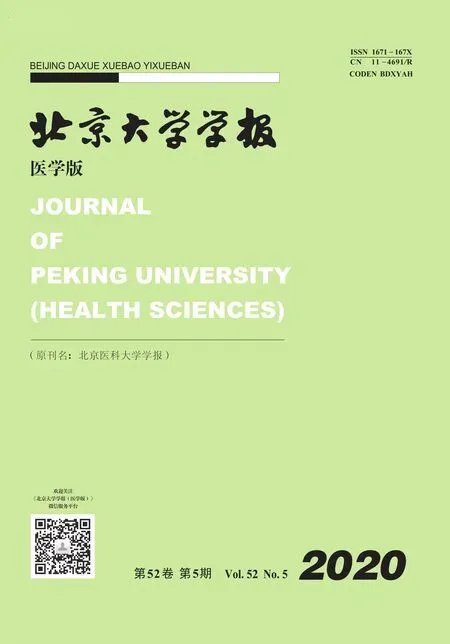3例肾尤文肉瘤合并下腔静脉癌栓的诊治
2020-10-09马潞林张树栋张洪宪
毕 海,黄 毅△,马潞林,陆 敏,张树栋,张洪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 泌尿外科,2. 病理科,北京 100191)
尤文肉瘤肿瘤家族(Ewing’s sarcoma family of tumors, ESFT)是一种少见、生长迅速的小圆形细胞恶性肿瘤,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其中,骨外尤文肉瘤(extra-osseous Ewing’s sarcoma, EES)约占ESFT的6%[1-2]。基于相似的形态学、超微结构以及染色体变异,EES被认为是骨尤文肉瘤的特殊表现形式。EES好发于四肢、躯干、头颈部软组织以及后腹膜腔,发生于实质性脏器的EES十分少见,通常采用骨尤文肉瘤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3-4]。该病具有较高的侵袭性,预后较差,且术前诊断率很低,关于EES的报道不多,原发于肾脏伴有下腔静脉癌栓的EES更是极为罕见,国内外报道的合并下腔静脉癌栓的肾尤文肉瘤尚不足10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收治了3例肾尤文肉瘤合并下腔静脉癌栓的患者,均成功行根治性切除,现结合既往文献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1:患者女性,16岁,主因“右侧腰背部疼痛半年,复发加重半月”来我院就诊。外院CT检查考虑右肾占位性病变,肾母细胞瘤可能性大。患者自发病以来,大小便正常,体质量无明显变化,既往体健。
病例2:患者女性,18岁,主因“右侧腰部酸胀伴间歇无痛全程肉眼血尿2周”来我院就诊。外院检查考虑右肾肿瘤。近一周患者未再出现血尿,大便无异常,体质量较前稍有减轻,既往有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18年。
病例3:患者女性,24岁,主因“右腰腹部疼痛2天,活动时加重”来我院就诊。外院检查提示右肾占位。近期大小便如常,体质量无明显变化,既往阑尾切除术后5年。
1.2 影像学检查
病例1:腹部MRI增强提示:右肾中下部破坏,可见团块状肿物影,信号不均匀,大小约14.0 cm×10.8 cm×16.3 cm,边缘尚清晰,增强扫描见不均匀强化,右肾盏受压积水,周围组织受压推移,右肾静脉明显受压,显影不清,下腔静脉内见软组织肿块,增强扫描可见强化,上缘位于肝下缘(图1)。诊断:右肾癌,病理类型待定,下腔静脉Ⅱ级癌栓形成。
病例2:腹部增强CT提示:右肾中下部可见团块状混杂密度影,以等密度、稍低密度影为主,可见点状高密度影,病变大小约6.9 cm×8.1 cm,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强化,强化程度低于临近肾实质,动脉期病变内可见多发小血管影,静脉期可见瘤栓沿着右肾静脉延伸至下腔静脉内,癌栓上端位于肝后,病变向肾窦内生长,右侧下部肾盂肾盏未见显影,上部肾盂肾盏扩张积水(图2)。诊断:右肾癌,病理类型待定,下腔静脉Ⅱ级癌栓形成,侵及临近肾盂肾盏。
病例3:腹部增强CT提示:右肾见巨大囊实性软组织占位性病变,大小约15.1 cm×16.5 cm×13.8 cm,其内密度混杂,可见实性成分、液性密度和少许出血,病变有包膜,边界清晰,其内可见分房或分隔,部分分隔可疑少许钙化,增强扫描见病变实性成分轻度强化,液性成分无强化,其内分隔可见强化,下腔静脉明显受压变窄移位,右肾静脉显示不清,右肾静脉于下腔静脉开口处可见静脉瘤栓(图3)。诊断:右肾癌,病理性质待定,下腔静脉Ⅰ级癌栓形成。
1.3 手术方式
病例1:因肿物巨大,行开放右侧肾癌根治及癌栓取出术。患者平卧位,采用右侧肋缘下切口,将右半结肠及十二指肠推向左侧,游离并显露肾门及下腔静脉,游离出右肾静脉,其内可触及质硬瘤栓,于其背侧游离出肾动脉,多重结扎后将肾动脉切断。于右肾静脉水平下方无癌栓处游离下腔静脉预备阻断,于右肾静脉水平下腔静脉左侧游离出左肾静脉预备阻断。沿下腔静脉向上游离至第一肝门处,结扎切断数支肝短静脉,游离癌栓上方下腔静脉预备阻断。将需要阻断的下腔静脉的属支尽量结扎完全,包括腰静脉、生殖腺静脉及肾上腺静脉。先后阻断下腔静脉远端、左肾静脉、下腔静脉近端,剖开下腔静脉,将右侧肾连同腔静脉瘤栓完全切除。以肝素盐水冲洗腔静脉管壁,4-0血管缝线连续缝合下腔静脉,然后依下腔静脉远端、左肾静脉、下腔静脉近端顺序解除阻断。手术时间517 min,出血量650 mL,输血400 mL。
病例2:因肿物大小适中,考虑尝试后腹腔镜右肾根治性切除及下腔静脉瘤栓取出术。患者麻醉后取左侧卧位,建立后腹腔空间,先游离出肾动脉,上三重Hem-o-lok夹闭后切断。因肾门淋巴组织较多,渗血明显,控制肾动脉后好转。按照开放Ⅱ级癌栓处理方式处理下腔静脉各个属支,游离出癌栓上方的下腔静脉、癌栓下方的下腔静脉及左肾静脉。下腔静脉采用自制下腔静脉阻断带(输血器皮管)阻断,左肾静脉使用血管阻断钳阻断。先后阻断下腔静脉远端、左肾静脉、下腔静脉近端,剖开下腔静脉,将右侧肾连同腔静脉瘤栓完全切除。手术时间278 min,出血量200 mL。
病例3:因肿物巨大,行开放右肾根治性切除及下腔静脉癌栓取出术。患者平卧位,右侧肋缘下切口,因肿瘤巨大,于肾内侧显露肾门及下腔静脉困难。游离肾脏背侧和肾下极,从肾下极内侧找到下腔静脉,紧贴下腔静脉游离肾脏,于肾门处找到一支肾动脉,三重结扎后切断,于动脉上方找到肾静脉,肾静脉较粗,探查下腔静脉,下腔静脉内肾门部可触及瘤栓,从肾静脉开口向近心端延伸,用侧壁钳部分阻断下腔静脉,切开下腔静脉,切除部分下腔静脉壁,将瘤栓完整取出,用4-0血管缝线连续双层缝合下腔静脉开口。手术时间364 min,出血量200 mL。
2 结果
病例1:病理结果提示:右侧肾癌,小圆细胞恶性肿瘤,倾向于Ewing肉瘤/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PNET), 大小17 cm×12 cm×9 cm,肿瘤组织侵犯肾盂及肾窦,伴肾/腔静脉瘤栓形成,大小10.0 cm×2.6 cm×1.2 cm。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CD99(弱+)、Fli-1(弱+)、WT-1(-)、Vimentin(+)、CK混(-)、S100(-)、NeuN(-)、CgA(-)、Syn(+)、CD56(+)、CD117(-)。经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检测确诊(图4)。患者目前术后5个月,未采用辅助治疗,术后3个月随访时未见明显肿瘤复发及转移表现。
病例2:病理结果提示:肾尤文肉瘤,大小 7.5 cm×5.5 cm×3.5 cm,肿瘤未侵及肾周脂肪组织,但累及肾窦,肾静脉及下腔静脉瘤栓送检组织为肿瘤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CD20(-)、CD3(-)、CD99(+)、TdT(-)、FLI-1(+)、Ki-67(30%+)、CK混(-)、EMA(-)。患者术后未采取辅助治疗,发生肺转移,术后1年去世。
病例3:病理结果提示:右肾尤文肉瘤/PNET,肿瘤大小约为13 cm×10 cm×9 cm,侵及肾盂及输尿管,输尿管断端未见肿瘤。腔静脉瘤栓为肿瘤性栓子,形态同肾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CD99(++)、NSE(少数细胞+)、WT-1(少数细胞弱+)、Syn(-)、CgA(±)、CD10(-)、CK混(-)。患者术后2个月入化疗科行辅助化疗,具体为:4周期VAC方案:长春新碱2 mg D1(D: day),表柔比星60 mg D1,70 mg D2,环磷酰胺1.7 g D1;序贯两周期IE方案:异环磷酰胺2 g D1~5,VP-16 100 mg D1~5。术后连续随访3年半,未见明确复发转移表现。
3 讨论
EES是一种少见、生长迅速的小圆形细胞恶性肿瘤,可发生于任何部位的软组织,侵袭性高,预后较差,其中,肾尤文肉瘤更为罕见。截至2016年,关于肾尤文肉瘤的报告不足150例[5]。肾尤文肉瘤好发于20~30岁的青壮年群体,男女比例为3 ∶1[6]。本组病例年龄为16~24岁,均为女性,虽与文献报道不太一致,但患者均存在下腔静脉癌栓,不除外女性为肿瘤侵袭性高的危险因素。
EES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目前认为EES的发生与EWSR1基因以及ET家族转录因子有关,如FLI1、ERG、ETV1、ETV4以及FEV等[7]。位于22q12的EWS基因分别与位于11q24的FLI1基因以及位于21q22的ERG基因发生易位,可形成EWS-ERG和EWS-FLI1融合基因,导致广泛的转录调控机制异常,诱导EES的发生。Yang等[8]的研究显示,90%以上的肾尤文肉瘤患者存在t(11;22)(q24;q12)染色体易位。EES的临床症状不具特异性,常表现为生长迅速的深部软组织肿块以及发病部位的疼痛和功能障碍,但患者在早期可以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晚期患者常有因肿瘤压迫引发的软组织疼痛以及肿胀感,同时可能伴有因压迫引起的相应症状(发生在神经旁的肿瘤通常会引起肢体感觉运动障碍),因此,EES的早期确诊率极低。本组病例均以腰背部疼痛为主诉,但病例2存在无痛性血尿,考虑与肿瘤侵袭肾盂有关,患者就诊时存在体质量下降,术后1年因肿瘤广泛转移去世,考虑血尿及体质量下降为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EES影像学检查常表现为肾内单发性软组织肿块,CT平扫为体积较大肿物,与肾实质分界欠清,其内可呈混杂密度,无钙化,增强后有不同程度强化;MRI在T1W1多呈等或低信号,T2W1无特异性表现,可呈混杂信号,因与肾细胞癌影像学表现相似,常误诊为肾细胞癌,确诊仍需组织病理检查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查[9]。值得一提的是,尤文肉瘤的动脉血供弱于肾透明细胞癌,且尤文肉瘤的癌栓内部血供也不丰富,CT及MRI增强程度较弱,可能作为一个鉴别点。本组病例的影像学表现均为不均一混杂强化,但强化程度均不明显,考虑并非肾透明细胞癌。这一点的提示主要在于尤文肉瘤的癌栓相对松散,如豆腐渣样,而透明细胞癌的癌栓相对结实,脱落风险较低,所以术前在看到类似影像学时,需要在术中小心操作,避免发生癌栓脱落。同时,影像学检查也可以帮助确定EES肿瘤的大小、位置、边缘情况及肿瘤周围的结构关系,同时判定瘤栓的级别及与下腔静脉壁的关系,从而帮助手术的实施。
因为影像学表现没有特异性,所以EES的确诊以及术后治疗方案的选择更依赖于组织病理学诊断。EES的组织病理学特点包括:(1)瘤细胞内存在大量的糖原;(2)缺乏致密核心颗粒——神经内分泌颗粒,细胞神经性突起及神经微管结构少见;(3)菊形团坏死是尤文肉瘤常见的病理学形态,但大多数的EES在镜下无菊形团结构;(4)HE染色均为蓝色小圆细胞;(5)绝大多数患者均表达血红蛋白A71 (HbA71),即CD99(+),Vimentin及S100蛋白在52%~70%的患者中呈阳性[10]。此外,EWS/FLI1融合蛋白的检测也是诊断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EES仍然缺乏典型的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除EES外,其他小圆细胞肿瘤(如肾母细胞瘤、滑膜肉瘤、淋巴瘤)也可表达CD99,因此需要其他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辅助诊断,如CD45可以辅助鉴别大多数淋巴瘤,WT-1可辅助鉴别肾母细胞瘤等。在分子诊断方法的选择上,有研究比较了FISH与逆转录PCR(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T-PCR)反应检测染色体易位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发现FISH检测的敏感性和稳定性均要优于RT-PCR检测,与CD99联合应用时,具有更佳的临床诊断价值。在缺乏FISH和RT-PCR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免疫组织化学抗体FLI1、CD99联合应用也可以提高诊断的特异性[11]。本组的病例1、病例2进行了CD99、FLI1联合检测,其中病例2的CD99、FLI1均为强阳性,因此未做FISH检测,病例1的CD99、FLI1均为弱阳性,进一步行FISH检测确诊。病例3仅CD99强阳性且并未进行FISH检测,可建议此类患者进行FISH检测,增加检测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以指导后续治疗。
由于EES的发病率极低,目前仍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案,首要的治疗方案仍然是手术切除。以往文献报道显示,接受手术治疗的肾尤文肉瘤患者的2年生存率可达80%,而未接受手术治疗患者的2年生存率仅为30% (P=0.02)[12]。肾尤文肉瘤手术术式的选择与肿瘤大小密切相关,当肿瘤负荷较大,直径大于10.0 cm时,腹腔镜手术难度较大,难以操作,一般选取开放手术[12]。同时,是否合并癌栓以及癌栓等级也是影响手术方式的重要因素。对于Ⅰ、Ⅱ级癌栓,腹腔镜手术依然是可考虑的治疗策略,但依赖于术者的经验和肿瘤的大小[13]。本组病例2的肿瘤大小为8.1 cm,为Ⅱ级癌栓,采用腹腔镜治疗,手术过程顺利,但术中粘连较重,手术难度高,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手术医生操作。对于Ⅰ、Ⅱ级癌栓,手术切口的选择建议采用平卧位,肋缘下切口,能提供更好的术野,更利于处理癌栓[14]。本组的病例1及病例3均采用平卧位肋缘下切口,对于癌栓的处理更方便。本中心的经验显示,尤文肉瘤的癌栓如同豆腐渣样,质地松散,容易脱落;肾透明细胞癌的癌栓为金黄色,质地中等,脱落风险较低,即使发生肉瘤样变,癌栓性状变化也不大;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癌栓质地偏硬,脱落风险更小。因此,对于合并癌栓的尤文肉瘤患者,术中需要小心操作,避免大幅度挤压触碰癌栓,减少脱落风险。除此之外,尤文肉瘤的癌栓操作与普通肾癌的处理模式相同:对于Ⅰ级癌栓,我们一般采用侧壁钳阻断的方式,免除了阻断下腔静脉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对于Ⅱ级癌栓,我们需要将癌栓上下方的下腔静脉及对侧肾静脉完全游离,结扎其所有属支,按顺序依次阻断癌栓下方腔静脉、对侧肾静脉及癌栓上方腔静脉,在完整切除癌栓、缝合腔静脉切口后,再按此顺序依次解除阻断。对于腹腔镜下治疗Ⅱ级癌栓,本中心采用输血器裁剪后作为下腔静脉阻断带,在达到相同临床效果的同时极大节约了成本,使腹腔镜手术治疗癌栓成为可能。
虽然EES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案,但其与骨尤文肉瘤具有相同的生物学行为,对化疗较敏感,绝大部分学者推荐局部广泛切除术结合术后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常见的化疗药物包括阿霉素、长春新碱、环磷酰胺、异环磷酰胺以及依托泊苷[15]。未采取辅助化疗时,肾尤文肉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足10%。应用辅助化疗的肾尤文肉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达45%~55%[16]。对于未进行手术治疗的肾尤文肉瘤患者,接受化疗者的1年生存率也高于未接受化疗者(93%vs. 75%,P=0.92)[12]。此外,对于组织病理证实淋巴结转移的肾尤文肉瘤患者,术后采用放疗体现出一定的优势,但仍不推荐作为首要治疗方式。
尽管采取了积极的治疗方案,肾尤文肉瘤患者的预后仍不尽人意,中位总生存期仅为26.5个月[12]。此外,有研究者总结了23例肾尤文肉瘤患者的治疗结果,发现尽管经过积极的辅助化疗,有随访记录的18例患者均出现了转移,其中肺转移12例,骨转移6例[17]。除肺转移和骨转移外,肾尤文肉瘤患者的常见转移部位还包括肝以及淋巴结转移[18]。如何降低肾尤文肉瘤患者术后转移的概率仍是临床工作中的难点。本文报道的3例患者中,有1例手术后行VAC 4周期序贯IE 2周期辅助化疗方案。化疗期间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有Ⅱ度消化道反应和Ⅲ度骨髓抑制,经对症处理后均缓解。术后连续随访3年半,未见明确复发转移表现,患者无病生存期超过3年半,疗效满意。另外2例患者因担心化疗的副反应以及影响生育等问题,不愿意接受辅助化疗。1例未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发生肺转移,术后1年去世,另1例随访时间仅为5个月,目前依然无复发转移表现。虽然个案不具备代表性,但结合国内外文献报道,仍建议患者接受术后辅助化疗。
综上,肾尤文肉瘤是一种十分罕见并且致命的肿瘤,好发于20~30岁青壮年群体,晚期患者常伴广泛的肾外侵犯及转移。该患者群体整体预后不佳,准确诊断和综合治疗手段仍是提高患者远期获益的重要基础,因此,肾尤文肉瘤一定要与肾脏的其他小圆形细胞肿瘤加以区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综合组织病理学、组织形态学、分子/基因测试得到的结果。肾尤文肉瘤合并下腔静脉癌栓的报道更少,在术前评估时应加以重视,手术方式的选择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此类患者推荐进行术后辅助化疗,以期提高患者的远期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