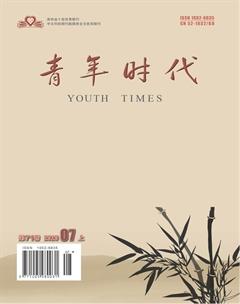抛却偏见自由心
2020-09-29高子璇
高子璇
摘 要:柳永作为北宋前期的一个重要词人,一直以来都被学者关注和研究,其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将羁旅行役、都市生活、市井女子等都纳入到了词中。而这一点也反映出了柳永词所具有的一种“抛却偏见”的精神特质,具体分为三种:女性偏见、悲喜偏见和俗雅偏见,其间亦有相通之处。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将多种生活纳入词中,开拓了宋词的题材,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
关键词:柳永词;抛却偏见;北宋社会
北宋社会在历史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它积贫积弱、武力衰微,却又安定和谐、经济繁荣。宋词便是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式,柳永作为北宋第一个专注于写词的作家,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他的词中所具有的那种“抛弃偏见”的精神特征,更是在现代社会也具有先进意义的特质。
一、“抛却偏见”
“偏见”一词,可简单理解为人们带着主观情感论人就事,具有主观臆断的特点,映射在社会上,也可理解为一种固有观念。很多文人奉行“诗庄词媚”,排斥柳永的俗词,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其深受儒家伦理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偏见”。柳永的词之所以能能够表现出广大的社会,开拓出词题材的新领域,部分原因正是柳永的词带有一种“抛却偏见”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对固有观念的突破,应该说是当时的北宋社会和柳永自己共同促进了这种特征的形成。
二、柳永词的“抛却偏见”
(一)女性偏见
这应该是柳永词中“抛却偏见”的精神特征里最重要的一点,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歌妓偏见,其二是妇女偏见。二者虽然同属于女性,但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当时,歌妓属于社会贱民,是供上层社会取乐的工具,北宋社会“狎妓”之风盛行,甚至形成了专门的歌妓制度,所以对歌妓的偏见应该属于一种阶级偏见;而妇女则不同,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形成了很多针对女子的无聊教条,以“三从四德”为代表,认为妇女就必须溫柔贤惠,所以这种对女性的偏见属于一种性别偏见。在柳永的词中,这两种偏见都被很好地抛弃了。
(二)歌妓偏见
北宋社会经济发达,“狎妓”之风盛行,妓馆也随之增多,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如相国寺南录事巷,寺北小甜水巷,景德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馆”。北宋的歌妓制度将歌妓分为三类,即官妓、家妓和私妓,其中私妓是市井勾栏之中最普遍低贱的一种,而柳永接触最多的也是这类歌妓,他的很多作品都与这类歌妓有关。
他珍惜旧日相熟的歌妓寄来的书信,“更宝若珠玑,置之怀袖时时看”(《凤衔杯》);他会与歌妓言“况已断、香云为盟誓。且相将、共乐平生,未肯轻分连理”(《尉迟杯》);他会在羁旅时怀念曾“剪香云为约”(《尾犯》)的歌妓,为自己“别后寡信轻诺”的行为心怀愧疚;他也会为歌妓的香消玉殒而感叹怀伤,叹“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秋蕊香引》)。最为典型的一曲词作,应该是柳永的《迷仙引》,他用一位歌妓的视角,向信任的男子倾诉,将自己不幸的命运和对生活的向往娓娓道来,言语真挚感人,没有任何的轻视,只因他“深知她们的痛苦并真正同情她们”。
这其实是难能可贵的,毕竟在当时的社会中,又有哪个文人士大夫会真的将底层的歌妓放在心上,不可能体会她们的悲凉,更不可能与她们许什么地老天荒,为自己辜负或抛弃了她们而自责,甚至为一个普通歌妓的逝去而悲悯。
柳永长期沉沦下僚,又因为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鼓励大臣多置田产和歌儿舞女之后,纵情享乐成为风尚,随后由于经济的发展,享乐之风蔓及整个社会,从统治阶级到新兴市民无不有享乐的需要,柳永与歌妓接触的机会也随之增多,为她们填词作曲并真正了解了她们的生活,“没有将她们视为低贱的附属于青楼的玩物,而且与她们交情颇深,颇能理解她们的处境,能够看到她们灵魂深处的美好”。
(三)妇女偏见
柳永词中有很多以市井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女子大胆、泼辣、直白,与封建上层社会的审美标准格格不入,但落在柳永笔下,她们无一不是可爱的。除了柳永本身自由天真的个性之外,北宋经济发展,促进市民意识觉醒,市井女子的自主意识开始萌发,也是柳永能够写出这样作品的重要原因。
《锦堂春》中,女子对于晚归的丈夫,暗打算“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秋夜月》中,女子与情人重逢,也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只道“待信真个,恁别无萦绊。不免收心,共伊长远”。尤其是一曲《定风波》(自春来),还惹得晏殊排挤,只因其中“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等句。
在这些深受封建礼教影响而饱存偏见的封建士大夫眼中,这类女子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审美,忤逆夫君,甚至不让他们追求功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但这是市井女子最真实的状态。柳永用他“抛却偏见”的笔写下这些女子的故事,描摹出这些女子的形态,无一不带着张扬的可爱与自信。
在有的解读作品中,将柳永上述很多词都解析为写给妻子的作品,意图体现他的深情,但笔者认为这反而是降低了柳永的格调,真的只剩下儿女情长了。
(四)悲喜偏见
所谓悲喜偏见在此是指文人士大夫对某一题材悲喜因素的固定观念,比如说到清明节就应该是祭奠亡人的伤感日子、说到七夕往往是悲叹恋人两地分离,秋天就悲伤,冬天就肃杀。唐代刘禹锡的《秋词》中“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之句其实也属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悲喜偏见。而柳永的词中,也有不少相通的作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柳永所处的时代真正是北宋的盛世,政治升平、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加上市民阶层兴起,柳永本身也是采用了一种民间的视角,在百姓的眼中没有那么多伤春悲秋,所以对于文人认为悲伤的题材也少了那么些许感伤,反而热闹非凡。以一曲《木兰花慢》为例: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
这首词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清明景象,杏花桃花争奇斗艳,人们倾城踏青,充满了热闹的欢愉,正是盛世之下百姓的生活,与文人眼中感伤的清明是完全不同的。此外还有《二郎神》(炎光谢)、《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都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文人所展示的热闹画面。
(五)俗雅偏见
俗雅偏见中俗雅的概念是针对文人士大夫的标准而言的,柳永的俗词之所以不被上层文人所接受,很大程度就是因為这些文人心中的“俗雅偏见”。除了词的语言和表现手法通俗之外,这些俗词所表现的内容题材也大多是具有“俗”的特质的,对于上层文人而言是其不愿意,或者说是不屑于表现书写的内容。比如柳永的《木兰花令》:
“有个人人真攀羡,问着洋洋回却面。你若无意向他人,为甚梦中频梦见? 不如闻早还却愿,免使牵人虚魂乱。风流肠肚不坚牢,只恐被伊牵引断。”
这首词写的是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男子对女子一见钟情,而女子却故作冷淡,男子因此笑问如果她真无意,为什么还老与他在梦中相见呢?表达了一种相思爱慕之情,更像是市井男女一种真率的情趣,被柳永写来,让人觉得真实而可爱。不过这种行为在上层文人的眼中应该类似于“登徒子”,不受待见也是理所当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俗雅偏见与上面提到的女性偏见和悲喜偏见是有交叉的,主要集中在柳永表现的那些市井生活上。柳永之所以能够首当其冲地抛却这种俗雅偏见,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北宋市民阶层的崛起,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柳永本来就是生活在市井之中的人,他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些内容,而他天真自由的真实个性又如实地将其记录下来了而已。
三、结语
范镇曾感叹“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宦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柳永虽然终生仕途不顺,却依旧写下了北宋的盛世荣光,用他“抛却偏见”的清澈双眸看尽了人间风光,留下了无数至今仍为人传唱的佳作。然而在他踏入仕途之后,他终于还是收敛起了那一身天真的自由,即使是他曾经深爱的风月红尘,也只选择了遥遥相望,“墙头马上,漫迟留、难写深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自由人敛了自由心,但他曾经抛却世俗偏见写下的无数词作,仿佛能穿透古今,让所有心怀偏见的人都为之愧疚。
参考文献:
[1]李濛.《清明上河图》里的北宋商业社会[J].光彩,2016(2):66-67.
[2]王丹.柳永评传[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8.
[3]谢桃坊.柳永词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孟斜阳.柳永:红袖翩跹,只为你泪尽而舞[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
[6]乐芳.北宋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柳永词研究[D].汉中:陕西理工学院,2010.
[7]王静.从《东京梦华录》看北宋社会的奢侈消费[J].科技创新导报,2014,11(29):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