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许达然,用文学呐喊
2020-09-26徐学
徐学
1986年,在深圳举办的全国第三届台港文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许达然。此前我已经听说过他,那时“台湾研究”在台湾还是非常忌讳的行为,他却在芝加哥举办和主持了好几届“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广邀学者。我们学院研究台湾历史的教授也受邀参会。会议间隙,许达然还带我的同事登上威尔斯楼(当时的世界最高楼)。同事说,他是顶级历史学者,能够结合马克思的学说与当代西方哲学研究历史,史学之外旁及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可会上的许达然并不显眼,宴席上总是安静听讲。听到我用闽南语说话,他问:“台湾南部很多人是从泉州府渡海而来,为什么说话却是漳州腔?”我答应他,回校后去请教闽南方言专家。
坐拥孤独城
许达然出身台南农家,记忆里总有童年这一幕:农闲时,父亲用牛车拉个小炉子到城里去卖小吃,母亲带着他捡些柴火挖点野菜。他天生敏感,“参加联欢,轮到表演时,会发抖;看电影,尽可能拖到开场后才进场;坐公共汽车,挤在陌生的面孔中,如入刑场”。虽然羞怯,内心却丰盈,他赞咏紫罗兰:“固执地不在白天绽放,只在黑暗时默默地害羞,默默地祝福别人,默默地闪烁贞洁。”其中的几分是自喻。他家祖上没出过读书人,但他从小嗜书如命,课余时间都交给图书馆,读遍了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读了许多英文原版书,代价是小学就高度近视。为了买书,他努力挣稿费,初中就开始投稿,除了翻译外国文学,也写散文。大三那年,他出版了散文集《含泪的微笑》,畅销一时,几十年后台湾的朋友见到他还都提起这本书。他爱历史,以第一志愿考上东海大学历史系。那时东海大学是港台新儒家的重镇,老师有徐复观,学弟有杨牧、蒋勋。
大学暑假时,朋友问他准备如何消遣,他说去图书馆。“图书馆,你在那里不感到寂寞吗?”他说:“不会,我在那里建了一座城。那是以书架为支柱以书本为砖石的孤独城,我在里面既忙碌又悠闲。”
后来,学校图书也填不滿他的求知欲,假期又到台北中央研究院看书,附近没有旅馆,他就找到一间草寮安身,不顾身边毒蛇四窜,在那里睡了两个月。大学毕业时,他以骄人成绩留校任教,三年后又申请到哈佛的奖学金,从哈佛到芝加哥再到牛津,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29岁,他便在美国大学任教,多年来在美国各大图书馆、台北故宫和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两年整个暑假都在北京查阅古籍)勘阅旧档,爬梳整理,著述皆有独家见解。他熟练掌握英、法、日多种外语,很多论文都是先用英文发表,然后国内刊物翻译成中文。我们台湾研究院的《台湾研究集刊》就发表过好几篇他的论文中译,一篇不到两万字的论文,注释竟达上百条。
静静地声音很大
熟悉许达然的人会叫他“省话一哥”,公开场合他总是惜字如金。曾见媒体采访他,问:“你的代表作是什么?”答:“都不太满意。”问:“你的写作秘诀和要点是什么?”答:“努力写就是了。”遂沉默不语,采访只能结束。许达然不在乎学界或者批评家是否关注他的作品,很少参加文人聚会。有一次,他的诗歌得了某文学大奖,文学新秀慕名前去采访,他却严肃地说:“现在奖太多了。奖,其实是一种社会控制。”
那次在深圳,他喝了啤酒,话似乎多了些,但对谈中,他依然会不时陷入沉思。等待的片刻里,我忽然觉得这简约话语中的停顿和沉吟,如同写意画的空白,大有韵味。
许达然没有一般学者常有的高傲,他说,“世界并非自己的桌子而是大家的人间,人间迄今我虽仍不甚了解,还是写了。”因宁静淡泊,他的诗文如同他的话语,尽量精简,一字多用或谐音引申,努力开发汉字最大隐喻功效,不少读者感到艰涩拗口,知音却非常喜欢。虽然他惜墨惜言,声音却犹如呐喊,评论家早就指出,他有鲁迅般的锋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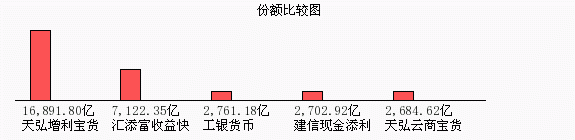
左图:1984年,许达然(左)在台中文化中心。右图:许达然在家中。
大四期间,许达然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知识分子应该为底层人民为社会理想奋斗的思想震撼了年轻的心灵。从那时起,他暗暗认定自己是左翼作家。多年后,他说:“左翼的定义是为人民说话,所有的作家都应该是左翼。”他用四个谐音词“感到、赶到、敢到、赶盗”阐明自己的创作观:“感到”是要有感而发,“赶到”是迅速捕捉现场,“敢到”是敢于干预到位,“赶盗”是驱逐黑势力。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他自成风景,以人道关怀与风花雪月型写作者分庭抗礼。
许达然以悲伤的目光,看着周遭麻木的人物和世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笔下有被压迫和侮辱的人群:牢狱里的政治犯、东门城下的摊贩、被强制拆屋的住户、垃圾堆中的人生……还有日益凋零的自然生态:废气污染下枯黄的木麻黄,被铁链紧锁的猴子,被绑赴刑场的猪,终身被牢笼缰锁的牛,甚至是被幽禁在抽屉却怀念风日阳光的砚石、一片被迫夹在厚重书页中的红叶……他有诗人的热肠,更有历史哲学家的冷面,他鄙视那些“把残酷的现实当笼鸟玩弄”的文字,小确幸看不见的残酷,他都能看见。他在意象的选择与营造中渗入自己对人生、社会、历史的理性认识。他说,“艺术的手段,是要使事物陌生起来,以便延长感知的困难和时间,而从中获得美。”他学习中国古诗炼字,特别擅长寓言式的隐喻。他曾自白“写作很痛苦,只因不愿仅写感觉,那些讨人欢喜的文字”。
许达然出版了17本文集和1本诗集,还有许多未结集的作品,有的被编入台湾的高中课本,还被译成英、法、德、日、韩等多种文字。有人对他不以为然,碎片化年代,谁会有心思读这拗口的文章?但许达然的文字整整流传了50年,影响了吴晟、陈列、阿盛等许多台湾作家,他们都把他视为乡土文学的先驱。1992年,在我两本文学研究专著里,我也把他定位为“把乡土放在中西文化中加以述说”的作家。
在异邦,用筷子,怎样夹都不是家乡味;思想起,怎样卧都不像长城;捧唐诗,怎样吟都不成黄河……然而身在国外嚷叫心爱国内,口再响亮头顶的仍是别人的天空。
土是肤色,也是归宿
许达然确实是依恋乡土,乡土对于他“是离开后,偶尔忆起的浓甘薯香;是流浪中,时常遇见的人情味;后来是泥泞思路上,一踏就滑倒的激情;再后来是拥抱祖乡的意识”。他写道:“在异邦,用筷子,怎样夹都不是家乡味;思想起,怎样卧都不像长城;捧唐诗,怎样吟都不成黄河……然而身在国外嚷叫心爱国内,口再响亮头顶的仍是别人的天空。”他的名篇是《土》,文章从童年记忆写起,出门就是一条蜿蜒伸进草地的土路,进门就靠着家里的泥巴土墙。
他常常回忆和书写母校东海大学。那是台湾最美的大学,有如唐宋禅院般的百年校舍,山边整排整排的相思树遒劲地伸出枝杈展开碧绿,含蓄夹带些淡黄婉约地排在一起。青年时期的他,总在树下胡思乱想一些与学业不相干的事。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回母校演讲开会,也客座一两年,还代理过历史系主任。

许达然作品《含泪的微笑》《为众生的悲心》。
青年时期,他面向西方,书架上一架都是英文传记,大学学位论文是《法英美三国拿破仑传记比较研究》,以英语撰写。那时,他读《雪莱全集》并译出其中许多篇章,但他没看过《红楼梦》。到了美国,他奋力弥补遗憾,他说,就是穿西式的鞋子也要走出自己的步履,他的学术方向从西洋史转移到汉人台湾开拓史,努力在泛黄的纸卷里寻找古朴文化的生命力,并发而为诗文。
他的诗虽短但凝缩着台湾社会变迁的轨迹,比如这首《车》:“阿祖的两轮前是阿公/拖载日本仔/拖不掉侮辱/倒在血池//阿公的两轮后是阿妈/推卖热甘薯/推不离艰苦 /倒在半路//阿爸的三轮车上是阿爸/赶忙敢忙/踏不出希望/倒在街上//别人的四轮上是我啦/敢快赶快/驶不开惊险/活争时间。”从日据时代写到今天,整整汉家四代人,是一卷台湾平民挣扎生存的历史。
為了让自己的文字走入平民心中,他努力在诗文中利用闽南方言词汇:太太是“牵手”,渔家是“讨海人”,一件衣服是“一领衫”,还有“亭仔脚”(骑楼)、“铁齿”(嘴硬)、“黑白讲”(胡说)。他并非方言至上的作家,选择那些“雅得可爱,俗得可亲”的方言词汇,让不懂闽南语的读者也能品出其中的乡土气息。
许达然曾说,是卑微质朴又沉默执拗的土塑造了他,“土成了我的肤色”。他对自己说,“不知已越过世纪,不知祖先墓冢的草已长得比你还高,只知自己老了。你悄然归来……故乡的老人会笑问客从何处来,你会泪答,你回自远方,回自梦。你属于故乡……然后,你忘记你曾在远方。然后,你死在故乡。”他许下大愿,生于斯土,长于斯土,终归斯土。
许达然
1940年生于台湾台南市,东海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从事台湾社会史研究。著有散文集《含泪的微笑》《远方》《土》《水边》《人行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