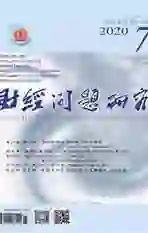管理者的雇佣歧视:辱虐管理分化的影响
2020-09-22滕飞
滕飞



摘 要:管理者的雇佣歧视不仅潜在危害大、持续时间长,更会引起职场排斥与职场欺凌,大大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以及生活满意度。现有研究往往模糊了雇佣歧视与辱虐管理之间的内涵界限,导致概念之间的界限不清、关系不明。本文在界定辱虐管理分化概念的基础上,试图以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解释辱虐管理分化的内部机制以及对管理者雇佣歧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辱虐管理分化可以被解释为在管理者个人层面上的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感知对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机制,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对管理者雇佣歧视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在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上述结论说明,管理者的辱虐管理会通过影响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形成员工感受到的辱虐管理分化,这种差异是雇佣歧视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反雇佣歧视的治理中,抑制管理者在部门中实施辱虐管理是工作重点,避免辱虐管理情境下部门形成小圈子的管理氛围也是必要的治理路径。
关键词:管理者;雇佣歧视;辱虐管理;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内部人身份认知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后,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债务规模屡创新高、产能与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严峻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产能过剩、新旧动能转化、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强、国内外挑战增多的复杂局面。996工作制、狼性文化盛行并凸显出很多企业不惜一切代价竞争的决心与勇气,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催生出更多的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问题。被自愿加班、35岁现象、不生孩子承诺等一系列赤裸裸的职场雇佣歧视问题已经使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失去职业自由,并被辱虐与歧视麻木地捆绑在一系列激化竞争、必须在道德上作出妥协的规则与制度之下。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问题已经让健康的企业文化逐渐变质并使很多企业误入歧途。我们很难相信,中国企业的未来可以通过管理者们的恶意企图去实现,我们更难以相信,部分管理者们鼓吹的超负荷工作和培养工作狂能让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的发展。
员工由于种族、性别、年龄等原因在招聘培训、薪酬发放、晋升辞退等组织环境中被区别对待,即可被认定为雇佣歧视。如何减少雇佣歧视,是理论界必须面对的客观问题。近二十多年来,在工作场所中,反歧视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雇佣歧视仍然无法根除。特别是管理者的雇佣歧视,因其隐蔽性强、持续性长、伤害广泛而深远,一直备受理论界的关注。在雇佣歧视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性别、年龄、种族、肤色等方面的歧视仍是研究的热点。自Tepper和Bennett[1]对辱虐管理的定义得到学界的共识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如何评价辱虐管理及其影响,已经成为组织行为学领域备受热议的重要话题。大量文献证实了管理者雇佣歧视的负面后果,例如,工作态度消极,精神和身体健康受损等。那么,管理者雇佣歧视是怎样产生的呢?现有对管理者雇佣歧视产生原因的解读,主要是基于管理者偏好、统计性、刻板印象、相似性等因素,可以从社会学习理论、资源保存理论等多个理论视角加以分析[2]。笔者创新性地引入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去解读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之间的内在联系。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提供了圈内人与圈外人的理论视角,从管理者个人层次来看,实际上明确了个体圈子质量差异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一视角出发,辱虐管理也是存在差异的,即辱虐管理分化(Abusive Supervision Differentiation,ASD)[3]。因此,本文基于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为解释理论,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中外企业管理者及其员工作为配对样本,剖析辱虐管理分化的概念内涵,揭示管理者的辱虐管理对雇佣歧视的影响,试图为雇佣歧视的治理问题提供另一条可行的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辱虐管理分化的产生:辱虐管理、内部人身份认知与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
从雇佣歧视的内涵来看,雇佣歧视是基于特定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不公平或负面对待。大部分研究将雇佣歧视视为负面行为,常常与欺凌、辱虐管理混为一谈。但是,一方面,雇佣歧视应被视为一种“被区别”的主观感知,欺凌、辱虐管理实际上仅表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敌对行为,并没有强调客观上持续性的、有意识的“区别”的主观态度,因而实际上辱虐管理和雇佣歧视是存在可区分性的;另一方面,辱虐管理还存在促进员工建言、和谐上下级关系等积极影响,类似的研究结论在对雇佣歧视的研究中并未发现[4]。因此,笔者认为,雇佣歧视与辱虐管理是不同的概念。从雇佣歧视的成因角度来看,现有理论主要关注管理者的个人偏好、统计性、刻板印象等方面的影响。领导风格或领导方式,尤其是辱虐管理这样的负面领导风格或领导方式是否会对管理者的雇佣歧视产生显著影响,这是一个会被忽视的问题。人们常常认为,雇佣歧视会形成辱虐管理,但很少考虑辱虐管理是否会滋生雇佣歧视。Tepper和Bennett[1]将辱虐管理定义为一种有针对性的、持续性的敌意行为,辱虐管理的终点是两者关系的终止或下属行为向领导期望行为的改变。正如Tepper等[5]强调的,辱虐管理的初衷是领导期望提升员工绩效而采取的有针对性、惩罚性的行为方式,并不存在蓄意、恶意伤害员工的目的或想法。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初衷是否会使辱虐管理促使管理者滋生雇佣歧视呢?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现有研究的模糊地带。基于此,笔者选择了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这一对变量,探索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现有研究结论表明,员工会因旷工、不良绩效和营业额下滑而被实施辱虐管理。作为回应,员工会使用诸如建言、与主管针锋相对或离职以保护自己免受虐待[5]。从成本角度来看,许多策略在工作上(例如,吹牛)或财务上(例如,退出)的代价很高,比较合理的策略是员工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支持与保护[6]。鉴于人们倾向于在遇險时寻求亲密社会群体的支持,因而保持与管理者高水平的领导成员交换成为理性的明智选择。可以推知,在辱虐管理的情境下,寻求亲密社会群体的支持是员工的理想选择,也客观上造成了ASD的发生。管理者对部门内的成员进行辱虐管理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即ASD。ASD说明辱虐管理对于不同个体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可以从团队层面去理解,也可以从个人层面去理解。一方面,对员工个体而言,员工存在领导成员交换的动机与意图,ASD表征了不同个体对圈子认知的差异;另一方面,ASD是在团队层面存在的,管理者与部门中部分成员形成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会促使管理者体会到更强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7],并据此进行资源交换,而这一情境也受到内部人身份认知(源自于社会认同理论)差异的影响,即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同时,个体会依据社会比较的结果以及自己对圈内人身份的认知情况产生积极区分的想法,其负面结果就是区别对待。这种分化实际上是领导成员交换客观造成的结果,结合社会认同理论来看,即导致了不同水平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当一个人察觉到在工作组中ASD客观存在时,往往会导致更糟的组织氛围,因为ASD助长了负面的自我对抗以及其他人对辱虐管理的社会比较。与其他人相比,当人们察觉到自己遭受辱虐的风险更大时,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消极情绪,进而使矛盾激化并促使管理者进一步区分圈内人与圈外人,由此,差异化的对待也随之加剧。分析其内在原因,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内部人身份认知是组织归属感、认同感产生的基础,是个人对组织成员身份的接受程度。事实证明,感受到圈内人与圈外人差异的管理者对辱虐管理的目标对象提供的组织支持更少,甚至会排斥这些员工。组织中个体层次对小圈子的感知可以提供资源与支持,更可以成为抵御其他主体雇佣歧视的坚强盾牌。对内部人身份感知越清晰,所造成的社会比较越严重。因此,从管理者自身出发,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交互效应,实际上影响了管理者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水平,并在组织层面形成差序式的组织关系。基于上述观点,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认知对管理者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
2.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与雇佣歧视
在工作场所中,以各种受保护或弱势的特征(例如,种族、性别、残疾状况、口音、籍贯、部门关系等)为原因公开歧视他人是非法的,基于与工作无关的特征(例如,性取向,性别认同,吸引力)为原因歧视员工在企业中是不被接受的。根据Turner[8]在自我归类论中的论述,社会比较必然导致积极区分,并将有利的资源分配给圈内人,而将不利的资源分配给圈外人。在组织或部门内部,这种积极区分是社会比较的必然结果,实际上造成的资源不均情况从负面影响来看客观上形成了管理者的雇佣歧视。
从领导成员交换的角度来看,领导成员交换理论[9]提倡领导者应该致力于与员工建立高质量的交互关系。该理论还指出,管理者不太可能发展与所有员工同样的交互关系。鉴于管理者时间、精力和资源有限,管理者区分员工,与某些人建立高质量关系的同时与另一些员工的关系必然相对变差,这个过程被称为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10]。结合社会认同理论可以推知,实际上,管理者成员交换差异化即为团队层面上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过程,而将视角关注到领导成员交换相对质量偏低的员工身上,管理者也会基于员工身份以及员工身上的显著特征而产生不同程度的雇佣歧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管理者个体层面上,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对管理者的雇佣歧视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
3.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由于资源、时间等因素的限制,管理者会和员工之间建立起远近有别的上下级关系,并对员工进行差异化的对待。以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为解释理论,笔者认为,辱虐管理实际上是因为部门内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差异化,即管理者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进而影响到管理者的雇佣歧视。首先,基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管理者在辱虐管理的实施过程中,被辱虐员工会寻求帮助与支持,ASD会引起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变化。其次,与部门同事建立的亲密关系是纾解辱虐管理的关键资源,圈内人会选择保护或支持被辱虐对象[11-12],减少辱虐管理引起雇佣歧视的可能。圈内人提供的关键资源恰可以改变管理者与员工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加剧或抑制辱虐管理对员工的负向影响。再次,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这一变量实际上贯穿了两个不同的、存在差异的过程,前一过程实际上是辱虐管理分化产生的过程,后一过程则是管理者雇佣歧视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辱虐管理必然导致在个体层面上对待不均的现实情况,而小圈子中的管理者也会受到差异与比较的影响,这是雇佣歧视产生的根源。最后,如果在领导成员交换视角以外,从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所谓社会认同的产生是基于差异化的身份认知,而这种身份是辱虐管理分化与个体对圈子的理性选择,结果则是个体对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区分对待,即雇佣歧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在管理者个体层面上,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在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1.研究程序与研究样本
本次采样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之间进行,共在371家中外企业发放问卷514份,回收问卷346份,经筛选后有效问卷301份,有效率为59%。本研究采取匿名的方式进行样本采样。调查对象为各个公司部门经理以上管理者以及其对应的员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充分考虑到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话题的敏感性,因而调研过程较为复杂。具体程序如下:一是通过多个企业家联谊会、MBA班随机联系企业家,发放匿名邮件,进行前期沟通与联系,说明项目目的;二是在约定的时点,通过邮件由接受调研的管理者填写问卷一,具体包括控制变量问卷、辱虐管理问卷、内部人身份认知问卷、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问卷、显性歧视问卷;三是在首次问卷提交后的3个月内,在该名管理者随机提供的3名员工名单中随机抽取1名,雇佣第三方机构与其联系后,辅导填写问卷二,包括辱虐管理问卷(第二次测量问卷),结合第一次测量结果,计算加权平均数(经专家咨询,权数定为50%);四是问卷回收后1个月内,雇佣第三方机构邀请该名员工再次填写雇佣歧视(人际歧视)问卷;五是随机采访另两名员工中的一位,检验管理者与员工对雇佣歧视问题填写的真实性;六是进行问卷匹配与筛选,筛选出有效问卷用于后续研究。这种设计方式虽然较为复杂,但通过在个体层面下不同来源、不同时点的数据收集,不仅可以尽可能地降低同源方法偏差,而且可以更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被調研的管理者样本中,不仅包括265名中国籍管理者,还包括36名外籍管理者(其中,15名美籍,6名英籍,4名法籍,11名其他国籍)。在所有管理者中,男性管理者占总人数的63%,平均年龄为35.681岁,平均任职年限为7.263年。在教育程度方面,本科以上学历的管理者数量最多,占比34.762%。研究样本的基本工作特征统计反映了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测量工具
辱虐管理(AM)。本研究采用Tepper和Bennett[1]开发的辱虐管理量表,该单维量表包含1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1代表“他/她不曾对我做过这种行为”,7代表“他/她非常频繁地对我做这种行为”。在问卷一中,笔者的调查对象变更为管理者,相应的题项也成为1代表“我不曾对他/她做过这种行为”等。在本研究中,问卷一与问卷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11、0.870。
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LC)。本研究采用Liden等[13]开发的基于个人层面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量表进行测量。量表为单维量表,包括“与大多数同事相比较,我与该同事有更好的关系”等6个条目。在本研究中,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信度系数为0.895。
内部人身份认知(IR)。本研究采用Stamper和Masterson[14]开发的基于个人层面的内部人身份认知量表,该单维量表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包括“我感觉我是本组织内部的人”等6个条目。在本研究中,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信度系数为0.882。
雇佣歧视。根据Hebl等[15]对组织情境下歧视的分类,雇佣歧视可分为显性歧视(Formal Discrimination,FD)与人际歧视(Interpersonal Discrimination,ID)。显性歧视通常发生在雇佣、职位升迁等环节,主要包括健康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可以通过符号进行积极区分的歧视行为。本文参考杨晓等[16]的研究,形成包括“我在组织招聘和日常管理中会对不同民族的员工区别对待”等6个题项作为显性歧视量表。在本研究中,显性歧视的信度系数为0.925。人际歧视主要参照负面感知量表(Perceived Negativity Scale,PNS)[17],對管理者对应的员工进行访问,包括“你发现领导对你是什么态度”等7个题项。在本研究中,人际歧视的信度系数为0.902。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领导的性别、年龄、任职时间、学历等4个要素。
3.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潜变量的区分效度,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模型(1)的相对拟合指标CFI、TLI均大于0.900,RMSEA未超过0.100,均达到评价标准,因而拟合效果更好,说明辱虐管理等5个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辱虐管理与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内部人身份认知、显性歧视以及人际歧视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与显性歧视以及人际歧视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从表2中得出的上述分析结果初步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并奠定了后续交互效应、中介作用检验的基础。
2.回归分析
基于交互效应的检验,本文先对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认知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便计算交互项,并进行层级回归。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第二步将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认知纳入回归模型;第三步将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交互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辱虐管理对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58,p <0.010),辱虐管理×内部人身份认知这一交互项对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36,p <0.050)。即管理者进行辱虐管理时,如果能更强烈地感知圈内人身份,就会在管理员工的过程中发生更多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基于此,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认知对管理者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假设1得以验证。这一假设的得证,阐明了辱虐管理、内部人身份认知与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之间的理论关系,充分解释了ASD形成的内在机制。
雇佣歧视对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对显性歧视(β=0.644,p<0.010)和人际歧视(β=0.618,p<0.010)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当管理者进行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时,均会促使显性歧视与人际歧视的滋生。基于此,假设2得以验证。这一分析结果验证了ASD对雇佣歧视的影响机制,并从两个维度说明这种影响的广泛性、易发性与显著性,为说明辱虐管理会产生雇佣歧视提供了理论依据。
3.中介效应的检验
本文借鉴了理论模型中既有调节效应又有中介效应情况下的常规做法,以基本中介模型(Basic Mediated Model)为基础,加入调节变量,应用拔靴法(Bootsrap),并使用Mplus统计软件分析调研数据,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在辱虐管理×内部人身份认知交互项与显性歧视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β=0.043,p<0.050);另一方面,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在辱虐管理×内部人身份认知交互项与人际歧视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β=0.047,p<0.050)。基于此,假设3得以验证,即当实施辱虐管理过程中越发产生内部人身份感知,管理者越可能通过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中介对员工施加更高水平的显性歧视与人际歧视。表5的分析结果对假设3的验证,形成了辱虐管理、内部人身份认知、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与雇佣歧视之间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既说明了内部人身份认知程度的高低对ASD到雇佣歧视这一理论路径的客观影响,也说明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这一核心变量对解释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之间关系的重要价值。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意在揭示管理者在实施辱虐管理的过程中如何滋生雇佣歧视的理论问题。以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本文借助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这一关键变量揭示了辱虐管理对雇佣歧视的影响。不仅如此,笔者还以辱虐管理和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诠释了ASD是如何产生的,这是Ogunfowora和Weinhardt[3]提出ASD后对这一内涵进一步的理论探索。笔者认为,辱虐管理×内部人身份认知交互项影响管理者的雇佣歧视变量,这一过程首先是基于管理者个体ASD这一机制而形成的。具体而言:一是管理者辱虐管理与其内部人身份认知交互影响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二是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对雇佣歧视存在显著的影响;三是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在管理者辱虐管理与其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交互作用与雇佣歧视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2.研究启示与研究展望
正如Ogunfowora和Weinhardt[3]所言,ASD研究中一个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ASD以及其后续影响。当试图明确ASD对员工的影响时,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引入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揭示管理者ASD内部的“黑箱”,即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认知对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交互效应。本文将研究视角由员工平移至管理者这一辱虐管理主体,开发并验证了一个链式理论模型,不仅证实了辱虐管理影响领导成员交换的现有研究结果[18],而且讨论了如何(解释机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边界条件)引致雇佣歧视的理论问题,并通过剖析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进一步扩展了理论贡献,从而揭示了ASD的内涵机制问题。总的来说,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越感觉到部门内自己身边存在一个关系亲近的小圈子,辱虐管理的结果就是越发明显的差异化对待。此外,该研究为ASD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说明了未来在不同研究设计中使用ASD理论的可行性。
这项研究更为重要的结论是阐明了辱虐管理对雇佣歧视的影响机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雇佣歧视研究的微观视野。从经验角度来看,以往的研究始终聚焦各种类型的歧视问题,忽视了歧视往往始于微妙的情境以及圈子文化对管理者的实际影响。对此,本文以理论为先导,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辱虐管理不仅不利于员工发展,而且会对管理者产生雇佣歧视的负面影响。从理论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辱虐管理与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交互效果作用更大,如果从自我归类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可以理解为,内部人身份认知既是辱虐管理影响管理者雇佣歧视的“帮凶”,反過来又可在反歧视治理中作为一种缓冲措施,抑制辱虐管理通过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影响管理者的雇佣歧视。此外,与大多数心理学研究将内部人身份认知作为中介变量的做法不同,本文将其作为调节变量。一方面,从自我归类理论的逻辑框架来看,内部人身份认知是基于个人文化认同、组织认同形成的态度认知;另一方面,内部人身份认知与核心自我评价、组织支持感等变量类似,为研究提供了工作场所的具体情境,因而作为调节变量更具有理论意义,研究结论也验证了交互效应的存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工作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本文的研究发现,辱虐管理显著影响管理者的雇佣歧视水平。因此,领导者应反思如何减少这种领导方式,并避免雇佣歧视的产生。具体可采取的如下方式:一是公开讨论有助于和谐工作环境的形成,和谐部门员工与领导之间的工作关系,减少辱虐管理的工作方式;二是管理者需要尝试改变部门小圈子的工作氛围与环境,避免与员工之间明显的远近亲疏;三是领导者应尽量在部门内部“一碗水端平”,消解辱虐管理的负面影响,控制或消除更远端的团队后果,例如,团队冲突、团队不信任和不良的态度后果。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为反歧视开启了另一扇大门。按照Tepper和Bennett[1]界定辱虐管理的本意来看,实施辱虐管理的管理者本身有敌意无恶意,其根本动机极可能是为了提升员工或组织绩效。但是,辱虐管理不仅是一种有敌意的、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并且存在ASD问题,显著影响管理者的雇佣歧视水平。换言之,可以认为,辱虐管理是管理者雇佣歧视的重要动因。这不仅警示我们要重视辱虐管理的负面影响,减少这种领导行为方式,更促使企业重视营造部门内部抵制辱虐管理的工作氛围,“有话好好说,有事按规则办”。除此以外,内部人身份认知、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也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辱虐管理与雇佣歧视之间关系的治理策略,为反雇佣歧视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
3.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研究采样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员工和管理者自我报告,因而共同方法偏差会对研究结果存在潜在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减少这种影响:一是本研究在收集调查数据时坚持小规模发放,并针对管理者及其员工进行匹配共同构成研究数据,时间上在管理者填完问卷一后再进行员工数据的匹配与采样。二是延长调研周期,以及对问卷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含蓄性处理,中断被试样本的样式响应,减少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虚假关系。其次,研究设计的问题。一是由于研究变量的特殊性,纵向研究或实验法可能会解决现有研究尚未涉及的问题,但由于现有模型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因而常规的截面研究设计是必要的方式。二是本研究仅局限在个人层面进行,并没有引入跨层次变量,因而并未进行跨层次研究。鉴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未来应使用不同的研究技术(例如实验法)、纵向面板数据、跨层次研究设计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 Tepper,B.J.,Bennett,J.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43(2):178-190.
[2] Tu,M., Bono,J.E., Shum,C.,et al.Breaking the Cycle:The Effects of Role Model Performance and Ideal Leadership Self-Concepts on Abusive Supervision Spillover[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8,103(7):689-702.
[3] Ogunfowora,B.,Weinhardt,J.M.,Hwang,C.C.Abusive Supervision Differentiation and Employee Outcomes:The Roles of Envy, Resentment, and Insecure Group Attachment[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9,16(8):1-31.
[4] 朱金强,徐世勇,张丽华.“宽猛相济”促创新——基于阴阳观的视角[J].南开管理评论,2018,(5):202-214.
[5] Tepper,B.J.,Duffy,M.K.,Henle,C.A.,et al.Procedural Injustice,Victim Precipitation,and Abusive Supervision[J].Personnel Psychology,2006,59(1):101-123.
[6] Nandkeolyar,A.K.,Shaffer,J.A .,Li,A.,et al.Surviving an Abusive Supervisor:The Joint Roles of Conscientiousn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4,99(1):138-150.
[7] Farh,C.I.,Chen,Z.Beyond the Individual Victim:Multilevel 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 in Team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4,99(6):1074-1095.
[8] Turner,J.C.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Identity:Some Prospects for Intergroup Behavior[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75,5(1):1-34.
[9] Graen,G.B.,Uhlbien,M.Relationship-Based Approach to Leadership:Development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Theory of Leadership Over 25 Years:Applying a Multi-Level Multi-Domain Perspective[J].Leadership Quarterly, 1995,6(2):219-247.
[10] Henderson,D.J.,Liden,R.C.,Glibkowski,B.C.,et al.LMX Differentiation:A Multilevel Review and Examination of Its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J].Leadership Quarterly,2009,20(4):517-534.
[11] Mitchell,M.S.,Vogel,R.M.,Folger,R.Third Parties Reactions to the Abusive Supervision of Coworker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5,100(4):1040-1055.
[12] Priesemuth,M.,Schminke,M.Helping the Neighbor? Prosocial Reactions to Observed Abusive Supervision in the Workpla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45(3):1225-1251.
[13] Liden,R.C.,Erdogan,B.,Wayne,S.J.,et al.Leader-Member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 and Task Interdependence: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 and Group Performance[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6,27(6):723-746.
[14] Stamper,C.L.,Masterson,S.S.Insider or Outsider? How Employee Perceptions of Insider Status Affect Their Work Behavior[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2,23(8):875-894.
[15] Hebl,M.R.,Foster,J.B.,Mannix,L.M.,et al.Formal and Interpersonal Discrimination:A Field Study of Bias Toward Homosexual Applicants[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2,28(6):815-825.
[16] 楊晓,师萍,谭乐.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工作绩效: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的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2015,(4):26-35.
[17] Liden,R.C.,Graen,G.B.Generalizability of the Vertical Dyad Linkage Model of Leadership[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0,23(3):451-465.
[18] Podsakoff,P.M.,Mackenzie,S.B.,Podsakoff,N.P.Sources of Method Bia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Control It[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12,63(1):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