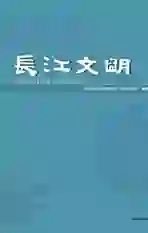抗战时期的《妇女生活》杂志
2020-09-15陈镜颖何刚
陈镜颖 何刚
摘 要:《妇女生活》是抗战时期一份比较重要的妇女刊物,也是国统区妇女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旗帜最鲜明的进步刊物。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教育启蒙妇女、宣传动员妇女抗战等方面积极呼号,以其进步性和革命性,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妇女;它历经六年,辗转上海、武汉、重庆三地,伴随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其主要内容和工作虽有所侧重,但都为中国妇女运动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妇女生活》;沈兹九;妇女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了使妇女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广泛动员妇女投入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中去,各党各派及妇女团体纷纷创办妇女刊物或报纸副刊,出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妇女报刊最活跃的局面。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大中小城镇还是农村,国统区还是抗日根据地,妇女刊物分布地域十分广泛。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出版的妇女期刊有130种。
在抗战时期众多的妇女刊物中,《妇女生活》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国统区教育启蒙中国婦女,宣传动员妇女抗战的一份重要刊物。它的创办和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抗战妇女刊物的一个缩影。该刊由现代著名妇女运动家沈兹九女士1935年7月在上海创办,1941年1月在重庆终刊,共出版83期。《妇女生活》以其时代进步性和革命性,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妇女,为妇女运动事业发展和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
《妇女生活》创刊的1935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展开,特别是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上海,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呼声高涨;而当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政府,镇压救亡爱国运动,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旨在“恢复固有的道德”的新生活运动,鼓吹妇女回家做新贤妻良母。这些均遭到了进步文化人士的抨击。正是在抗战风云激荡的时代浪潮里,为了启迪教育广大中国妇女,宣传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妇女生活》应时而生。
《妇女生活》的创办代表了妇女刊物大都从报纸副刊到专门刊物的发展之路,也反映了当时进步妇女刊物在创立之初面临的艰辛。《妇女生活》的前身是上海《申报》的《妇女园地》副刊。1934年2月18日,倾向进步的上海《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利用腾出的《自由谈》星期日的版面,聘请沈兹九开辟副刊《妇女园地》。沈兹九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在目前中国妇女急应开拓的园地,最少有这种工作:拯救商品的身肉,使之独立自尊。拯救昏暗的灵魂,使之聪明洁净。拯救垂亡的种族,使之光大长存。”[1]
在沈兹九的主持下,《妇女园地》“排除太太小姐式的‘闷闷不乐到公园里去散散心的怡情逸致”,“摒弃讨论怎样取悦男子以博得男子施惠”[2],所刊文章大都揭示妇女所受压迫之根源,阐释妇女解放道路,其大胆的笔触、进步的思想给当时万马齐喑的妇女报界注入了清新之风,深得读者欢迎。著名作家冰心回忆道:“1934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3]但是,好景不长,1934年10月,史量才遭暗杀,《妇女园地》的命运自然也受到严重威胁,难以为继,最终于1935年10月停刊。就在《妇女园地》受到严重威胁之时,沈兹九和她的朋友们从长计议,早作准备,决定开拓新的阵地,自己筹办妇女刊物,并定名为《妇女生活》,“以继承惨亡的‘妇女园地的精神,而开拓我们的新园地”。[4]
1935年7月1日,《妇女生活》创刊,最初由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办公地点设在沈兹九家中,更“因了《妇女生活》内容文字的警惕和激烈,常常接到当局的警告,她为要维护刊物底本身,不惜向各方面奔走呼吁,使《妇女生活》从艰难苦斗中度过”[5]。虽然创刊之初的处境如此艰难,但是,《妇女生活》积极响应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号召妇女抗日救亡。
在《妇女生活》上,沈兹九以兹九、兹、沉淫、莫湮等笔名发表大量文章,倾注了全部心血。同时,她还团结邀请一大批社会进步人士撰稿,主要有茅盾、夏衍、邹韬奋、郭沫若、章锡琛、曹聚仁、沈志远、艾思奇、陶行知、何香凝、阿英、张仲实、沈西苓等。同时,沈兹九利用《妇女生活》,广泛联络妇女群众,成立爱国妇女团体。1935年12月21日,沈兹九与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等发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作为上海妇女救国会的会刊,《妇女生活》成为宣传动员各界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1936年5月,经由《妇女生活》及沈兹九等人的努力,发起成立了以沈钧儒为领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杂志公司决定不再与《妇女生活》合作,刊物只得由沈兹九独立经营。后来经胡愈之介绍,《妇女生活》改由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发行、销售,才算有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20日,《妇女生活》出至第5卷第5期后被迫撤离上海。
撤离上海后,《妇女生活》迁往武汉。1938年8月,武汉告急,《妇女生活》再迁往陪都重庆继续出版。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文化领域不断制造摩擦,打击进步文化出版事业,沈兹九因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愿与其“合作”,辞去主编职务,投入新的战斗岗位,《妇女生活》也因此在出版到第8卷第12期后暂时停刊。三个月后,在中共的组织安排下由曹孟君接任主编,改为月刊继续出版。在第9卷第2期《妇女生活》上,曹孟君发表公开声明:“今后要与编委们一起,仍将本着过去的一贯方针和工作精神,作不懈的努力。在已有的基础上要使她坚持下去,还要使她更壮大,更发扬,完成它应负的使命……”[6]编委会成员主要有曹孟君、沈兹九、史良、刘清扬、胡子婴、韩幽桐、杜君慧、谭惕吾、陆晶清、罗叔章、彭子冈、张志渊、胡耐秋等。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中共代表团和许多进步人士被迫撤离重庆,《妇女生活》于1941年1月被迫终刊。六年期间,《妇女生活》共出版83期。
二
《妇女生活》的“创刊词”鲜明指出了其办刊宗旨和目的:“我们现在开辟了这小小的园地,希望同胞们合力来灌溉,努力来耕耘。叙写你们的所有主张,诉说你们的一切苦难”,“她将做您的知友,给您许多智慧,使您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认识一切的丑恶。她将做您的先导,给您许多指南,使您知道怎样脱去重压,怎样做人,怎样做社会的人,怎样携手走上光明大道。”《妇女生活》从一开始就发出了“妇女也是人”的呼声,明确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附属物,而是整个社会的一分子,得做个健全的“社会人”,“可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享受社会一切的权利”。[7]
《妇女生活》历经六年,辗转三地,伴随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其主要内容和工作也有所侧重。从创刊到“一二·九”运动到全面抗战以前,虽已着手推动抗战,但争取妇女本身利益的斗争,特别是经济斗争,成为中心工作。《妇女生活》主要提供妇女运动的正确理论,对过去中国妇女运动理论与实践提出批评意见,剖析现实的妇女问题和妇女痛苦的生活;从“一二·九”运动到“八一三”上海抗战,《妇女生活》联合其他妇女团体,推动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从“八一三”到被迫停刊,《妇女生活》竭力鼓吹并推动各界妇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妇女的反法西斯统战工作,动员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战,如战地服务、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慰劳伤兵、从事生产事业,推进妇女文化、加紧妇女训练等等,促进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团结合作,将抗战进行到底。具体来说,《妇女生活》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回顾评价“五四”以来妇女运动发展情况,调查介绍国内外妇女状况和妇女运动状况。其中,对有关苏联妇女情况的报道介绍尤为着力,并将其作为妇女解放的范例和中国妇女运动的未来之路。例如,为配合妇女参政和民主运动,《妇女生活》经常介绍苏联妇女参政和民主生活情况,刊载的文章有《苏联妇女政治上的地位》《劳动妇女史上的创舉》《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苏联妇女》《苏联女科学家》《快乐的苏联母亲》。
第二,注重引进借鉴国外妇女运动理论,特别是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注重将妇女解放的潮流引向民间,从而发动劳苦大众。有的文章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历史,分析当前各种妇女问题,帮助广大妇女认识过去,分析现实,展望未来。例如,杜君慧的《我国女权运动的生长和没落》、碧遥的《二十四年来中国妇女运动走过的路程》等;有的文章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学说,如沈志远的《社会科学之哲学的基础》等。同时,还邀请艾思奇到组织的妇女读书会讲《大众哲学》,罗琼编辑“经济纵横”专栏,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妇女就业问题和妇女生活问题等。
除了理论分析之外,《妇女生活》还设置灵活多样的栏目,利用传记、小说、电影、诗歌等生动的文艺作品,形象地反映中国女工、农妇和职业妇女失业彷徨、流离失所的生活,指导妇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引导她们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寻求思想解放和生活独立,成为有理想有知识的新时代女性。
第三,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妇女回家论”“新贤妻良母主义”等复古倒退论调进行抵制和批判,号召广大妇女“跑出家庭,为自身,为民族,求利益”。 由此形成了自“五四”以来围绕“新贤妻良母主义”的第二次大论战,为动员广大妇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作了思想准备。
她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论”“只是法西斯麻醉妇女的毒药”,“是封建社会奴役妇女的美名”[8],“是锢禁妇女的工具”[9],坚决反对妇女回到家庭去做贤妻良母,而是应该从家庭中走出来,走到社会中去。在“发刊词”中,她们就指出:“卫道先生们,在主张‘妇女回家,有的高唱恢复‘三从四德,然而在这疮痍满目的半殖民地生活条件下,无情的事实,却不能如他们的愿望。大多数的妇女,已无法从父从夫从子;她们不得不抛弃家庭,跑上社会去挣扎。”[10]同时,《妇女生活》借着对易卜生的戏剧《娜拉》的讨论,从第1卷各期到第2卷1期,连续刊登了碧遥的《娜拉三态》《“薇薇”与“娜拉”》,雨椿的《使娜拉出走的是什么》,王孝英的《妇女回家庭去吗》,以及《娜拉》座谈会记录,对这些论调进行批判。甚至到了1937年1月,还刊载有郭沫若的《旋乾转坤论——由贤妻良母说到贤夫良父》一文,提出:“男女应该以同等的人格相对待,互相尊重,互相玉成,以发展各自所禀赋的性能。”[11]
第四,抗战全面爆发后,各地妇女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妇女生活》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关切时局发展,报道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情况,记述各地先进妇女集体和模范人物从事抗战宣传、慰劳、衣物征募、伤兵服务、难民救济、儿童保育等工作,进一步鼓舞广大妇女投身全面抗战,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抗战中的湘西妇女》《妇女救亡运动在南昌》《妇救运动在陕西》《华北抗战妇女》《广东妇女抗战工作已踏上最前线》等。她们坚决主张,只有“在求民族解放的总路线下,才能解放妇女自身,离开民族利益,妇女就无从求解放”[12],“因为当前的抗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中华民族争得解放的一天,妇女才有解放的可能;只有妇女在民族的斗争中尽着最大的努力,在民族解放之后,妇女才能真正地获得解放”[13]。
三
《妇女生活》是国统区妇女刊物中坚持最长久,旗帜最鲜明的进步刊物,其“全部的历史充满着为妇女大众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的斗争”[14]。她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自觉担负起宣传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妇女救亡工作的时代任务,当然与主编沈兹九等编委会成员的艰苦努力,追求进步的革命精神紧密相关。除此之外,还需指出,《妇女生活》虽以个人名义创办,但它始终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与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刊物。所以,《妇女生活》各项成绩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影响密不可分,此处仅举两位共产党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来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位是早在1928年就參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妇女运动理论家的杜君慧。沈兹九后来曾深切回忆道,在创办《妇女园地》和《妇女生活》的时候,她“为自己肩负的重担而焦虑”,“多么希望能得到党的指导和帮助。就在这个彷徨的时刻,党主动找我来了。来找我的人就是杜君慧,她是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老师”[15]。1934年初,中国共产党委派杜君慧协助沈兹九主办《妇女园地》副刊。刚来的杜君慧就在《妇女园地》上用八个月的时间连载了《妇女问题讲话》一文。这是一篇用马列主义观点揭示妇女被压迫根源、阐述妇女解放道路的长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在史量才被杀,《申报》政治态度有变时,杜君慧凭借政治敏感性,告诉沈兹九要做好转移阵地、另辟战场的准备,这才有了《妇女生活》的顺利诞生。沈兹九后来说:“杜君慧是如此机智而且巧妙地使《妇女园地》过渡到《妇女生活》,甚至还利用了最后几期《妇女园地》为将要诞生的《妇女生活》大登广告,不仅没有中断读者与我们的联系,而且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妇女生活》的创办,怎能不归功于君慧,归功于党呢?”[16]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杜君慧马上带着宣言的油印稿给沈兹九看,并立即赶写社论,发表在第二天的《妇女生活》上。杜君慧和上海妇女的一些党团员“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更踏实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成立各种各样形式的小型妇女组织”[17],在杜君慧的引导和影响下,《妇女生活》和沈兹九积极联络上海各界妇女代表,开展座谈会、报告会,共商妇女抗日救亡大计,而这些座谈会、报告会“都是上海地下党文委组织领导的,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作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18]
第二位就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邓颖超同志。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后,《妇女生活》先后辗转武汉、重庆两地。相继任中国共产党长江局、南方局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对《妇女生活》进行了直接的指导。她经常参与《妇女生活》的编辑工作,给予办刊方向和人员组织等方面的指导。例如,1938年初,邓颖超就在刚刚迁到武汉的《妇女生活》上发表《对抗战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妇女运动的总任务和中心工作,为当时武汉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要在总的抗日统一战线下,经过统一战线,去动员组织各界妇女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19]
在武汉复刊后,沈兹九在筹办图书馆、组织《妇女生活》读者会时,经常邀请邓颖超、邹韬奋等到读者会作报告,提高女青年的政治觉悟。编委会重要成员罗琼回忆道:“我初见邓大姐是1938年春末在武汉的时候,那是在几次妇女界的集会上,一次是《妇女生活》杂志、妇女救国会的领导骨干会议,一次是上层知名妇女座谈会,再一次是武汉女学生读书会”,她在这几次座谈会上“精辟地阐明党的抗战纲领以及对妇女支援抗战的意见”。 [20]刚到武汉的罗琼不仅在妇女座谈会上见到了邓颖超,而且通过同是中共党员的季洪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邓颖超就来到罗琼家里访谈。当罗琼表示刚到武汉因为人生地不熟,活动大都在上海老朋友圈子里,较难同当地妇女接触开展工作时,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说:“革命青年要有五湖四海的胸怀,要有同一切主张抗战的人合作的气魄。上海妇女、武汉妇女都是中国妇女。你们那天开的《妇女生活》读者会,当地女青年那么热情,都愿意到农村去,同农村妇女一起支援抗战。你们开展工作的条件很好,既可鼓励她们读你们的杂志,又可鼓励她们写文章,大家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平等相待,互相启发,把《妇女生活》杂志办成她们的喉舌,把你们上海妇女救国会的工作扩展到武汉妇女中去。”[21]
1939年,同样在邓颖超的介绍与帮助下,沈兹九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邓颖超的直接安排下,接替沈兹九主编《妇女生活》的曹孟君也是共产党员。1939年9月,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1940年2月底回国,回国后为《妇女生活》连续写了《我在苏联》《莫斯科印象》等几篇文章,介绍苏联建设成就及妇女生活状况,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但已经消灭了阶级间的不平等,亦消灭了民族间、男女间的不平等”,“实现了男女彻底的平等。”[22]对于邓颖超的指导,沈兹九后来曾说,《妇女生活》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取得成绩,“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武汉与重庆时期,是中共长江局和南方局妇委的正确领导”。[23]所以,邓颖超对《妇女生活》的全面指导,保证了《妇女生活》在思想和组织上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抗战统一战线政策保持一致,为推动中国妇女运动事业发展和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均做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碧遥.快开拓妇女的园地[N].申报,1934-02-18.
[2] 敏之.谁的妇女园地[N].申报,1934-02-18.
[3] 冰心.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A].董边.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11
[4] 沈兹九.悼“妇女园地”[J].妇女生活,第1卷第1期,1935.
[5] 梅邨.沈兹九[A].杨之华.文坛史料[C].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250.
[6] 曹孟君.接编的几句话[J].妇女生活,第9卷第2期,1940.
[7] 发刊词[J].妇女生活,第1卷第1期,1935.
[8] 罗琼.从“贤妻良母”到“贤夫良父”[J].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
[9] 罗琼.怎样走出家庭?走不出又怎样?[J].妇女生活,第4卷第7期,1937.
[10] 发刊词[J].妇女生活,第1卷第1期,1935.
[11] 郭沫若.旋乾转坤论——由贤妻良母说到贤夫良父[J].妇女生活,第4卷第1期,1937.
[12] 胡刚.由“五四”“五卅”说到我们目前的步伐[J].妇女生活,第2卷第4期,1936.
[13] 寄洪记录.今年怎样纪念三八[J].妇女生活,第5卷第9期,1938.
[14] 曹孟君.接编的几句话[J].妇女生活,第9卷第2期,1940.
[15] 黄景钧.风云岁月[A].董边.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53-54.
[16] 黄景钧.沈兹九与《妇女生活》[J].新观察,1983(18).
[17] 沈兹九.忆杜君慧同志[N].人民日报,1982-02-11.
[18] 罗琼谈,段永强访.罗琼访谈录[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19.
[19] 邓颖超.对抗战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J].妇女生活,第5卷第6期,1938.
[20] 罗琼.罗琼文集[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162.
[21] 罗琼谈,段永强访.罗琼访谈录[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38.
[22] 邓颖超.我在苏联[J].妇女生活,第9卷第1期,1940.
[23] 季洪.历史的足迹[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