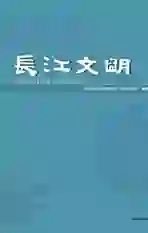古代巴渝古琴文化考略
2020-09-15梅强
梅强



摘 要:考察琴史不能只着眼于狭义的乐器史或音乐史,而应当将其置于广义的文化史中。巴渝地区并非“古琴文化荒漠”,该地区有关琴文化的古代遗迹和书写一直存在。出土琴俑表明至晚在东汉本地已有琴艺活动,隋唐至北宋不少琴史留名的客籍琴人与巴渝有过深厚渊源,两宋之际琴文化融入本地士人圈,明清时期琴文化在本地普及到各个阶层。巴渝琴文化的发生、发展是在中国琴文化大环境与地域文化演变的交互中进行的,其主体更是基于文人琴的传统。研究巴渝琴文化对进一步挖掘巴渝文化资源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古代;巴渝;古琴;琴文化
中国古琴岁历绵暧,博大精深,被尊为“乐之统”,在中国艺术史、文化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社会一个地域琴文化的兴盛程度是其礼乐文明程度的一种反映。相较于蜀地古琴文化研究的显盛,对巴渝古琴文化长期以来缺乏关注,乃至有学者和琴家断言:“从古琴文化方面看,我们没有查到晚清以前的资料,似乎说明此前重庆没有出过古琴名家。”[1]“重庆是古琴文化的沙漠,现在才刚刚兴起。”其实不用说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琴艺活动的繁荣,即便是古代巴渝地区(以重庆为主体,兼括陕南、鄂西、湘西北、黔北、川东部分地区[2]),有关琴文化的遗迹和书写一直存在。琴史学家唐中六先生曾撰有《古巴渝地域的古琴资料》[3](下文简称《古》),提供了一部分古代巴渝琴史材料。但这一工作仍显不足,主要体现在材料挖掘不广、史实考辨不详尽、研究系统性不够等。《古》文中如剔除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以及尹吉甫、尹伯奇、司马相如等籍贯受到争议的人物,剩下可以作为信史的材料并不是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发掘材料的范围局限于艺术史文献(如《琴史》《琴史补》《琴史续》)造成的。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士无故不彻琴瑟”(《礼记·曲礼》)、“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风俗通·声音》),古琴与传统士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由此超越了一般乐器本身而有了文化的属性,正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言:“由于它的风雅和逸趣,(琴)逐漸成为文人生活的象征。古琴的音乐属性渐渐成了这件乐器的附属物,而它的中心则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一种恰好包容中国旧式文人中庸倾向特征的思想意识。”[4]考察琴史不能只着眼于狭义的乐器史或音乐史,而应当将其置于广义的文化史中。乔建中认为广义的琴学,除了涵盖乐器、乐律、乐学内容外,还延伸出“人文、历史、社会的诸多事项”[5]。按照这样的琴学观,举凡琴人、琴事、琴曲、琴谱、琴论、琴文学、琴派、琴器等的历史沿革都应当属于琴文化观照的范畴。由这个思路出发,我们挖掘和整理出一条丰富而清晰的巴渝琴文化史脉络。
一、作为信史的巴渝早期琴文化:汉至南北朝
关于古琴的创制,传世文献中有伏羲说、神农说、炎帝说、唐尧说、虞舜说等。唐中六先生认为巴渝古琴可以溯至伏羲作琴[6],不过《古》文中所列论据只能说明巴渝民间存在伏羲信仰,与琴的关系不大。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民间文学调查采录了巴县广阳镇回龙村(今南岸区广阳镇回龙村)村民口述的《瑶琴的来历》[7],与旧题东汉蔡邕《琴操》“伏犧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山海经》郭璞注引《世本》“伏羲作琴,神农作瑟”等文献倒是吻合。尽管这样,这类传说本身的年代与人物仍不足为据。因为类似的传说在汉代才开始大量出现,且都附会在近乎全能的上古圣王身上,正如顾颉刚所云“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间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8],这些“琴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难以采信。当然,这类传说中透露出琴的起源久远,且被人们视为意义重大的创制确是毋庸置疑的。
真正作为信史的巴渝琴文化,还要从巴渝出土的汉代抚琴俑说起。20世纪50年代起,江北、开县、万县、忠县、涪陵、丰都、奉节、云阳、巫山等地陆续有抚弦类乐器俑出土,墓葬年代跨度在东汉(如巫山琵琶洲遗址M4、万州沙田墓群M5、丰都大湾墓群M20)至南朝(如万州大地嘴遗址青龙嘴墓地M35、M40、M47)。 之所以说是“抚弦类乐器俑”,因为关于这批俑所抚乐器的定名还存在一些争议:《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2002年)、《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丰都二仙堡墓地》等考古报告以及唐中六《巴蜀琴艺考略》将它们统称为“抚琴俑”;《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把其中一部分有尾枘的(如1957年江北东汉崖墓出土奏乐俑)标为“鼓瑟俑”;李松兰折中诸家说法,认为东汉时期琴的形制未定,具有地域性形态差异,仍将它们统称为琴[9];而李洪财则指出不应当对器型不加区分,这些俑“所持乐器与古琴并无直接关系”[10],“有一弦枘且首尾同宽的乐器应是‘瑟……无弦枘,首尾有岳山,而且短宽的乐器应是汉代的小瑟……无弦枘,首尾有岳山,器形较长的乐器应该是筝。”[11]这些说法我们认为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确实不能认为这类器型都是古琴,因为这些差异是类型化差异而非个别差异,是明显的乐器器型的不同;也不能笼统地将它们归为琴的“地域差异”,这样无法解释为何同一种乐器的“地域差异”会出现在同一个墓葬中。例如丰都镇江包山丘墓地2007FRBSM3号墓的两种抚奏乐俑,M3:92的琴器较M3:19长而窄,尾端无岳,其器型更接近今天的古琴形制(图1),而M3:19则是一种面宽(弦数多)有首尾岳的弦乐器(它与典型的瑟和筝也有一定的差异,目前还无法确定是何种乐器前身)。这一情况同样出现在丰都镇江沙包墓地2008FRSBM12:81、2008FRSBM12:34。
而李洪财“目前所见汉代抚琴俑所持乐器与古琴无直接联系”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相较于瑟、筝,琴在两汉文献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何以在出土中只见到前两者而不见后者?仅就重庆出土的抚弦类乐器俑来看,有一部分俑所持乐器有首岳而无尾枘、尾岳,且为全箱式结构,如巫山麦沱古墓群M47:26(原题“击筑男俑”非是),从器型和抚奏方法上看与今天已十分接近,应当看作早期的古琴。这类出土于重庆的真正的“抚琴俑”我们目前统计有19个 。它们的出土表明,至少在东汉早期巴渝地区已存在琴参与的艺事活动。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好琴,有《西禅听戴道士弹琴》《听履霜操》等琴诗十余首,琴文若干。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别驾,遣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后又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黄在黔州期间以琴相伴,时“携琴至草堂”,认为这是“息焉游焉”之义(《与张道济帖二》[33])。其作于戎州的《题杨道人默轩》(题下自注“崇宁二年戎州作”)中有“轻尘不动琴横膝,万籁无声月入帘”[34]二句,于困厄之中琴境愈高。在黔、戎期间他广结琴友,有荣州(今四川荣县)琴僧祖元大师善琴,黄庭坚与之交,作《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诗,中有“王师学琴二十年,响如清夜落涧泉。满堂洗净筝琶耳,请师停手恐断弦”[35]之句,极赞祖元琴艺之高。另外黄庭坚在赴任黔州途中写过一篇著名游记《黔南道中行记》,记录了巫山(今重庆巫山县)尉辛纮(字尧夫)弹琴场景:
步乱石间,见尧夫坐石据琴,儿大方侍侧,萧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尧夫随磐石为几案床座。夜阑,乃见北斗在天中,尧夫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风激涛波,滩声汹汹,大方抱琴而归。[36]
辛纮善弹《履霜操》《烈女操》,黄庭坚所记其演奏时萧然远举之风神,千載之下犹令人怀想。从这则材料也可以看出宋代士人与琴关系之密切,出游亦必携琴以往,这一行为在宋人诗文中时有体现。
外来文化巨匠的到来促进了巴渝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他们在这里兴学倡教,播下了文化的种子。从刘禹锡慨叹“今之胶庠不闻弦歌”(《奏记丞相府论学事》)[37],到黄庭坚称赞黔倅张茂宗“化民曾寄十三徽 ”(《与黔倅张茂宗》)[38],巴渝乐教事业从无到有逐渐起步。而琴作为乐教以及士人文化的重要部分,也随之在本地士子中普及,本地士人的诗文中也零星有了关于琴的书写。如中晚唐夔州云安(今重庆云阳县)诗人李远,有琴诗《赠殷山人》云:“有客抱琴宿,值予多怨怀。啼乌弦易断,啸鹤调难谐。曲罢月移幌,韵清风满斋。谁能将此妙,一为奏金阶。”[39]“啼乌”“啸鹤”既是借物烘托,又用琴曲《乌夜啼》与《别鹤操》典,颈联韵味深长。诗人若非对琴有足够的了解和赏会能力,无法表达这样的感受。
随着礼乐文化在本地不断扎根与深入,本地士人能琴者开始逐渐增多,群众基础愈加深厚,巴渝本地琴文化由此进入一个发展期。
三、本地琴文化的普及:两宋至明清
宋代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古琴成为士人阶层普遍爱好的雅器,从帝王到文人士大夫再到佛道中人,弹琴、赏琴已成为风尚。对巴渝地区而言,两宋间(尤其南宋重庆由州升府以后)官学、私学和书院的蓬勃兴起使得本地文化事业蒸蒸日上,本地的文人雅士涌现,琴在他们的生活中愈加常见。
如主要生活于高宗时期的理学家、文学家,巴县洛碛[40](今重庆渝北区洛碛镇)人冯时行[41],颇以琴为能事。他用琴表达志趣:“聊以写我心,素琴时按摩。澹泊有妙意,岂忧焚天和。”(《忆渊明》其二)[42]以琴排解苦闷:“遥夜未渠央,取琴和秋虫。”(《东方有一士》)[43]他对琴有着颇为高妙的见解,其《题郭信可琴中趣轩》云:“视听非耳目,况复求音声。”“情尘泯绝处,大地皆?韺。” [44]反映了一种追求“大音希声”的琴学观,此诗亦为琴诗中的优秀作品。又如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东南)的南宋理学家、易学家阳枋,其子阳少箕在《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里说他:“生平所储,惟书数卷,琴一张。”[45]“每良天佳月……编《易》张琴,水边林下,行吟坐啸,乐其自乐。”[46]其侄阳昂亦说他“琴书自娱,无他玩好”[47]。足见琴在阳枋生活中不可或缺。阳枋有琴诗《咏丝桐》云:“地阔天宽人一般,琴心会得语言难。高山流水知音少,月白风清时自弹。”[48]道出了音乐具有超语言功能,颇得理趣。阳枋不但自己好琴,也将琴传之后代,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即丁卯(1267年)中元,“子孙娱侍”之时,阳枋还与其子炎卯“鼓琴以写真乐”[49]。阳枋同乡理学家度正亦能琴,其句“举箑清风满,弹琴白日消”(《奉挽友三舅知县还山》其二)[50]可以为证。
琴文化到了明清时期已十分兴盛,古琴作为传统文人“四艺”之一,成为这一时期士人“标配”之一。优秀琴人辈出、琴谱大量刊刻、琴派业已形成,都是这一时期琴史繁荣的表现。由于此一时期巴渝地区商业的繁荣和文化事业的活跃[51],同时也受琴史大环境的影响,巴渝地区能琴、好琴者在此时屡见不鲜,琴真正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一)文人士大夫
“左琴右书,无故则不撤琴”(明张大命《太古正音琴经》卷一《琴原篇》)的士人风气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巴渝地区的文人士大夫。明代勋臣、才子江津人江渊,游赏家乡风物则“携琴时复到林垌”(《马骁春色》)[52]。梁山(今重庆梁平区)理学家、诗人来知德游白帝城赤甲山时曾“援琴鸣弦写寂寥”(《赤甲行》)[53],隐居万县求溪山时喜欢“流水高山半调琴”(《戊子求溪元日纵笔十首》其一)[54]。其《江边别郭梦菊四首》其三云:“我有孙枝琴,龙凤蟠唇足。不向人间弹,往往寻幽独。朝弹露下松,暮弹月下竹。君侯知我音,五马来空谷。投我白雪篇,掷我阳春曲。感君缠绵意,徽上写不出。为君再三弹,再三山水绿。”[55]抒发了一种不媚世人、唯待知音的琴士高情。明嘉靖年间合州人李谏,为廉政爱民之名宦,政务之余“弹琴种花,大有彭泽遗意”[56]。清代江津才子周佲祚写荔枝园中悠游,必欲以琴佐酒:“携焦琴 ,载浊酒,纵豪吟,酌大斗。”(《荔枝园赋》)[57]清代石柱马氏土司汉文化修养颇高,家族中有不少人善琴,据《补辑石砫厅志·土司志》载:“(马宗大)善琴操……子光裕、犹子光裁、孙孔昭……兼工图章琴棋,秉家训也。”[58]马宗大在追念其祖秦良玉时便说她“相传有素琴”(《九日登西山》)[59]。
《新论·琴道》云:“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对文人士大夫来说,琴是其文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个人修养的象征,是一种文化符号,甚至超越了音乐娱乐的功能而进入“道”的层面,这也是琴在士人书写中占很大比重的原因。
(二)平民阶层
从明清传奇、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琴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琴在此时早已越过了精英文化的畦畛而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除了在文人士大夫的诗文中寻绎出琴文化的线索,我们在巴渝地区明清时期的文献中还发现了这样的材料:
彭万官,字庆莲,四川万县人。工琴……琴声落落指生寒,不似筝琵错杂弹。曾说梨园有三妙,银儿幻术桂儿兰。银官戏法,桂官画兰,万官弹琴,时称三妙。(清吴长元《燕兰小谱》卷二)[60]
巴县妓女郑钗香,貌妍心慧,工弹唱,能鼓七弦琴……县官张公子敏,风流令也。每燕集,招之侑酒,听其曲,神为之倾,令抚七弦,更色舞眉飞,夸为绝技。(清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卷一《节妓》)[61]
涂孝……家贫,甘旨常给母,(母)喜听音乐,夜则吹笛弹琴,博其欢心。(清光绪《江津县乡土志》卷一)[62]
彭万官为伶人而善琴,时人称妙;郑钗香处勾栏北里之中而善鼓七弦琴,且技艺较高;而涂氏孝子虽为贫士,亦解操缦。这些都是此一时期古琴在平民阶层普及的例子。对于平民阶层来说,他们未必如文人士大夫那样将琴视为负载“道”的工具,大多时候只是把它当作娱乐的工具。
(三)琴家杨正经、竹禅和尚
重庆本土分别在明末和清末诞生了杨正经和竹禅和尚这两位对琴文化贡献颇大的人物。前者是明末清初腾誉全国的琴学大家,其人其琴更是当时一种遗民文化符号;后者则是近代禅林琴家的代表人物,其琴学思想和传曲对现代琴学影响深远。重庆本土能够产生这样影响全国乃至后世的琴人,不能不说是琴文化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结果。
杨正经,字怀玉,酉阳(今重庆酉阳县)人。初为武职,后为朝廷郊庙乐章审订音律,晋为太常寺卿。正经琴艺极佳,明屈大均《翁山文钞》卷二《御琴记》云:“(正经)尝奏琴便殿,为太古声,上称为过于师襄。”[63]清末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十五云:“(正经)通音律,琴学为海内冠。”[64]又据明末陆符《大还阁琴谱·序》:“蜀有杨生,顾以知琴客于中涓,清禁所传皆其音调。”[65]则正经琴学于宫禁中至为流行。明亡后,正经抱御赐琴入淮,作《西方思》《风木悲》二操,抒发怀君思亲之意 。崇祯帝有琴名“翔凤”,为济南李氏于兵燹中购之,“正经岁逢先帝忌日,辄从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设玉座,拜奠如礼。”(《御琴记》)[66]屈大均、王猷定、李确、李沂、靳应升、张养重等遗民文人皆有听正经弹琴诗,又其事经屈大均、王猷定等人口传,海内名士如张岱、毛奇龄、董俞、魏畊、陈子升等虽未睹其人亦和诗咏之年,足见其影响之远,王士禛乃比之为宋末琴家汪元量。杨氏琴学后由徽人叶鲁白继承之,叶鲁白之琴亦得以“妙绝一时” 。
竹禪(1824—1901年),俗姓王,法名熹,梁山县任贤乡(今重庆市梁平县任贤镇)人。20岁时在梁山双桂堂受具足戒,嗣法于第九代双桂法脉一超禅师。[67]竹禅琴艺高妙,善操《普庵咒》《白雪》《风雷引》《忆故人》《高山》《流水》等曲[68],清《普陀洛迦新志》卷六《十方寄寓》云:“(竹禅)喜抚古琴,其声渊渊,悠扬悦耳,令人万念顿消。”[69]竹禅之于琴学有两大贡献,一者是竹禅在为清代琴僧释空尘《枯木禅琴谱》作序时提出的“以琴说法”,对北宋琴家成玉礀的“攻琴如参禅”说作了很好的补充[70];二者是今天广为流传的琴曲《忆故人》,与竹禅传谱有着密切联系。据《今虞琴刊》中彭祉卿、张子谦《忆故人》跋文乃知此曲传自彭祉卿父亲彭筱香,而清末顾玉成《百瓶斋琴谱》卷外《忆故人》识文云:“此谱乃庐陵彭筱香家骥受传于蜀僧竹禅之钞本……竹禅特其最善者耳。”[71]
四、古代巴渝琴文化特点
从以上给出的材料来看,古代巴渝地区能琴者不在少数。然而,今天即便对巴渝古琴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也主要津津乐道于重庆抗战陪都时期琴艺活动的繁荣,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高峰地位的取得并非完全一蹴而就的,如果在此之前没有一定的积淀、当地人文环境对琴文化无有一点接受度和认同感,外来琴文化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对接。巴渝文化自古以来滋养着琴文化在这里发生的土壤。尽管前面说到许健、唐中六等先生认为巴渝古琴在唐代已有地域特色的说法恐有偏颇,不过巴渝琴文化确实有着自己的本来面目。
首先,巴渝琴文化的发生、发展尽管大体上遵循中国琴文化史的进路,不过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发展史特色。从整个琴史来看,古琴从众多乐器中逐渐独立出来,演变为一个迥异于其他乐器的演奏和审美体系;琴艺活动(包括欣赏和演奏)主体由宫廷至贵族豪右再到普通士人乃至平民阶层,经历了一个跨越阶层的过程。巴渝琴文化发展大致也体现了这两点,从两汉豪强地主阶层蓄养的作为乐班成员之一的古琴演奏,到两宋士人化的琴文化书写,再到明清时期平民阶层琴艺活动的出现,巴渝琴文化与整个琴文化的发展脉络大体上是一致的。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巴渝地区历史上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环境变迁的历史特殊性,巴渝琴文化并不完全和中原琴文化同步。汉代抚琴类乐器俑所持器带有很强的楚文化特色;隋唐至北宋初期巴渝地区尚属于中原礼乐文化的边区,巴渝琴文化是以外来琴人为主导的;北宋后期恭州更名、南宋光宗时期由州升府等事件带来的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夔州路作为战略要地形势的逐渐凸显,加之移民的大量涌入,巴渝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文化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文人群体、书院和学派,本地琴文化在这样的土壤下才得以成长起来。此外,清中叶以后重庆商业贸易的发达、商业组织制度的完善以及民众“重商”意识的增强[72]促生了一批商业士绅,他们中不少参与了地方文化事业建设,晚清民国间琴事活动的中心在“天顺祥”杨氏家族中并非一个偶然现象,这与同样是商业之都的上海晚清民国时期琴文化形态颇有些类似。总之,古代巴渝琴文化是在中国琴文化大环境与地域文化演变的交互中发展的。
其次,巴渝琴文化的主体更基于文人琴的传统。琴史上自古有“文人琴”与“艺人琴”两大传统,反映着两种琴人的身份属性和审美取向。刘承华指出,“文人琴”是“以文人的身份弹奏古琴而形成的琴乐形态,这文人身份既指从事文学写作的诗人、作家,同时也包括学者、文人出身的官员、画家、书法家等从事文化职业的人,后来也可以包括一些有其他稳定职业的人士”[73]。“艺人琴”则是“以艺人身份,其中主要是琴人身份弹奏古琴而形成的琴乐形态,这琴人身份主要指朝廷乐官以琴待诏、权贵所养的琴客、以授琴为业的专职琴人和一些专攻琴艺的僧道琴家”[74]。就巴渝地区的琴文化来看,从贬谪到此的能琴士人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等到本地能琴士人李远、冯时行、阳枋、度正、来知德乃至石柱马氏土司家族,其身份都是士人,其操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修身养性。从阳枋“月白风清时自弹”到来知德“我有孙枝琴……不向人间弹”的表述都体现着这样一种“慰己”而非“娱人”的心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杨正经和竹禅和尚虽以琴名世,但前者时为掌宗庙礼仪的太常寺卿,与宋代的琴待诏有很大不同。另外其所从事的琴事活动都旨在践行儒家的忠孝节义,说明他本身也是以一个士的身份自许的。而竹禅和尚除琴艺以外兼善书画,从事琴与书画等艺事的目的是为了“说法”“参禅”,艺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总起来说,巴渝地区琴文化的主体是文人群体,其审美取向也更接近文人琴的审美取向。
结语
古琴自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热度与日俱增,而与这种热闹相反的是琴学研究的不完善不充分。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其身上承载了传统文化的诸多细节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正如清徐祺《五知斋琴谱》卷一《上古琴论》所云:“琴之妙道,岂小技也哉?而以艺视琴道者,则非矣。”[75]从琴史上看,琴道的传承主体一直是文人士大夫,这使得古琴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乐器而有了文化史上的地位。古琴文化与士人文化有了一种互文关系,由此作为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补充而有了独特的价值。
挖掘和研究地方琴文化是研究整个琴文化的分项和基础,不仅有着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更有其现实意义,对丰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大有裨益。古代巴渝琴史中有许多是非常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果充分挖掘能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例如梁平双桂堂深刻挖掘竹禅和尚生平和艺事资料,于2009年成立了竹禅琴社,并出版了《名家荟萃忆故人》音像制品,既弘扬了竹禅琴学,也将竹禅打造为梁平的一张文化名片,取得了社会效益。不过客观地说,类似的做法目前还很不够。其实,如唐代裴淑、元稹鸣琴黄草峡的佳话,宋明两代擅琴的巴渝理学家及其琴事,明末琴家酉阳杨正经等许多古琴文化资源就很有进一步开发的价值。像杨正经这样一位明末清初遗民中现象级的文化人物,在我们目前出版的重庆名人书典(如《重庆名人辞典》《重庆历史名人典》《重庆与名人》)中居然全部失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反映了此前相关研究的匮乏。而我们希望借助这股古琴复兴的热度,将颇具文化史意义的古代巴渝地区琴学资源挖掘出来,填补之前此项研究的空缺,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这部分文化资源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
[1]薛新力.重庆文化史(远古—1949年)[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17.
[2]唐冶泽.天风和畅——论抗战时期重庆“天风琴社”的成立[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09):5.
[3]唐中六.古巴渝地域的古琴考[J].天风环佩:重庆·2013中国古琴传承、保护与传播学术研讨纪实.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104-121.
[4][荷]高罗佩著,宋慧文、孔维锋、王建欣译. 琴道[M].上海:中西书局, 2013:1.
[5]乔建中.现代琴学论纲[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02):4-9.
[6]唐中六.古巴渝地域的古琴考[J].天风环佩:重庆·2013中国古琴传承、保护与传播学术研讨纪实.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104.
[7]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M].北京:中国 ISBN 中心, 1998:80.
[8]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
[9]李松兰.穿越时空的古琴艺术:蜀派历史与现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7.
[10]李洪财.抚琴俑及相关材料存在的问题初探[J].音乐探索,2016(01):65.
[11]李洪财.抚琴俑及相关材料存在的问题初探[J].音乐探索,2016(01):72.
[12]新编汉魏丛书编纂组.新编汉魏丛书[M].厦门:鹭江出版社,2013:189.
[13][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275.
[14][晋]常璩著;汪启明、赵静译注.华阳国志译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8.
[15][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8.
[16][汉]桓宽著,白兆麟译注.盐铁论注译[M].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142.
[17]李松兰.穿越时空的古琴艺术:蜀派历史与现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7.
[18]李松兰.穿越时空的古琴艺术:蜀派历史与现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14.
[19]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51.
[20]许健.琴史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12:144.
[21]唐中六.巴蜀琴艺考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41.
[22]薛新力.重庆文化史(远古—1949年)[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67.
[2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79:1485.
[24][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79:1485.
[25]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57.
[26][宋]朱长文.琴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0.
[27]毛水清.唐代乐人考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50.
[28]谢永芳.元稹诗全集汇校汇注汇评[M].武汉:崇文书局,2016:430.
[29]吴钊,伊鸿书,赵宽仁.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178.
[30]吴钊,伊鸿书,赵宽仁.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178.
[31][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85:13063.
[32]周勋初,葛渭君,周子来等.宋人轶事汇编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69.
[33]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804.
[34]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1170.
[35]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865.
[36]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748.
[37]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 [M].长沙:岳麓书社,2003:1071.
[38]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745.
[39]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 1999:5931.
[40]胡问涛,罗琴.冯时行及其《缙云文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272.
[41]郑敬东.重庆古文化资源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47.
[42]胡问涛,罗琴.冯时行及其《缙云文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9.
[43]胡问涛,罗琴.冯时行及其《缙云文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331.
[44]胡问涛,罗琴.冯时行及其《缙云文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39.
[4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 第35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69.
[46]曾枣庄,刘琳.全宋文 第35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72.
[47]曾枣庄.宋代序跋全编[M].济南:齐鲁书社, 2015:5555.
[48][清]永瑢,纪昀等篆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83册428b.
[49]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5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73.
[50][清]永瑢,纪昀等篆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70册167a.
[51]薛新力.重庆文化史(远古—1949年)[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83.
[52]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9辑[M].1982:156.
[53]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梁平县文史资料 第11辑 来知德诗赋选[M].2006:66.
[54]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梁平县文史资料 第11辑 来知德诗赋选[M].2006:219.
[55]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梁平县文史资料 第11辑 来知德诗赋选[M]. 2006:197.
[56][清]宋锦,刘桐纂修.合州志八卷.清乾隆十三年刻本:卷五.
[57][清]曾受一修,王家驹纂.江津县志.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卷十九.
[58]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164.
[59]周建华,谭宏永,马世凡.石柱文史资料 第9辑 吟秦良玉诗词联辑[M].1988:11.
[60]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5.
[61][清]丁治棠.仕隐斋涉笔[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8.
[62][清]佚名.江津县乡土志[M].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 第三册.成都:巴蜀书社,2009:24.
[63]《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 119 翁山文钞 翁山文外 雅坪诗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
[64]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07:113.
[65]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琴曲集成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311.
[66]《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 119 翁山文钞 翁山文外 雅坪诗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
[67]释克观.竹禅和尚生平及其艺术成就[J].佛教文化,2010(6):16-5.
[68]唐中六.清代著名琴僧竹禅上人琴艺考[J]. 曾成伟,杨晓主编. 蜀山琴汇 2013成都琴会论文集[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249.
[69]杜洁祥. 普陀洛迦新志[M].台北:明文书局, 1980:422.
[70]夏凡.“以琴说法”——<枯木禅琴谱·竹序>的佛理阐释[J].中国宗教,2013(08):50-51.
[71][清]顾玉成辑.百瓶斋琴谱[M].北京:中国书店,2015.
[72]薛新力.重庆文化史(远古—1949年)[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80.
[73]刘承华.文人琴与艺人琴关系的历史演变——对古琴两大传统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J].中国音乐,2005(02):9.
[74]刘承华.文人琴与艺人琴关系的历史演变——对古琴两大传统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J].中国音乐,2005(02):9.
[75]蔡仲德注译.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 增订版 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391.
[76]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7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77]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8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78]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9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79]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2000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80]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2001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81]重慶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2002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82]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83]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大坪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84]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忠县仙人洞与土地岩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85]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奉节白马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86]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二仙堡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87]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忠县邓家沱遗址与渔洞墓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88]张才俊.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J].文物,1985.
[89]陈艳,郭昌莲,裴健等.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Ⅲ区东汉墓葬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2008.
[90]严福昌,肖宗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四川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12.
[91]刘智、杨大用,重庆市合川区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编.合川馆藏文物精品图典[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