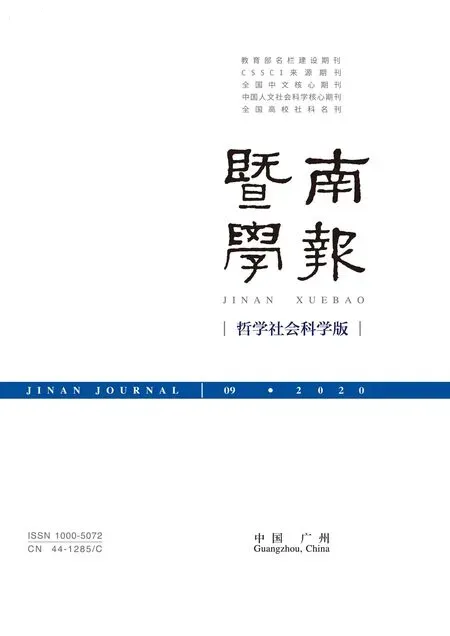南宋初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2020-09-14韩毅
韩 毅
南宋初年,受自然灾害、宋金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瘟疫曾数次暴发并广泛流行,不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灾民迁徙和土地荒芜,而且引起中央政府、地方官吏、医学家和社会民众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积极的防治措施。
学术界有关南宋初年瘟疫流行与防治措施的研究,尚无专文加以探讨。关于宋代瘟疫的研究,笔者在出版的专著和论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宋代新史料的发现、新墓志铭的出土和海外藏宋代珍稀医学文献的刊布,有关南宋初年社会各阶层防治瘟疫的措施,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重点探讨南宋初年建炎、绍兴年间(1127—1162年)中央政府、地方官吏、医学家、社会民众等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揭示社会不同阶层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历史借鉴。
一、南宋初年瘟疫的流行情况与重要影响
(一)南宋初年瘟疫的流行情况
瘟疫是一种发病急骤、具有强烈传染性且死亡率较高的疾病。宋代医学文献根据其发病时间、疾病特征和流行强度,称之为疫、大疫、疾疫、疠疫、疫疠病、疫病、天行温疫、湿疫、瘟疫等,多指“传染之病”的总称,包括疾疫、伤寒病、时气病、麻风病、天花病、肺痨病、痄腮病、痢疾病、疥癣病、瘴疫等传染病和地方流行病。
南宋建炎年间,金朝派兵南侵,引发瘟疫大流行。如建炎元年(1127年)二月,金朝军队围攻开封(治今河南开封)数月之久,“放兵四掠,东及沂,西至濮、兖,南至陈、蔡、颍,皆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泗淮之间荡然矣。京城之外,坟垄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造成开封“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三月,开封城内太学诸生“困于荠盐,多有疾病,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数十人者”;淮南东路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乡中大疫”。建炎三年(1129年),金朝骑兵攻破淮南东路楚州淮阴县(治今江苏淮安淮阴区),引发该地“疫疠大作”;同年,金军经过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时,“徙其官民北渡,时暑多疾疫,老弱转死道路”。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两浙西路湖州(治今浙江湖州)“大疫”;夏天,两浙西路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疾疫大作”。
南宋绍兴年间,自然灾害和战争引发的瘟疫时常发生。如绍兴元年(1131年),两浙西路常州(治今江苏常州)“大疫”;六月,两浙西路地区“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秋冬,两浙东路绍兴府(治今浙江绍兴)“连年大疫”。绍兴二年(1132年)春,夔州路涪州(治今四川涪陵)“疫,死数千人”。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荆湖南路永州(治今湖南永州)疫。绍兴三年(1133年),梓州路资州(治今四川资中)、荣州(治今四川荣县)二州“大疫”。绍兴四年(1134年),福建路漳州龙溪(治今福建龙海)发生“旱疫”。绍兴六年(1136年),四川疫。绍兴七年(1137年)秋七月,江南东路建康(治今江苏南京)“疫盛”。绍兴九年(1149年),行都杭州(治今浙江杭州)“大疫,汗之死,下之死”,南宋医家陈言认为此次疫病是“湿疫”。绍兴十二年(1142年),杭州疫。绍兴十五年(1145年)六月丙申,福建路漳州、泉州、汀州、建州接江西、广东之境官军,“不习山险,多染瘴疫”。绍兴十六年(1146年)夏,行都杭州疫。绍兴十九年(1149年),岭南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一带“瘴疫大作”。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成都府路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大疫,死者相藉,有亲族忌,不觇伺者”;同年,两浙东路永嘉(治今浙江温州)发生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往往顷时,寒疫流行”。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冬十月,临安府时气病流行。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夏,行都临安(治今浙江杭州)又发生瘟疫。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南侵,击溃淮河一线的南宋守军,随即抵达长江北岸,宋金发生“采石之战”,南宋军队“御敌而还”过程中,在两浙西路京口(治今江苏镇江)一带“遇疫”。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二月,江南东路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两浙西路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太平州(治今安徽马鞍山)、江南西路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江南东路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屯戍军兵,“近来多有疾疫之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金人围攻淮南东路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镇江都统张子盖(1113—1163年)奉命驰援,“战士大疫”。
南宋初年,金朝境内多次暴发瘟疫,并随金军渡河、渡淮、渡江而传播到南宋辖区,造成双方军民的大量死亡。如绍兴八年至十九年间(1138—1149年),金朝境内时疫疙瘩肿毒病流行,该病“生于岭北,次于太原,后于燕蓟,山野颇罹此患,至今不绝,互相传染,多至死亡,至有不保其家者”,系新出现的一种传染病,可能为大头天行病或鼠疫,“古方书所论不见其说,古人无此病”。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十八日,东京副留守刘锜(1078—1162年)上奏:“顺昌府累与金贼大兵接战,其酋首三路韩将军、龙虎大王等,皆缘败衄,往东京告急。至今月九日,四太子亲率大兵诸头项贼马并力攻围府城。于当日激励将士,戮力血战,杀死五千余人,及捉到活人,供通伤中者一万余人,往往身体黄肿,皆用骡马驮负北去;马中伤死者三千余匹。”此病发生在六月的京西北路顺昌府(治今安徽阜阳),症状为身体黄肿。绍兴十九年至绍兴二十二年间(1149—1152年),即金海陵王天德年间,“岁大疫”,河北西路广平(治今河北广平)尤甚,“贫者往往阖门卧病”。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即金海陵王天德三年,金朝“广燕京城,营建宫室”,张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施工,“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即海陵王正隆六年,金朝征发诸道工匠至京师(治今河南开封),“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始骚然矣”。
南宋初年暴发了数次动物传染病的流行。如绍兴五年(1135年),广西市马,“全纲疫死”。绍兴五年(1135年),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羊群中发生“大疫”。绍兴九年(1139年)秋冬之间,荆湖北路暴发动物瘟疫,造成大批动物染病而亡。庄绰《鸡肋编》卷下载:
绍兴九年,岁在已未,秋冬之间,湖北牛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麞、鹿、野猪、虎、狼皆死,至于蛇虺亦僵于路傍。此传记所未尝载者,若以恶兽毒螫之物自毙为可喜,而牛马亦被其灾,是未可解也。
可见,此次湖北境内发生的动物瘟疫,不仅造成家畜动物牛、马死亡,也造成野生动物麞、鹿、野猪、虎、狼、蛇等死亡。
(二)南宋初年瘟疫流行带来的重要影响
第一,瘟疫流行遍及全国诸路,尤以宋金交界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利州路一带最为严重,不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灾民流动,也引起了人们对疫病流行的恐惧。如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开封暴发瘟疫后,太学也未能幸免,“学校疾疫,无甚于今年,自春夏至此,亡者二百余人。初在学者七百余人,今殁故已三分之一矣”。建炎四年(1130年),两浙西路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甚至出现“举家病疫”的惨状。绍兴八年(1138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自中原陷没,东南之民死于兵火、疫疠、水旱,以至为兵,为缁黄,及去为盗贼,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
第二,瘟疫常常和其他自然灾害如地震、旱灾、水灾、畜灾等并发流行,文献中常用“震疫”、“旱疫”、“水疫”、“火疫”、“饥疫”等描述,对南宋初年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如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两浙西路湖州“大疫”,夏秋之际“旱,大饥,死者甚众”;夏天,两浙西路平江府“疾疫大作,米斗钱五百”。
第三,金朝南侵引起的宋金战争,以及金兵渡河、渡淮、渡江引起的人口南迁,引发靖康、建炎、绍兴年间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疫病的大流行,不仅造成大批宋金军民的死亡,也影响到某些局部战争的发展态势。如建炎元年(1127年)二月,金朝军队包围开封,造成“城内疫死者几半”。建炎三年(1129年),金朝军队经过江宁府时,将劫掠的宋朝官民迁徙北渡,“时暑多疾疫,老弱转死道路”。绍兴三年(1133),进犯利州路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洋州(治今陕西洋县)一带的金兵,在南宋刘子羽、吴玠的夹攻下,死伤十五之六,加之“粮日匮”和“涉春已深,疠疫且作”,金军“遂遁去”。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张浚(1097—1164年)在《论招纳归正人利害疏》中指出:“自往岁用兵,大军奔驰,疾疫死亡,十之四五。”可知,南宋初年由于疾疫流行造成的军民人员死亡,相当惊人,并影响到新兵队伍的扩充。

总之,南宋初年瘟疫的流行,主要是由自然灾害、宋金战争和社会因素等引起。尤其是长达十多年的宋金战争,多次引发瘟疫大流行。因此,重大疫病的流行和防治,不仅是一个疾病和医学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促使中央政府、地方官吏和医学家等积极地去认识疫病,寻找防疫之法,建立一个长期的、有效的疫病救治体系。
二、南宋初年政府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一)中央政府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1)医学措施。
其一,派医诊治,施散药品。
绍兴七年(1137年),江南东路建康(治今江苏南京)“疫盛”,秋七月甲申宋高宗下诏“遣医行视,贫民给钱,葬其死者”。《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二九记载甚详:
七月二十四日,诏:“建康府内外居民病患者,令翰林院差官四员分诣看诊。其合用药,令户部药局应副,仍置历除破。如有死亡,委实贫乏,令本府量度给钱助葬,仍具已支数申尚书省除破。”
宋政府在此次建康疫病流行期间,下令翰林医官局派遣医官4人前往诊治患者,其所用药品由户部下官府药局和剂局支付,病亡者尸体大多由官府出钱掩埋。
绍兴十六年(1146年)夏,行都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大疫。但秦桧为了粉饰盛世,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派官救济,另一方面却讳言瘟疫。六月二十一日,应尚书省建议,宋高宗下诏加以救治。《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三一载:
六月二十一日,尚书省言:“方此盛暑,虑有疾病之人。昨在京日,差医官诊视,给散夏药。”诏令翰林院差医官四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看诊,合用药令户部行下和剂局应副,候秋凉日住罢。
在此次应对临安府疫病中,宋高宗下诏翰林院派遣医官4人前往临安府城内外诊治病人,其所用药物由户部下和剂局支付,至秋天乃止。这项举措后成为一项制度,“每岁依此”,“自是行之至今”。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冬十月,临安府时气病流行。宋高宗发布《戒饬民间医药诏》:“访问今岁患时气人,皆缘谬医例用发汗性热等药,及有素不习医、不识脉症,但图目前之利,妄施汤药,致死者甚众,深可悯怜。据医书所论,凡初得病患,头痛、身热、恶风、肢节痛者皆须发汗。缘即今地土气令不同,宜服疏涤邪毒,如小柴胡汤等药,得大便快利,其病立愈。临安府可出榜,晓示百姓通知。”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夏,行都临安又疫,宋高宗拿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并下令医官将“小柴胡汤方”张贴在交通便利之处供民选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三三记载甚详:
六月二十一日,三省言:“初伏,差医官给散夏药。”上宣谕曰:“比闻民间春夏中多是热疾,如服热药及消风散之类,往往害人,唯小柴胡汤为宜。令医官揭榜通衢,令人预知。颇闻服此得效,所活者甚众。”沈该等曰:“陛下留神医药,其恤民疾苦可谓至矣。”
南宋熊克撰《中兴小记》卷三七也载:
时以初伏。辛卯,宰执奏:“差医官给散夏药。”上曰:“比闻春夏间民病,多是热疾,如服热药及消风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汤为宜。”曾令医官揭榜通衢间,服之者所活甚众。上留神医药,恤民疾苦如此。
宋高宗推荐的“小柴胡汤方”,最早出现于《伤寒杂病论》,用于治疗伤寒类疾病。宋代官修《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有记载,主治伤寒、温热病身热恶风,颈项强急,胸满胁痛,呕哕烦渴,寒热往来,小便不利,大便秘硬,或过经未解,或潮热不除,及瘥后劳复,发热疼痛,妇人伤风,头痛烦热,经血适断,寒热如疟,发作有时,及产后伤风,头痛烦热,并宜服之。其方剂组成,绍兴年间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半夏(汤洗七次,焙干,二两半),柴胡(去芦,半斤),人参,甘草(炙),黄芩(各三两),上为粗末。每服三大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枣一个擘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稍热服,不拘时。小儿分作二服,量大小加减。”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二月,江南东路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两浙西路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江南东路太平州(治今安徽马鞍山)、江南西路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治今安徽池州)屯戍官兵中发生疫病,宋高宗下诏加以救治。《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三七载:
(绍兴)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戍军兵,〔近〕来多有疾疫之人。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荆、襄、四川准此。”
此道诏令规定:一是命令诸路转运司划拨钱物,加强对军营中患病士兵的救济;二是让诸州守臣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配制药品,派遣职医分头诊治病人;三是命令荆湖北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等做好疫病预防,并按上述地区的救治措施加以应对。
其二,编撰方书,依方制药。
南宋初年,中央政府延续了北宋时期的传统,极为重视医学方书在瘟疫防治中的应用。如绍兴十九年(1149年)六月辛酉,右朝奉郎、知广南东路南雄州(治今广东南雄)朱同任满,他向朝廷上奏:“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毙。望取古今名方治瘴气者,集为一书,颁下本路。”宋高宗“从之”,采纳了朱同的建议,向广南地区颁布《治瘴气名方》。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二月乙卯,宋高宗下诏“诸州置惠民局,官给医书”。这里的医书,即绍兴年间编撰的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2)经济措施。
南宋政府在防治瘟疫过程中,经济方面采取了划拨资金、提供粮食、减免赋役、发放度牒等措施。
其一,划拨资金,提供粮食。
划拨资金,提供粮食,救治患病民众,是南宋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之一。如绍兴八年(1138年)秋七月,江南东路建康(治今江苏南京)疫病流行严重,宋高宗下诏“遣医行视,贫民给钱,葬其死者”。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六月辛丑,大理卿张柄面见宋高宗,指出“州县有岁赐药钱,以待军民所须,而奉行灭裂,但为文具,乞申严觉察”,宋高宗“从之”。
其二,减免赋役,发放度牒。
蠲免租赋,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是南宋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之一。如绍兴七年(1137年),江南东路建康(治今江苏南京)“疫盛”,秋七月甲申,宋高宗下诏“蠲诸路民户绍兴五年以前欠租。上旨也。坊场净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负亦除之”。
度牒是僧人合法身份的证明,具有法定的官府价格,宋政府常常通过发放度牒的形式募人掩埋病尸。如绍兴元年(1131年)秋冬,两浙东路绍兴府(治今浙江绍兴)“连年大疫”,宋政府“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十二月十四日,绍兴府通判朱璞上奏朝廷,请求以奖励度牒的方式鼓励医官诊治病人和僧人掩埋尸体。《宋会要辑稿》食货六〇之八载:
绍兴元年十二月十四日,通判绍兴府朱璞言:“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赈济。今乞委都监抄札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发入养济院,仍差本府医官二名看治,童行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将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以上,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给度牒一道;及五百人以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五十贯;二百人以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二十贯。并令童行分给。所有医官医治过病患人痊愈分数,比类支给。若满一千人,死不及一分,特与推恩。如有死亡之人,欲依去年例,委会稽、山阴县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闲官地埋葬,仍委踏逐官点检,无令暴露。其养济院及外处方到未曾入院病患死亡之人,去年召到僧宗华收敛,顾人抬棺出城掩瘗。令县尉监视,置历拘籍,每及百人,次第保明申朝廷,给降度牒。”
宋高宗采纳了朱璞的建议,下诏“每掩瘗及二百人,与给度牒一道,余依所乞”。
(3)政治措施。
南宋政府在防治瘟疫过程中,政治上采取了保证信息渠道畅通、奖励防疫救治官民、调整官吏选任方式、遣使祭祀、分封诸神等措施。
其一,保证信息渠道畅通。
政府是否决定对疫病采取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时和准确。因此,南宋初年极为重视信息渠道的畅通,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如绍兴七年(1137年),江南东路建康(治今江苏南京)“疫盛”,秋七月甲申宋高宗下诏“命疏决滞狱”;秋七月丁亥,宋高宗下诏“今后士民陈献利害,令给舍子细看详,其可采者取旨施行”。
其二,奖励防疫救治官民。
南宋政府对参与疫病救治的官吏和民众,按其救活人数予以奖惩。如绍兴四年(1134年),福建路漳州龙溪县(治今福建龙海)发生“旱疫”,龙溪主簿卓先(1146—1229年)多方救治,全活甚多,宋政府擢升其为“建宁军节度推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辛亥,镇江都统张子盖救援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军中大疫,医学家王克明(1112—1178年)时在军中,医活者几万人。经张子盖奏闻,宋政府授予王克明“额内翰林医痊局,赐金紫”。
其三,调整官吏选任方式。
南方地区瘴疫的流行及其带来的高病死率,迫使南宋政府对瘴疫流行地区官员和军队的换任方式做出适当调整。如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六日,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曾统上奏:“本路州县水土恶弱,多是阙官,至有差摄癃老疾病及疲懦不任事之人,(乞)令提刑司于本路见任官内选择,两易其任,见阙正官处令逐司奏辟。”宋高宗“诏依。如徇情移易及奏辟不实者,并依上书诈不实科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八月十三日,沅州知州秦杲上奏:“卢阳、黔阳、麻阳三县各接傜僚生界,及接广南,系水土恶弱瘴烟之地,县令任满循两资。今乞比照本州幕职官与改合入官,或止依判司任满该磨勘,与减举主二员。”吏部勘当:“欲将三县县令依见行赏格推赏,如任满得替应磨勘改官人,任内不曾透漏蛮贼五人以上入界,即与依本州判司减举主二人,不愿减(举)主者听与循资。”宋高宗“从之”。
其四,遣使祭祀,分封诸神。
宋代盛行的多神信仰崇拜也影响到政府的疫病救治,对于防疫中起到独特作用的“神灵”或“历史人物”,宋政府多次给予加封,提高其祭祀地位。相较而言,南宋时期的封神活动次数较多,敕封地区较广,敕封人物较多。如绍兴三十年(1160年),鉴于城隍庙“岁之丰凶,时之水旱,民之疾疫,求焉而必应”的情况,宋高宗发布《封保顺通惠侯敕》,册封杭州宝月山城隍庙庙主为“保顺通惠侯”。《咸淳临安志》卷七一《祠祀一·土神·城隍庙》载:
敕曰:“钱塘为郡尚矣,自版图归于我家,逾二百年,维城与隍,必有神主之,况岁之丰凶,时之水旱,民之疾疫,求焉而必应者哉!不知郡历几将,而无一牍之奏,以答神之休意者。聪明正直,交感于幽显之间,固自有时也。朕今驻跸于此,视之不异畿甸,重侯美号,用疏不次之封。其歆其承,永妥尔祀,可特封‘保顺通惠侯’。”
此后,南宋皇帝屡次颁诏册封杭州城隍庙。乾道六年(1170年),宋孝宗颁诏“加封城隍庙”。咸淳八年(1272年),宋度宗发布《改封保顺通惠侯为辅正康济广德显圣王诏》,改为辅正康济广德显圣王。
(二)地方官吏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南宋初年,地方官吏在防治疫病中采取了亲临疫区、派医诊治、施散粥药、打击巫术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
(1)亲临疫区,派医诊治,施散粥药。

(2)打击巫术,加强社会管控措施。
宋代巫术在地方和民间的流行及存在,造成部分地区民众在疫病流行期间不敢寻医,不敢视疾,不敢服药,甚至出现遗弃亲属的行为,严重地威胁到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和地方政府的救治活动。为了有效地防控各类疾病的流行,宋朝地方官吏对“巫术”的非法活动采取了打击、控制和改造的措施。
绍兴六年(1136年),曾慥在《类说》一书中将巫术列为“七害”之一,认为:“巫蛊左道、诱惑良民者,必止之。”绍兴年间,李忠任淮南西路无为军无为县(治今安徽无为县)县令,“南方信禨,虽至父母疠疫,子弃不敢侍”,李忠指出:“冬伤于寒,春必病瘟理也,尔乃不问医而问巫,愚亦甚矣。”于是加以变革,“故时有疫则必家至,与之善剂,日候其安否。其贫不能自存与死无以自葬者,皆悉力营给之,恶俗为变”。 陆宲任两浙东路台州宁海县(治今浙江宁海)县丞时,当地“巫以淫祀惑民”,陆宲“悉捕寘扵法,习俗为变”。
总之,宋代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在防治瘟疫过程中,其采取的举措主要以派医诊治、施散药物、赈济病民、减免租赋、调整官吏选任方式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为主,其中赈济病民和免费赐药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官修医学方书的编纂与推广,官府药局药品的生产与应用等,在一定范围内对控制瘟疫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南宋初年医学家和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一)医学家防治瘟疫的措施
南宋初年,医学家许叔微、王克明、刘昉、张锐、窦材等对瘟疫、斑疹伤寒、天花病、麻风病等传染病给予了详细的观察和记载,留下了大量临证医案和验方、效方。
关于瘟疫的防治,南宋初年医家关注较多。如建炎元年(1127年),淮南东路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乡中大疫”,医学家许叔微(1080—1154年)“遂极力拯疗之,往往获全活者颇多”。其所撰《普济本事方》“伤寒时疫”,收载了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温粉方、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柴胡汤、白虎加苍术汤、黄芪建中加当归汤、海蛤散、真武汤、清心丸、竹叶石膏汤、白虎加人参汤、肉豆蔻汤、良姜汤、滑石丸、茵陈蒿汤、五苓散、瓜蒂散等50余首防疫名方。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金朝骑兵攻破淮南东路楚州淮阴(治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疫疠大作”,时有王姓朝奉郎寓天庆观得疾,“身热自汗,体重难以转侧,多眠,鼾睡,医作三阳合病,或作漏风症,治之不愈”,许叔微诊断后指出“此风温病,投以葳蕤汤、独活汤,数日瘥”。 风温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热变最速,多按卫气营血规律传变,最易伤津耗液。绍兴九年(1139年),杭州大疫,其症状为“汗之死,下之死”。医学家陈言指出:“此无他,湿疫也”,遂开五苓散,患病民众服之“遂愈”。
斑疹伤寒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以出红色、黑色斑点为症状,伴有寒战、高热、剧烈头痛、肌肉疼痛等,死亡率较高。绍兴年间,医学家许叔微在《伤寒九十论》中指出:“若热毒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其热乘虚入胃,则胃烂。然热入胃,要须复下之,不得留在胃中也。胃若实为致此病,三死一生。其热微者赤斑出,剧者黑斑出。赤斑出者五死一生,黑斑出者十死一生,但看人有强弱耳。病者至日,不以时下之,热不得泄,亦胃烂斑出,盖此是恶候。”绍兴二十年(1150年),刘昉《幼幼新书》引《斑疹候》,指出此病极为难治,“伤寒毒传胃而成。其候有疹,有麻,有痘,其实一体。时多哭叫,手脉来大,浑身甚热,两耳尖冷,鼻准冷,饮水多吐,宜发出其疮。大为阴,小为阳。”歌曰:“胃热成斑疹,须知此病由。哭多心壅极,舌黑是堪忧。肿满来双水,红涎谷道流。变成如此候,一见命须休。”在“伤寒发斑”中,刘昉列出了《太平圣惠方》、《南阳活人书》、《汉东王先生家宝方》、《仙人水鉴方》所载大青散、犀角散、大黄散、毒黛散、麦汤散、透关散、败毒散、葛根橘皮汤、黄连橘皮汤、化斑汤、元参升麻汤、阿胶大青四物汤、猪胆鸡子汤、仲景调胃承气汤等20余首验效名方。
痘疮病,也称虏疮、豌豆疮,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尤以小儿易患此病,“小儿时行疮豆,恐相传染”。现代医学称此病为天花病。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太医局官校佚名撰《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明确指出痘疮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家有数儿,一儿既患,余儿次皆及之。便当为备以防之,以秽气转相传染也。”其治疗药物有升麻葛根汤、消毒散、 紫草饮子、化毒汤、 人参散、紫草如圣汤、黄柏膏、胡荽酒、鼠粘子汤、紫草散、必胜散、龙脑膏子、安斑散、快斑散、抱龙丸、《小品》犀角地黄汤、木香汤、猪胆醋、莱菔汁、紫茸汁、活血散、蝉蜕饮子、四圣散、川芎升麻汤、解毒汤、黑龙散、白虎化斑汤、神通散、如圣散、七神散、宣毒膏、猪血脑子、人齿散、白母丁散、桃胶汤、百祥丸、牛李膏、金液丹、调肝散、兔肝圆、龙蛤散、煎柿散、仙灵脾散、珍珠散、浮萍散、蛇蜕散、仙术散、煮肝散、如圣汤、紫雪、通关散、甘露饮、青黛、败毒散、牛黄散、升麻汤、青金散、清凉饮子、神朱散等64首验效方剂。
大风癞疾,也称癞病、恶疾、大风疾,是一种严重的皮肤传染病,现代医学称其为麻风病。癞病在宋代流行较为广泛,患者深受其苦。绍兴三年(1133年)成书的张锐《鸡峰普济方》所载胡麻散,主治癞病。绍兴十六年(1146年)成书的窦材《扁鹊心书》,在癞病的治疗方面充分发挥针灸的功效,并辅以药物治疗。绍兴年间刊行的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载有3首治疗大风癞疾的方剂:第1方,蓖麻法,治厉风手指挛曲,节间疼不可忍,渐至断落。其方为:“蓖麻(去皮),黄连(锉,如豆,各一两)。上以小瓶子入水一升同浸,春夏三日,秋冬五日,后取蓖麻子一粒,擘破,面东以浸药水吞下,平旦服,渐加至四五粒,微利不妨,水少更添,忌动风物,累用得效神良。”第2方,柏叶散,治厉风。其方为:“柏叶,麻黄(去根节),山栀子(去皮),枳壳(去穰,锉,麸炒),羌活(去芦),羊肝石,白蒺藜(炒,去角),升麻,子芩(去皮),防风(去钗股),牛蒡子(隔纸炒),荆芥穗,茺蔚子,大黄(湿纸裹,甑上蒸,各半两),苦参(一两),乌蛇(一条,酒浸,去皮、骨,焙干)。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水调下,日七八服。庞老方。”第3方,绿灵散,治肺毒疮,如大风疾。其方为:“用桑叶洗熟蒸日干为末。水调二钱服,日四五,无时。出《经验方》。”
(二)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措施
宋代民间地方乡绅、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对瘟疫的态度和防治措施较为复杂,通常采取捐献钱粮、赈济病人、施散药物或逃亡躲疫等措施。
(1)捐献钱粮粥食,赈济病人。
在瘟疫流行期间,某些地方民众会捐献钱粮粥食,赈济病人。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成都府路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大疫,“死者相藉,有亲族忌,不觇伺者”。广汉民众杨椿(1122—1155年)“多技能,尤工于琴与医、指法及脉法,往往自得”,于是积极加以救治,“不择高下,往赴无惮,家人惧甚,拘是不得出,则谬为他适,其人多赖以活,亦不自以为德也。间持缗币适市,遇贫急探怀袖与之,不省问谁氏”。
(2)宣传官府医书,依方治病。
某些地方民众精通医药,积极宣传官府医书,依方治病。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南侵,击溃淮河一线的南宋守军,随即抵达长江北岸,宋金发生“采石之战”。十一月,在中书舍人、直学士院虞允文(1110—1174年)的指挥下,南宋军民打败金军,挫败了金军从采石矶渡江南侵的计划。南宋军队在“御敌而还”过程中,在两浙西路京口(治今江苏镇江)一带“遇疫”,京口名医艾钦之积极加以救治,“视证惟香苏饮为宜,而病者多莫能家至,则置锜釡煮药于庭,来者饮之,或恣所酌取,人以全活”。香苏饮,见于绍兴年间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二《绍兴续添方》,治四时瘟疫、伤寒。其方剂组成为:“香附子(炒香,去毛),紫苏叶(各四两),甘草(炙,一两),陈皮(二两,不去白)。右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七分,去滓,热服,不拘时候,日三服。若作细末,只服二钱,入盐点服。”
(3)逃亡躲避瘟疫,求助神灵。
普通民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生活穷困,缺衣少食,对疫病充满了强烈的恐惧,他们大多采取了逃亡躲疫或求助于神灵的措施,显示了面对瘟疫时的无奈。如绍兴十二年(1142年),杭州瘟疫流行,当地百姓求助于蒋通神,奉而祀之。清梁诗正纂《西湖志纂》卷五《南山胜迹中》载:“灵应庙,在小麦岭饮马桥侧。《成化杭州府志》:神姓蒋名通,事亲至孝,宋绍兴十一年七月即小麦岭桐木之下端坐而逝,七日如生,观者惊异。次年疫作,有父老梦神衣紫横金曰:‘疫不侵此境。’于是奉而祀之。”
四、南宋初年防治瘟疫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借鉴
(一)重视各级官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的核心作用
南宋初年,宋朝建立的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仍然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其中宋政府建立的各级官府机构积极参与救疗并发挥了显著作用,对疫病救治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地方乡绅、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通过酬以官爵、授予医职或赐予封号等措施,将其纳入到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之中;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救治的范围大多集中在乡村,以个体活动较多,弥补了官府力量未到达的地域。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城乡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因分散在基层,有关治病、施药、熬粥等救济活动更为直接,发挥的效果也较为明显。
(二)重视医药学知识在防治疫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南宋初年,政府极为重视医学方书的编撰及其疾病防治中的应用。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二月十七日,户部员外郎李涛面见宋高宗,指出:“近置诸州惠民局,虑四方药方差误,望以监本方书印给。”宋高宗采纳其建议,下诏“将太平惠民局监本药方印颁诸路”。此次校勘、增补后的新方书为《增广校正和剂局方》,也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共5卷,目录1卷,增补《绍兴续添方》72方,全书共369方。此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就成为南宋各级官府、药局和医学家制造药品和防治疾病最主要的医学著作之一,如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柴胡石膏散、圣散子、林檎散、升麻葛根汤、葛根解肌汤、香苏散、柴胡升麻汤、神术散、来苏散、十神汤等,是宋代有名的治疫名方,至今仍用于临床。
药品是南宋政府防治瘟疫最重要的物资之一,由官府药局和剂局生产。每有重大瘟疫流行,南宋政府通常下诏户部从和剂局中支付,或拨钱从民间药铺中购买。如绍兴六年(1136年)正月四日,宋高宗应户部侍郎王俣之请,下诏“置行在和剂局,给卖熟药用”。绍兴十八年(1148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宋高宗下诏将和剂局更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二月乙卯,宋高宗“诏诸州置惠民局,官给医书”;十二月十七日,宋高宗下诏“以监本药方颁诸路”,成为官府药局、民间药铺和医家制造成药的法定处方。
(三)重视医学机构在防治疫病中的管理及应用
南宋初年,朝廷建立的医学机构如翰林医官局、太医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院等,在防治瘟疫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绍兴十六年(1146年)十一月五日,宋高宗宣谕辅臣说:“居养、安济、漏泽,先帝之仁政。居养、安济已行之矣,惟漏泽未曾措置,宜令条具添入。”十二月十四日,给事中段拂上奏:“仰惟国朝爱育元元者,垂意甚备。以居养名院,而穷者有所归;以安济名坊,而病者有所疗;以漏泽名园,而死者有所葬。行之累年,存殁受赐。望申饬有司,讲明居养、安济、漏泽之政,酌中措置。令可久行,务使实惠,均被远迩。”宋高宗下诏“令户部看详,措置申尚书省”。可见,南宋初年安济坊仍旧是政府用作收留病人、隔离病人和治疗病人的重要机构,漏泽园是掩埋尸体的场所。
五、结 语
南宋初年防治瘟疫的措施,不仅承袭了北宋时期形成的以各级官府为主、社会民众为辅的防疫体系,也开创了南宋时期防治瘟疫的新局面,对南宋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央政府、地方官吏、医学家和社会民众等在防治瘟疫的过称中,除继续采用传统的赈济措施外,对医药学知识给予了高度重视,“按方剂以救民疾”和“依方用药”仍是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