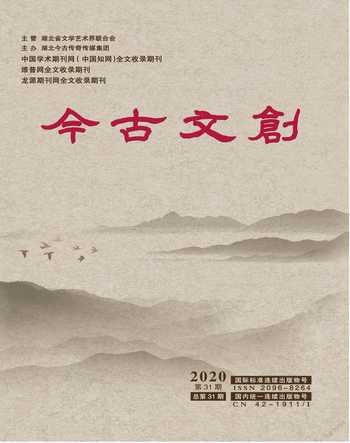《为奴隶的母亲》中秀才形象分析
2020-09-10朱雯婷
朱雯婷
【摘要】 本文通过《为奴隶的母亲》的题材及故事情节推测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由当时经济状况,论述秀才赠送春宝娘的两块钱对春宝娘的重要性,通过两块钱的重要性以及两者的生活遭遇阐述秀才对春宝娘的特殊感情,即在无情背后的有情。《为奴隶的母亲》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典妻”题材中的著名作品,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刻画阐发了作者對上层人物的态度。作品《为奴隶的母亲》从文中人物到创作者都体现出人性的美好品质。
【关键词】 为奴隶的母亲;知识分子;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1-0036-02
柔石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为奴隶的母亲》,是“典妻”题材的杰作,以女主人公春宝娘两度身不由己地离开亲子为线索,刻画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没有人权的悲惨命运。
一、由“典妻”知时代
“典”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1],这里的“典”是名词,直到唐代才逐渐产生作为动词“典”的用法。
能找到较早的“典”的动词用法是在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其含义是一方将土地、屋子等东西典质给另一方使用,以换得一笔财物,不需要付息金,约定年限,到期收回原物。
“依据抵押”是动词“典”的基本意思,“典妻”的含义与“典”的含义稍有差异,“典妻”是指无法满足生活基本要求的一方,将自己的妻子作为物品抵押给另一方,妻子常作为另一方生养孩子的工具,在双方都满意对方提出的要求并商议完年限后,一方获得另一方支付的钱财,另一方获得一方提供的妻子,到期另一方归还一方的妻子,如果另一方还有需要,可适当延长归还的时间并支付给一方相应的钱财。
《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就是被当作物品典当给秀才的。“典妻”制度向上可以追溯到宋代,《中国婚姻史》中记录,“典雇妻妾之风,始于宋元之际,观于元世祖时,元朝对南方典雇妻女风俗之请牒云云。”[2]从始至终,上层统治者对“典妻”这一风俗是不支持的,但明清之际,“典妻”之风不减,甚至呈现出越演越烈的局势,直到新中国成立,“典妻”的习气才逐渐消失。
《为奴隶的母亲》中,皮贩因自身生活贫困、王狼逼迫以及沈家婆引诱,决定将妻子典当给秀才。沈家婆作为皮贩和秀才的中间人,虽然也是一名女子,却从事剥削女子的工作,“但妻——虽然是结发的,穷了,也没有法。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3]她一面向皮贩灌输妻子是可以被舍弃的思想,一面又向皮贩推荐秀才,“有一个秀才,因为没有儿子,年纪已五十岁了,想买一个妾……年纪约三十岁左右,养过两三个儿子的。”[3]
沈家婆作为一个中间人,催促皮贩答应她的提议,这其中确实有皮贩想要典妻的原因,但沈家婆也是“功不可没”的。
秀才想要典一个妻子,秀才娘子就找沈家婆,说明沈家婆不是第一次参与“典妻”,而是一个“老手”。如此一来,就可以知道“典妻”在当时是很常见的。
春宝娘问皮贩是否要将自己典当,皮贩回答“只待典契写好”[3]。“典契”的存在,证明“典妻”有一定的程序,进一步说明“典妻”制度的民间合法性。因此,《为奴隶的母亲》的背景大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典妻”制度没有消失前。秀才在沈家婆嘴里是一个好归宿,“那边真是一份有吃有剩的人家。”[3]通过沈家婆对秀才的称呼和对秀才的形容,推测出《为奴隶的母亲》的背景大概是在清朝被推翻后,而作品后半部分出现的对钱的称谓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为奴隶的母亲》的时代背景应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二、由时代知经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中国受外来侵略者欺辱,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遭到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各地军阀纷纷而起,物价水平在两相冲击下飞快增长。当时,银币分为银元和角币,一元等于十角,相当于一百分,即一千厘,而一厘可以购买半个馒头,一元就可以购买五百个馒头。这样一来,一元对于底层农民家庭而言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为奴隶的母亲》中,在春宝娘回到皮贩家的当天,秀才给了春宝娘两块钱,“拿去罢,这两块钱”[3],秀才除了没有讨回青玉戒指,还额外赠送春宝娘两个月的生活费,这一行为与剥削底层劳动人民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罪恶形象是不符合的,但作者柔石却故意将秀才与赠送两块钱的行为联系起来,其目的是表现秀才对春宝娘特殊的情感,进而表达自己对秀才这一人物的独特感情。
三、由经济知感情
春宝娘是作为物品典当给秀才的,在秀才家里,春宝娘作为生育工具而存在。因此,皮贩和秀才对于有用处的器物——春宝娘,是不会也不该产生感情的。但在《为奴隶的母亲》中,柔石通过对秀才行为的描写,表现出秀才对春宝娘隐秘的情感。
秀才在春宝娘生下秋宝后,瞒着自己的大妻给春宝娘青玉戒指。这只青玉戒指的存在,大妻是不知道的,“我有一只青玉的戒指”[3],但作为“典妻”的春宝娘却获得了秀才的青玉戒指,还拥有了戒指的使用权,虽然秀才在得知青玉戒指被春宝娘给了皮贩后很生气。“那只戒指是宝贝,我给你是要你传给秋宝的。”[3]但从他的言辞中,也能推测出他对春宝娘的感情。
他说“要你传给秋宝”,作为“典妻”的春宝娘在被典卖的时候就签好了典契:“年数呢,假如三年养不出儿子,是五年。”[3]
依据典契,春宝娘在秀才家的时间短则三年,长则五年,这与秀才的言语不符,他要春宝娘将青玉戒指传给秋宝,不可能将戒指传给一个孩子,如果秀才的真实意图就是如此的话,那青玉戒指根本没有需要给春宝娘,而秀才提出青玉戒指是他希望通过春宝娘传给秋宝的,那么秀才就隐含着想要将春宝娘长久留下来的意图,这表明秀才要违逆大妻。
大妻不希望秀才娶妾,所以她才找“典妻”,秀才无奈答应,因为秀才畏妻,“哎,一向实在太对她好了……所以今日,竟和娘娘一般地难惹了。”[3]但面对大妻的反对,秀才却愿意与大妻抗争,这表现了秀才在与春宝娘相處的过程中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纯粹的爱情,而是一种欲望、一种悲悯恻隐之情,甚至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复杂情绪。但无法辩驳的是,秀才对春宝娘有了真情。
数见不鲜,虽然春宝娘将秀才的青玉戒指给了皮贩,但秀才并没有将这件事张扬出来,甚至在春宝娘离开时主动提出给春宝娘两块钱。皮贩家的生活是困苦的,早在作品一开始就有所体现,皮贩因为贫困染上恶习,被王狼催债,因此而典妻,生活的困苦导致皮贩人性的扭曲。皮贩的贫穷与秀才的富足和文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同样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春宝娘受到了不一样的对待。
春宝娘从秀才家到皮贩家时受到了皮贩的冷嘲热讽。“男人冷笑了一声,答说:‘你真在大人家底家里生活过了!’” [3]
皮贩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贫困农民的形象出现的,但相较于农民的淳朴老实,皮贩是冷漠残忍的,“会生疏得那么快,一顿打呢!”[3]由皮贩的言语和心理活动可知,在春宝娘离开春宝后,皮贩通过打骂春宝的方式使春宝遗忘春宝娘,这又和秀才对秋宝的万分重视形成了对比。
一个对于自己亲生骨肉都没有情感的男人,对于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妻子更是无情,这从他轻易典妻可以一窥究竟。相反,秀才对春宝娘可以说是殷勤备至。
四、由感情知遭遇
春宝娘是一个被丈夫随意抛弃的底层女性,她受到命运的不公平对待。作为上层知识分子的秀才,受到大妻的压迫,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因此,秀才对春宝娘有同病相怜的同情,他对春宝娘的感情有怜悯,是他对自己的怜悯,但他无法和其他人交流自己的不幸,因为他的大妻太厉害了,他无能为力。而春宝娘的出现使得他有了可以交流的对象,春宝娘沉默老实,是可以诉说的对象,而且两人有着相同的不幸,可以理解对方的悲伤。
秀才对春宝娘的感情还有男性对女性的欲望。秀才是五十多岁的男人,而他的大妻又要比他大,这自然是无法满足秀才对情欲的渴望的,精神压迫和情感压抑,使秀才对春宝娘没有抵抗能力,春宝娘只有三十岁左右,可以满足秀才对欲望的遐想,而在灵与肉结合过程中,“灵”无法摆脱“肉”,这也是秀才在接触春宝娘后逐渐对她产生感情的主要原因。
再者,秀才本身对孩子的渴望,使两者长期接触,秀才除了发泄长期难以满足的欲望外,也和春宝娘交流,而这两方面增加了秀才对春宝娘的感情。
秀才对春宝娘的感情还有感激。秀才渴望拥有一个孩子,但大妻生下的孩子早夭,他们一直处于期盼孩子的生活中,却没有达成愿望。可是,春宝娘在三年中使得他们长期没有实现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秀才的欣喜也是对春宝娘的感激。秀才为秋宝绞尽脑汁地取名字,正是因为他长期处于无子的痛苦中。
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刻画了长期到生理压抑、妻子控制和精神压迫的小知识阶级形象,通过知识分子对受到不幸的底层女性的怜悯同情,表现了自己对底层女性的不幸命运的同情。同时,也是由人性出发,柔石以同情的笔调刻画了秀才的形象。
故而,《为奴隶的母亲》从底层女性到上层阶级再到作者本身,在情感上,都呈现出和谐的统一,即对不幸人民的同情,都体现出人性的美好。
参考文献:
[1]柴剑虹.中国古典名著百部[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270.
[2]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12(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08-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