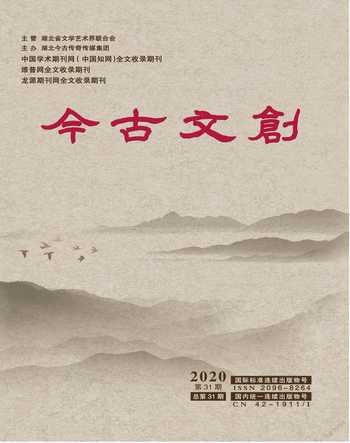论《诗经》在汉代的文化影响
2020-09-10李书姝
李书姝
【摘要】 《诗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经典,汉代则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汉代诗学以经学为基础,围绕《诗经》又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别,对后世《诗经》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不单指文学,这是一个集政治、思想、文学等多个方面为一体的概念。所以本文将以《诗经》的经学化为基础,从政治、道德和文学三个方面立体分析《诗经》在汉代的文化影响。
【关键词】 《诗经》;诗学;经学;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1-0027-03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计305篇,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即“国风”,指的是乡土之音,收录周朝各地的地方民歌共160篇,又被称为“十五国风”;《雅》包含“二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指的是周人的正声雅乐,朝廷之音,都是典范性的乐曲;《颂》包含“三颂”,即《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皆为宗庙之音。孔子提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世在传诵过程中便又称其为《诗三百》,直至汉武帝将《诗》列为五经之一,才正式改称为《诗经》。
汉代对《诗》的理解建立在先秦诗学的发展背景之下,当时的春秋赋诗断章、政治传统和礼义文化对汉人的诗学观念的形成影响极大,尤其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几位大家的观点提出直接影响了汉代诗学的发展。
汉初传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主要分布于民间,口耳相传或者以竹帛记载,按地域小范围流传,整体呈现无序状。至汉武帝时期,《诗》成为五经之一,设置五经博士,《诗》学研究的经学色彩浓厚,有了稳定的传播系统,这才逐步发展,并在后期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自西汉时期发展,以《鲁诗》《齐诗》《韩诗》(简称“三家诗”)为主要代表,首先在西汉时期获得大量关注,占据主导地位,属于官学;古文经学以《毛诗》为主要代表,属于私学,直至东汉才受到重视,但是影响更为深远,相关研究延续至清朝,比今文经学更加具有承上启下的意味。虽然古今文经学在学术思想和精神方面有所区别,但是两派以《诗经》为基础的研究论述,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经》在汉代的发展主要以诗经学为依托,整体上呈现出以历史化为基础的经学化和政治化,但是除了政治教化和道德人性方面的影响,其文学价值也应该得到肯定。接下来,本文将从政治教化、道德人性和文学价值三个方面分析《诗经》在汉代的文化影响。
一、汉代《诗经》的政治功能
《诗经》是西周礼乐政治文化的产物,它的政治功能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自秦、西周时期流传下来,在汉代扩大了影响范围。
《诗经》中含有许多劝谏作品,主要集中在“二雅”中,是贵族用来对君王进行劝谏的,比如《小雅·节南山》中“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直谏斥责尹氏失政;《大雅·民劳》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描写了百姓极度困苦疲劳,目的是劝谏周厉王要体恤民力。这种文字直白的驳斥是因为先秦时期的君主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西周时期更是建立了宗法制,任职的卿大夫大多是与君主有血缘关系的贵族,他们在劝谏时以直谏为主,主要形式就是“献诗”。
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官员“行人”去民间“采诗”,以这样一种朴素的方式将民情反馈给君王。所以“献诗”和采诗是当时干预政治的两种主要方式,互为补充。但是从秦朝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开始,西汉汉武帝加强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客卿制取代世卿制,君臣关系就不复之前的较为平等的师友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臣子对君王单方面的依附,形成了完全的上尊下卑。虽然汉武帝“独尊儒术”,但是“直谏”已经不符合当时君臣关系的需求,“讽谏”应运而生。
“讽谏”也可写作“风谏”,即用诗歌对君主进谏,这两种用法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所出现,各家对“讽谏”也都进行了积极讨论,其中以班固在《白虎通·谏诤》中讨论的最为具体,他认为“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说明当时人们认为讽谏是一种兼具智慧和艺术性的进谏方式。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以“美刺论《诗》”,即将诗与历史事件相结合,以史证《诗》,为劝谏增添信服力的同时将《诗》与时代朝代更替、政治变化紧紧捆绑在一起。虽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同一篇诗歌是“美”还是“刺”的理解不相一致,但是美刺是手段,教化諷喻是目的,这是一致的。古文经学表现得尤其明显,《毛诗》在每首诗之前都注有一篇《序》,便是用美刺讽喻来解诗,《关雎》前的《毛诗大序》更是将“风谏”的诵读之意缩小,强化了这个词的政治色彩,使《诗》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汉代儒生更加积极地将《诗经》整体政治化。
除了上文提到的贵族直谏之作,《大雅》《小雅》中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点评时政、表现民生的作品,比如《大雅·召旻》: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贼内讧。昏椓靡共,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贬。
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我相此邦,无不溃止。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职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职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此诗共七章,首章责问天子,次章痛骂奸人,第三章感叹自己位低权小无法制裁奸人,第四章将天灾与人祸联系在一起,第五章针砭小人,第六章痛心疾首希望周幽王认清现状的残酷,最后一章怀念前代清流功臣。全诗层次丰富,主题明了,就是痛斥周幽王祸国殃民,抒发了诗人嫉恶如仇的愤慨,表现出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其他诗歌,比如《小雅·北山》《小雅·四月》等,展现了作者痛恨劳逸不均,或表达个人悲痛心境,都是以个人感怀来表现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以及委婉表现对君主的不满。汉代儒生以讽谏的角度切入,将部分诗歌的劝谏功能无限扩大到整部《诗》,直接把《诗》用作了政治工具。比如《小雅·苕之华》写的是下层人民在慌乱年月中的痛苦,而《魏风·硕鼠》是为了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这些诗篇虽然可以表现出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引起统治者的警戒,但绝不是为劝谏而作,更不要说将一些表达男女情感的诗,比如《郑风·子衿》等强行套上劝谏的外壳,还是委婉劝谏的外壳,确实过于牵强。
今文经学以灾异说诗,一方面是因为《诗经》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描述灾害的文字,并且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对统治者行为有失的惩罚。比如《小雅·十月之交》中“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描写了自然地貌的突然巨变使得百姓不得安宁、灾难不断,还有《小雅·雨无正》中“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把自然灾害导致的民不聊生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宦官扰乱朝政的情况与《诗经》中描写的政治乱象较为符合,满足了经学家以此为发散点,警示统治者的目的。
二、汉代《诗经》的道德教化
上文有所提及,《诗经》自产生就自带礼乐文化的教化功能,承载了先秦时期的以礼义教化人和人伦秩序的精神内核,正所谓“以诗为教”,汉代围绕《诗经》建立诗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进行道德教化。
这一点可以从古文经学的代表作品《毛诗》中充分体会。《毛诗》以《诗经》为依托,具有极强的人伦教化和道德教化功能。《毛诗》自有一套教化体系,即以《诗大序》为理论核心,《诗三百》为具体的阐述基础,将《诗》看成是“夫妻之道、生民之本、王道之端”的教化之源。
第一,《毛诗》从男女感情,夫妇相处之道的角度出发进行教化。在《诗大序》中,《毛诗》将“经夫妇”放在教化问题的首位,这明显是对《诗经》中夫妻感情主题的一种继承。《诗大序》将《关雎》的内容解释为说明后妃之德,认为“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就是在强调夫妇相处之道是人伦教化的根基。
第二,《毛诗》将民间的风俗审美与儒家礼乐文化以及政治教化相结合,以达到观察民情的目的。毛宣国认为汉代以诗观察风俗民情也是学习于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更是明确了诗歌在观察、教化民间风俗上的作用。但是真正以诗教化风俗的还是汉代。汉代重视风俗美善,希望风俗能够符合儒家礼乐文化的要求,所以《毛诗》就利用《诗三百》的内容,以《序》约束与统治者兴趣爱好有关的风俗引导。不过,《毛诗》将民间风俗的善恶与统治阶级的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目的并不是将风俗捆绑于政治,而是希望形成一个统治阶级可以由上而下地移风易俗,同时民间情况可以及时反映给统治阶级的双向沟通。
第三,《毛詩》表现出强烈的民本精神,统治者也在教化范围之内。上文有所提及,既然《毛诗》是想创造一个双向的沟通环境,向下影响了普通民众,那么必然也会向上影响到统治阶级。虽然当时的教化主要是指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的单向影响,但是《毛诗》提出的“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就明确表达了古文经学的态度,被统治者也可以以自身思想行为来影响感化统治者,一些咏叹自己内心痛苦,怀念昔日快乐生活的诗歌,就是对统治者的教化。
今文经学在道德教化上的表现虽不如古文经学系统规整,但是也有所体现,特别是在今文经学的鼎盛时期——西汉影响广泛。今文经学观点是在先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的,由董仲舒塑造出汉代特性,将阴阳五行、经学研究等都纳入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观,并把这种哲学观实际运用到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之中,使汉代高度重视《诗经》的人伦教化功能。今文经学认为天人相通,人的性情道德是极为重要的,可以影响到自然灾害和国家政治,这与西汉的主流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备受推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齐诗》。
今文经学以性情说《诗》,认为《诗》表现了人的思想感情,那么人的性情需要受到礼教道德的规范,所以在解《诗》时强调了性情受礼教约束的必要性。
三、汉代《诗经》的文学价值
“诗”应当具有志、情、言三大基本要素,学界普遍认为汉代《诗经》研究功利性太强,将情强行加入儒家色彩,失去了本质,不具有文学价值,其实不然。汉代诗经学是以《诗》为基础建立的,无论其外在如何发展附加概念,核心部分《诗》本身具有极强的文学特性,这是无法被磨灭的,所以汉代诗学虽然政治色彩浓厚,但是在发展中也给文学留有余地,保有一定的文学特性。
首先,《诗经》的“赋比兴”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赋比兴”源于《周礼》,《毛诗》将其发展为“六义”,是写诗方法,“赋”是铺陈直序,“比”是比喻,“兴”是联想与象征的合体,“比兴”用具体事物类比政治道德伦理,相对委婉,符合汉代政治环境下“美刺”的要求,所以更为儒生推崇。汉代儒生对“比兴”的研究更是在客观上保存了《诗》的文学性。儒生以比兴为手段,将《诗》中的各种形象用联想和感悟解读,以其委婉特质来进行“美刺讽喻”。虽然政治色彩浓厚,但是客观上刺激了儒生群体对诗歌的重点关注,对“比兴”的深入研究,催生了后来人们对情景交融、神韵滋味的美学探究。
其次,“ 《诗》无达诂”,即重视文学和诗的主题接受,重视文本意义阐释的不确定性和读者阐释态度的多元化,这是汉代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也是一个文学命题。这个概念在汉代极为流行,也是古今文经学多样化发展的原因之一。虽然汉代儒生后来为了迎合政治诉求将道路越走越僵化,解《诗》时过于主观化,但是在发展初期还是呈现出了《诗经》研究的蓬勃生机和各种可能。比如,汉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其评价标准就是《诗经》,司马迁写《史记》,引用《诗》、分析《诗》的素材很多。
另外,汉代诗学在研究《诗》时还是保有对内含情感的体悟,这并没有被儒生忽视。汉代诗学对《诗》的历史化解读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功能不仅有抒情,还有记事,比如《卫风·氓》就是一首弃妇自述悲惨婚姻的诗歌,诗歌中仔细回忆恋爱甜蜜和婚后痛苦生活的部分,就是记事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毛宣国.《毛诗》“教化”理论及其对后世诗学的影响[J].中国文学研究,2011,(01):19-24.
[2]毛宣国.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路与方法[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2(02):236-245.
[3]杨子怡.汉代经学挤压下的诗性失语与存活[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02):86-90.
[4]赵长征.《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8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