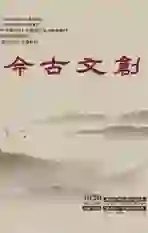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黄河上的月亮》中的创伤弥合与身份重建
2020-09-10张倩兰
【摘要】本文通过创伤理论的角度解读爱尔兰剧作家丹尼斯·詹斯顿(Denis Johnston)1931年在阿贝剧院上演的剧本《黄河上的月亮》(The Moon In the Yellow River),探讨此剧中的饱经沧桑的铁路工程师多贝尔在爱尔兰当时的历史语境和个人悲剧下造成的心理创伤、多贝尔的创伤弥合与布兰黛的身份重建与其对爱尔兰集体记忆和民族创伤的重构和影响。本文的研究意义是通过探讨《黄河上的月亮》对爱尔兰集体记忆和民族创伤的重构和影响,探究文本对爱尔兰历史创伤的弥合隐喻与对爱尔兰身份重建的深刻作用,以及阐发《黄河上的月亮》中爱尔兰历史创伤的弥合对爱尔兰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黄河上的月亮》;丹尼斯·詹斯顿;创伤弥合;身份重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3-0026-03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尔兰历史语境下的人们——多贝尔的精神“瘫痪”
就叙事而言, “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是“叙事语境”, 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 (申丹,2005:308)可以说,探寻爱尔兰集体记忆的文化意象, 必须追寻爱尔兰的社会历史语境。
这一时期的爱尔兰饱受动荡、战乱,几乎总是处在内忧外患中。此时全国一片混乱,小范围的战争处处可见,城市遭到轰炸。1922年内战结束,但六个郡的问题悬而未决,双方仍然有小规模摩擦。新成立的愛尔兰共和国在德·瓦莱拉(de Valera)领导的共和党执政下,渐趋保守,弘扬原始的农村田园生活,限制技术和工业发展。詹斯顿从工业技术进展与传统文化桎梏之间的深刻时代矛盾入手,塑造了多贝尔这样一个无处施展抱负,妻子难产死亡,深陷爱尔兰滞后的工业背景和动荡的历史大环境之下,沉浸在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带来的创伤中专注在家修建无现实意义的“玩具火车”的前爱尔兰杰出工程师形象。
他整日浑浑噩噩,对女儿布兰黛的存在熟视无睹,实现了踌躇满志到“精神瘫痪”的心理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原因不仅是个人心理创伤造成的,也集中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爱尔兰争端不断之下、文明进步与传统桎梏的冲突造成的集体创伤。
弗洛伊德思想是创伤理论的原创点和源头活水。从1915年到1939年去世,弗洛伊德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残酷,在《悲悼与抑郁症》(1917)中,弗洛伊德分别探讨了两种心理创伤——悲悼与抑郁症。受创的悲悼主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将爱从失去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顺利实现移情。受创的抑郁主体却拒绝承认爱的客体之丧失,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长时间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排除甚至拒绝心理移情。因此在抑郁主体分裂的心理空间中,自我之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不断进行道德审判和惩罚,将对外在爱的客体的憎恨和惩罚以逆转的方式发泄到自我心理空间中被对象化的自我上。内在自我心理空间之分裂、对自我持续的心理惩罚,还有从爱畸变成的憎恨,都是抑郁创伤的典型特征。(陶家俊,2006:67)多贝尔始终没有完成对妻子的哀悼,因为他始终无法原谅布兰黛,在陶希与长期陷于沉默的创伤中的多贝尔之间的对话就表露了多贝尔对他的排斥,这实际上是他对自身曾经身份排斥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甚至想用鬼怪的传说吓走陶希并轻蔑地嘲讽与打击他不切实际地想要带领爱尔兰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单纯愿景。
这其实是一种将憎恨和惩罚以逆转的方式发泄到自我心理空间中被对象化的自我——不速之客兼“外来者”的陶希的身上。但是他对他受到的具体地创伤经历始终闭口不言。卡鲁思1996年的《不被宣称的经历》 (Unclaimed Experience) 一书中也做出了解释:“创伤无法定位于某人过去发生的某个单纯暴力的或最初的事件, 而是定位于它的那种独特的本质——它的那种在最初无法被确切感知——过后返回来缠绕幸存者的方式。” (Caruth,1996:4) 指明了创伤的不可言说性。
但陶希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帮助多贝尔反复讲述与重现创伤场景:哥伦巴的出走,布莱克的死亡。从而起到了打破多贝尔的现实与幻想、生命与死亡、记忆与遗忘、过去与现在的界限的作用(陶家俊,2006:73)
在爱尔兰这个遭遇了战火、饥荒、内战、死亡等创伤事件的地域上, 创伤不可避免地和集体叙事相联系, 个人创伤经历往往喻指着集体经历的历史性事件。创伤主角担任一个重要的作用, 在他或她所展示的创伤经历背后, 往往隐藏着更多人的集体记忆, 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创伤人物的塑造是创伤叙事的要素之一。
二、超现实的历史图景——香农电力公司的“爆炸”意图与其对爱尔兰历史创伤的影响
《文明及其不满》见证了弗洛伊德创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心理创伤转向文化创伤。他提出的核心论点是:“现代文明进程中充满了爱欲与死亡的对立冲突。现代人自诩有能力驾驭自然,也掌握了毁灭部分乃至整个人类的技术,这恰恰是我们倍感焦虑、不快乐的根源,也充分证明了文明固有的死亡本能和深度创伤……进攻倾向是人与生俱来、滋长泛滥的本能脾性……它对文明构成最大的障碍。”(Freud,1961:69)
纵观爱尔兰历史,不难理解对“香农电力公司”爆炸的焦虑在詹斯顿的《黄河上的月亮》中的集中体现,罗伯特·基(Robert Kee)在《爱尔兰史》中写道:“有些人认为过于细致的考察爱尔兰历史是一件危险的事,其原因不言自明……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军一直指望能通过暴力改变英国政府政策。”(罗伯特·基,2010:8),可以说,针对暴力对文明产生不可磨灭影响的恐惧与焦虑是自始至终深埋在爱尔兰与英国民族基因里的,其文化创伤的不可言说性造成的讳莫如深与爱尔兰民族的真实感情在历史中被英国不断他者化,被迫固定于野蛮与暴力的刻板印象中,这使丹尼斯·詹斯顿的重述成为必要。而在他充满现代性的重述中,身份处于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符号永远不能指任何稳定的意义。
卡鲁斯(Cathy Caruth)说过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他者借助声音打破沉默,从事件当中述说,提供另类的历史,这与詹斯顿的拥有超现实色彩的历史描写似乎不谋而合,通过撰写香农电力公司并未发生过的“爆炸”,詹斯顿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一个有着超现实色彩的扭曲的记忆,是建立在合理基础上的创伤受害者的重新构成与重新编辑。
詹斯顿从另类的角度的“再记忆”展现了历史的颠覆性,在历史真实和叙述需要中选择了后者忠实和背叛在史学真实和故事虚构的层面上交合混杂,也折射了作者通过共和军的虚妄梦想的破灭弥合多贝尔的个人记忆的心理创伤与深埋在爱尔兰基因中历史创伤的意图。使多贝尔和沉浸在“拥抱黄河上的月亮”的虚妄梦想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正视现实,却也加强了共享这段历史爱尔兰人民的相互联系。詹斯顿通过重新想象历史,叙述历史,创造历史,意在构建新的历史记忆。正如詹斯顿所说:“这部剧不是关于电力公司的,而是关于人的。”(Johnston,1983:95)
此外,为了再现创伤记忆碎片化、断裂性、无逻辑性的特点,《黄河上的月亮》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第二幕与第三幕时间上的重叠与重复颠覆了传统的按时间顺序展开的三幕剧,全文也有多处体现其超现实性与现代性的地方,如对《夜莺颂》和《胡丽痕的凯瑟琳》等经典剧目和诗歌的杂糅使用,德语和英语的交替运用与布莱克殒命时对暴君尼禄的戏仿,戏谑的军事法庭的裁决与对庞德所翻译的李白的《黄河上的月亮》的应用,原本的叙事框架被表现主义的手法解构得支离破碎。而同一类型的叙述内部的时序也时常是杂乱无章的。文本像是一幅巨大拼图的零散碎片:杂乱、无序且琐碎。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拓宽了其艺术空间,有一定的非理性和神秘的元素,展现了一幅超现实的历史图景。
三、被重新接纳的布兰黛——爱尔兰的身份重建
创伤记忆并不局限于直接遭受创伤性事件打击的个体和一代人,它还会悄然传递给没有亲身经历过该事件的下一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位匈牙利心理学家亚伯拉罕(Nicolás Abraham)和托洛克(María Torok)提出了“代际幽灵”的理论,用一个比喻形象地阐释了创伤的代际传递过程:创伤性经历在第一代受害者的内心形成了一个“墓穴”,受害者将之埋藏于内心最深处;当孩子与怀揣着内心“墓穴”的父母互动之后,创伤记忆像幽灵一样,作为未被意识充分理解的记忆从父母的潜意识悄无声息地传递到了子女的潜意识中。这正如布兰黛与多贝尔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之间从未有过正式的交流,但是多贝尔的缄默不语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布兰黛对自己身份的危机感。
事实上,剧中的角色列表中提到的是“哥伦巴姑姑”(Antie Columba)而不是“哥伦巴”(Columba),这表明这个故事展开的顺序可以从小女孩的角度来观察。她的个人探索贯穿于各种思想斗争之中。当她在剧本的开始遇见陶希时,她不明白他为什么叫她“淑女”:“哦,我不是淑女……但这是我父亲的错。他叫我小荡妇,但我认为别人叫你什么,你就会是什么人。”(Johnston,1983:104)。
布兰黛认为人们在话语的传播中创造了现实,这样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吟游诗人的诗歌和早期的传统爱尔兰国家剧院的愿望:在舞台上塑造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尽管女孩似乎相信父亲的话,但她质疑自己与父亲的关系的可靠性,以及他的权威:“我没有父母。除非你把父亲也算在内。可我们相处得不太好。我不记得我的母亲了。”(Johnston,1983:105)詹斯顿创造性的在主線中穿插了布兰黛对自己身份的寻找与探索,用布兰黛的视角进行叙事,有着“后记忆”式因两代人亲情的断裂而造成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诘问与质疑,布兰黛甚至觉得自己不过是父亲养的一只“鹅”。她梦想得到从未得到的“正规”的教育。(Johnston,1983:142)
凯鲁斯认为,创伤一旦发生就永远无无法完全从记忆中抹去,但我们总会竭尽全力修复创伤经历在心灵中留下的裂隙,只有这样才能重建患者与外界的联系,重塑患者积极的自我。从社会和集体的角度来看,集体创伤的修复更是重建集体归属感的关键,也是反思历史、防止悲剧重演的必要步骤。
在电厂在一声巨响中轰然倒塌之后,詹斯顿通过玛丽的幻影重新联系起了父女间破碎的亲情。在布兰黛经历了“荡妇”“鹅”“淑女”的身份探寻之后,“玛丽”的称呼重建了多贝尔难以言说的创伤经历,布兰黛叫他“父亲”并再次信任他,并在他的膝盖上进入梦乡,新的一天的黎明取代了背景中的爆炸的光芒。象征着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爱尔兰。
正如在赫曼的《从创伤到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创伤复原的第三个阶段提到的那样:第三个阶段患者逐渐准备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现实世界,有勇气面对恐惧,与自我讲和,并建立起新的自我以及对他人的信任。(Herman,2015:155)。多贝尔在他的心理发展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扮演了一个饱经沧桑、精神麻木的退休工程师后,他又开始重新思索,这一事实表明他找到了一条出路,开始弥合自身心理悲剧以及1927年后爱尔兰历史语境下造成的创伤,摆脱了精神“瘫痪”的浑浑噩噩以及悲伤丧气的恶性循环。通过重建亲子关系,多贝尔在黎明的曙光中重新赋予了爱尔兰民族——布兰黛崭新的身份。正如后来更多剧作家所阐明的那样,《黄河上的月亮》试图阐明的是:历史创伤的避而不谈只会对加重创伤的溃烂,和解和跨越,把眼光从过去的伤痛跨越到未来的眺望才是走出伤痛,弥合创伤的有效途径。
四、结语
詹斯顿创作的剧本《黄河上的月亮》用超现实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框架,运用创伤人物多贝尔的塑造,表现主义式的历史图景的结合,引入象征着爱尔兰的冉冉“升起”的父女裂痕的弥合,重新架构了爱尔兰历史与创伤的联系,利用个人创伤经历喻指着集体经历的历史性事件。本文通过创伤理论,希望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解读《黄河上的月亮》,以期当代爱尔兰走出与英国二元对立的迷雾,消解至今仍然存在的深埋在英国与爱尔兰民族基因中的对于暴力的焦虑以及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而引起的普遍存在对爱尔兰身份的不确定所引起的后现代焦虑。
参考文献:
[1]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16.
[2]Johnston, Denis. The Moon in the Yellow River (MYR)[M].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3
[3]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4]罗伯特·基.爱尔兰史[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2010.
[5]李元.20世纪爱尔兰戏剧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6]陶家俊.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7]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151-156.
作者简介:
张倩兰,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爱尔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