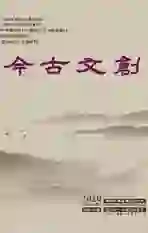《鼠疫》
2020-09-10薛翌阳
薛翌阳
【摘要】 《鼠疫》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代表作,正如西西弗斯推着石头上山一样,每当石头推上山顶石头便会滚到山底,而西西弗斯只有重复这日复一日的灾难,人们面对鼠疫也同样如此。主人公里厄大夫认为其他都没有意义,只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最根本的意义。而小说中还有两种代表:一是试图掩盖事实,二是选择自我麻痹。小说赞扬了里厄大夫这类人的做法,并对英雄主义进行了定义。
【关键词】 《鼠疫》;荒诞;英雄主义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6-0007-02
荒诞“虚伪而不可信的”,是一种致命而不可摆脱的特点,关于荒诞的来源,加缪用“一个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对这个世界的错误认识”来加以概括,荒诞一词来源于人,用以形容于人。也就是说在人类的世界里,荒诞是无法消除的,那么如何对待荒诞,将成为自古以来哲学家们探索的重点。
《鼠疫》正是这样一部荒诞之作,它讲述了平静的城市奥兰经历了一场瘟疫,在這场瘟疫中以里厄和塔鲁等为首的人员组建成医疗小队与鼠疫抗争的过程。以鼠疫发展的时间顺序为线索,着重描写了重大灾害面前人性的真实性。作者加缪企图用鼠疫来表示一种人类所经历的灾难,并且这灾难永不消逝,时刻潜伏在他们的浴室、地下室、行李箱和旧纸张里数十年,等候着冥冥之中的指令或人类的不幸,到那时鼠疫将再次催醒它的鼠群,送他们去某座幸福的城市,由此可见,作者对这种灾难持久性的肯定。那么对于某种持久性的无法摆脱的灾难,会自然地想到这灾难的发源地——奥兰小城,作者用一种自以为是的平静气氛来形容它,避开常人喜欢的季节,说它冬季有着宜人的天气,这不仅让人感觉荒诞,作者描写的小城透露出一种平静中掩盖着冷漠和死亡,无人在意与自己无关的事和人,是没有温度的城市,是自以为是的城市,是掩盖着的城市,它就是一个荒诞的缩影,而鼠疫的到来似乎是对这座被掩盖着的城市来了一次放大,在鼠疫面前人是无力的,它对于任何年龄,任何性别的人都痛下杀手,毫不留情。面对被流放的人们,他一律平等,使他们进退不能,面对束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他折磨其身,使其挣扎而死,他折磨无数个与之斗争或放弃斗争的人,把他们一个个拉下坟墓。人们在荒诞的处境,迷茫不知,一视同仁。由此,可以做出一种推断,鼠疫也可以是一种抽象化的人类灾难——荒诞。
作者加缪用鼠疫来表达了一种人类所经历的灾难,企图表达的并不仅仅侧重于当时所经历的二战,而是一种宏观的灾难,而这种“荒诞”正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在文本中作者描述的“鼠疫”,造成了奥兰城中,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的局面,身不由己,犹如被流放般的痛苦和绝望。与荒诞相同的是,这二者都是无法消除,无法避免的,并且摧残着人们的心灵。
那么在这种痛苦中,人们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对待方式。第一种人试图逃避,这类人以当局含糊其词的态度为代表,凭借着众人均认为不明智的固执,当里厄说服了省里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时,大部分人所表达的意愿,不是寻求如何应对这种疑似症状,也不是通知群众做好预防准备,而是一边持观望的态度,又一边自作乐观的否定行为。这种全然不作为的行为,集中表现为逃避、害怕现实发生,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这种可能,实在荒诞愚昧至极,值得作为深刻教训。他们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活在自己主观臆断的态度中,也就是表面的不作为,坐以待毙,去欺骗自己或向他人散播一种虚假事实,来获取一种心理安慰,让所谓的荒诞,落入其骨深深将其与自己融合,不做任何抵抗,是荒诞的宿主。
第二种人选择自我麻痹,这类人相对于上者,略有改观,最起码他们面对了现实,并且采取了必要的挣扎,而挣扎是否有效,暂且不提,“今宵有酒今宵醉”是一种值得赞赏而潇洒的人生态度,若“宵宵有酒宵宵醉”的持续下去,则会造成精神萎靡,并不能改变事实,那么久而久之,就与那些直接逃避的人没有了区别,但这或许也是那些无能为力的大多数人的选择,被“荒诞”所俘虏,认为自己无法改变,而选择沉默,实则丝毫不能使自己处在清醒的境地,反而被吞噬落入更加混沌的形势。
第三种人与其斗争,《鼠疫》中着重强调了“斗争”,在鼠疫局面下,里厄、塔鲁等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首先鼠疫的故事叙述者医生里厄是一个读者眼中不折不扣的斗士形象,他却在书中数次强调,不要将此书当成所谓的英雄传记,他时刻希望世人了解到的是“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身份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做一个凡人”,诚然他也确实做到了如何作为一个凡人的关键部分——正视现实。在鼠疫当前,收起自己的感性情感,面对感染病人,他隐藏住柔软,不顾被病人家属泪水所淹没,表现得近乎决绝地拉走即将生死离别的一家人,那么能说他无情吗?不,不能。如果没有他的决绝,会是更多人的生离死别。那么该说他冷漠吗?也不能够如此形容他,如果他冷漠就不会参与整场鼠疫的抗争,他只是在尽他的责任,没有被一切现实的荒诞所蒙蔽双眼,而是擦亮它们,直视这种荒诞,正如加缪所发出的“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 ”①字字掷地有声,同时里厄身上也无不烙印着类似如此的“反抗”“自由”与“激情”。为受害者斗争,为解除荒诞枷锁斗争,为心中的执念而斗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这样形容,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②,加缪给予了里厄一个斗士的形象,让他凌驾在荒诞之上,无数次地推动阻碍人类生命的荒诞存在——鼠疫,此种存在,即反抗的观念,实在不能不说是“存在主义”大师加缪思想的负责者。哪怕知道可能会是一场空的结果,哪怕付出了生命,也去为他们心中的执念和理想奋斗,这种“存在即反抗”的态度,如同西西弗的诅咒,循环往复,非常辛苦,但斗士们却将这种“荒诞”变成了“荒诞”的天堂,在此天堂行走,不为别人,只为完善自己的生命。让与荒诞抵抗的血性烙印在自己的生命中,通过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平凡的人来抵抗“荒诞”,做自己的主人,试图改变这种荒诞的状况。
倘若里厄是为人类而战的斗士,那么塔鲁同其一致,他也是一个为人类的生命和自由斗争的斗士,与里厄相反的是,他所感兴趣的并非是平凡的人,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圣人,这就使他与现实生活中略有出入,过分的人道主义,可能会导致新的错误,如果让一个有着特立思想抱负的人,学会接受思想的错误,他们一定会迷茫,但也绝对会反思,塔鲁所追求的人类社会是无“谋杀”的世界,人人无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诸代价,他所构想的完全无杀戮,无规则世界,宛如希腊学者所提出的,“以人为尺度”般,以飞快的速度引人耳目,又飞速的陨落。
他的反抗与斗争,实质上与这种过度的“人道主义”背道而驰,一切政權的建立都必定出现反对者,而如果企图建立理想中的政权,势必要做出一番斗争,于是塔鲁在这样的道路上矛盾丛生,反而充当了“谋杀者”的身份,直至最终他不得不发出人类的全部不幸都来自没有用明确的条款,来规定事物的感慨。诚然,世事若都从利益考虑,本无对错之分,企图破坏或重建,终摆脱不了杀戮,人们应该放弃斗争吗?塔鲁令人敬佩之处在于,它没有因为认识的错误而放弃心中所坚信的执念,而是迅速地投身于另一场战斗,即与里厄组建医疗小队来救助病人。并且为之倾注自己的生命,值得一提的是,在无数的斗争中,作者唯一给予死亡结局的只有塔鲁一个,而不是书中同样身患鼠疫的格朗,相反,作者将这个全书唯一重点强调的“英雄”格朗,戏剧化地安排了一个死里逃生的戏码,却将沉重的死亡深刻地砸向塔鲁,这就要从人物的本源说起,作者笔下的格朗或许在读者眼里是荒诞可笑且懦弱的,但作者十分欣赏他,因为他是一个里厄式的人物,即用行动做反抗的人物,他很平凡也不完美,但加缪就是要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物来更有说服力地说明英雄的定义:平凡的人就是英雄。不得不说,格朗在鼠疫中,其实就是加缪给予英雄的正确形象,英雄并非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也并非就一定要义愤填膺,无所顾忌地献身于事业,当人在某件事物上奋斗过、行动过或反抗的过失,他就是英雄,所以加缪将这种情感寄托在格朗身上,他就是一个喜剧式的人物,是作者的意志所加,不能把他写上死亡的句号,相反塔鲁的一生为反抗事业做斗争,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会比格朗深邃而富有壮丽之感,正如加缪与西西弗的神话中写道:“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 ③可见塔鲁同里厄一样,也是西西弗式的人物,但由于他的特例,他是极端的西西弗,他付出的代价也必定更为沉重,以至于用毕生的生命投向斗争。
现实有多荒诞,反抗就有多必然。那么加缪所表达得极为反抗事业中的牺牲精神,塔鲁就是他给定义的吃螃蟹的人,盲人从一开始就深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源于人道主义,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人们所追求的人道主义犹如一场鼠疫中的光明,逃不出荒诞的溯源,只不过反抗与否是鉴别英雄的标准罢了。
注释:
①加缪:《西西弗神话》,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②罗曼·罗兰:《名人传》,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③加缪:《西西弗神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