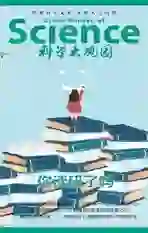制度化建设
2020-09-02王之康
王之康

要想真正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需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推进高校的现代治理,要把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这类教育事务全部交给教授委员会管理、决策,对每个教师的教学、学术评价实行同行评价而不是行政主导的评价。
1977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得以恢复。
可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有两大分水岭,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另一个则是1977年恢复研究生教育。
40多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看来,这些成就首先就表现在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上。
据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这17年间,我国一共招收的研究生人数不到2.4万,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时,招生人数也仅为1.07万,而在2011年,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56.02万,是这17年招生总数的23.3倍。
不难想象,在这些事实的背后,不仅是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幅提升,也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而上世纪80年代初学位制度的建立,也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可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至今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
在学位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和学位授权体系基本形成,建立了学科门类齐全、结构布局相对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拥有了硕士授予单位;学位授予类型既有学术学位也有专业学位,学位获取既可以通过考试(推荐)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也可以通过自学或其他学习方式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形成了职能和权限分明的中央、地方政府和培养单位三级管理体制。其中,中央研究生管理部门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在本地区研究生教育的统筹、学科建设、学位授予、质量监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培养单位则在有关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拥有相当的自主权。
此外,我国研究生法规体系也逐渐完备,一系列与研究生教育相关的组织机构相继建立,如1994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1999年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成立,2003年成立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等。
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要得益于我国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些有益探索。而在这些探索中,沈文钦认为,首先就表现在国家“重视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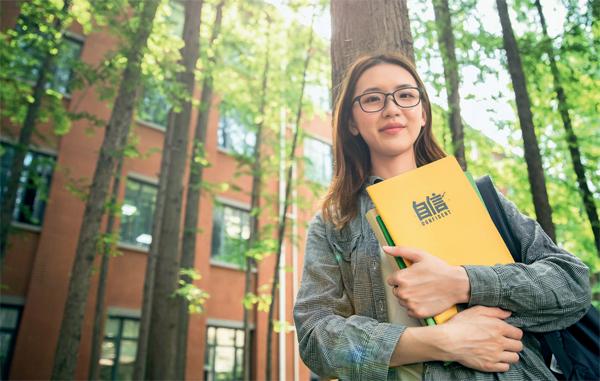
其实早在1979年,教育部就提出了在研究生招生中要坚持“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为此,国家在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建设、科研条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对研究生导师资格设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同时还采用了多种质量评估方式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同时,“985工程”“211工程”和其他一些重大计划的实施,也使得一批重点高校、重点学科与博士点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有力地保证了博士培养质量的整体水平。
“随着我国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加大,更多的博士生获得了参与课题研究的机会。”沈文钦告诉记者,他曾参与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的博士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导师的课题中,“而随着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博士生的资助水平也大幅提高,使他们能够依靠资助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以2015年为例,国家奖学金共奖励硕士研究生3.5万人、资助金额7亿元,奖励博士研究生1万人、资助金额3亿元;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共奖励研究生100.31万人、资助金额70.41亿元;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314.23万人、资助金额106.11亿元;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资助137.43万人、资助金额36.33亿元。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三助”比上一年度分别增加50.43亿元、31.36亿元、7.49亿元。
“此外,我国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与探索,并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稳妥做法,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沈文钦说,例如博士生导师的审批权最早归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后来下放给各个高校;一开始只有教授才有资格指导博士生,后来清华大学等研究型大学改革了博士生导师制度,允许助理教授指导博士生;在招生制度方面,近些年很多高校也開始尝试探索申请审核制等。
那么接下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又该如何更好地发展,以推动质量再提升呢?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认为,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教育因社会的存在而存在,不可能脱离社会、远离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我国“教育学泰斗”、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曾提出高等教育的“两个规律”,即“大学应主动适应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才有生存权和生命力”的外部规律,以及“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应按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办学,而不能按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办学”的内部规律。在杨德广看来,作为大学教育一部分的研究生教育,也应该符合这“两个规律”。
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表示,我国要想真正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需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推进高校的现代治理,要把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这类教育事务全部交给教授委员会管理、决策,对每个教师的教学、学术评价实行同行评价而不是行政主导的评价。
“这样才能让课程和学术研究都注重品质,并结合不同的培养定位,对学生提出不同的培养要求。”熊丙奇说,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在课程之外提供更多科研机会,让学生在科研中提升学术能力;对于专业型研究生,在完成所有高质量的课程学习后,不必参与科研项目,撰写好论文即可毕业。
“只有实行学术自治,高校才能切实建立起导师制。”在熊丙奇看来,我国现在虽有导师制,但导师一方面在行政评审和考核中已经失去对教育和学术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用自己的声誉对学生质量负责的意识——在研究生招生、培养、毕业中,导师并无多大话语权。“这是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切实解决的问题。”
◎ 来源| 中国科学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