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笔下的“小人物”与“大时代”
2020-08-28高华
高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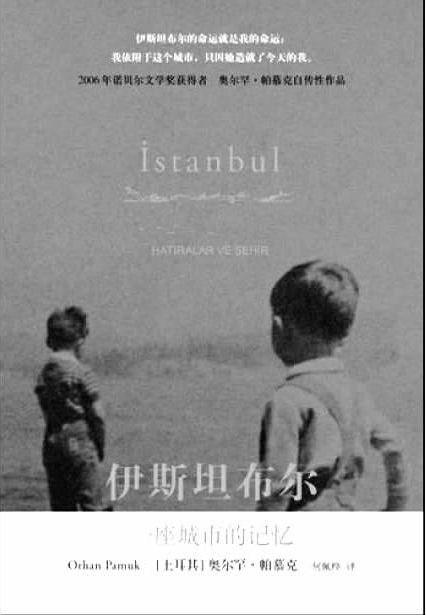


帕慕克曾经说过:“我必须这么回答:‘我只为土耳其人写作。”读过帕慕克作品的人都知道,帕慕克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土耳其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而展开,帕慕克笔下的人物关系,包括父母亲情、“兄弟之争”“杀父”与“弑子”,以及他所有“脑袋里的怪东西”,都在变相地诉说着土耳其的当代故事和“小人物”处于“大时代”洪流中的命运纠葛。帕慕克出生和生活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瓦、大街上行走的每一个生命都可能出现在帕慕克的创作中,对他们的感情也会流淌在帕慕克的血液里,“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帕慕克把自己的命运和伊斯坦布尔的命运相连,他用文字记录土耳其的历史,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中,他用记录“小人物”命运的方式来反映“大时代”的历史进程。
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和《红发女人》分别完成于2003年、2014年和2016年,其成书阶段分别可对应“前埃尔多安时代”、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模式”阶段和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时代”。在这三部作品中,帕慕克分别把作为个体或小人物的“我”置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用“小人物”的命运串起对“大时代”土耳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城市化进程等的思考,“小人物”是“大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小人物”的命运又在“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被裹挟、被主宰。时代总是在轰轰烈烈地变迁,它以国家的宏大叙事不断向人们展示历史的乌托邦景象,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到来看上去好像带来新的期望,但给“小人物”带来的却往往是新的损害:《伊斯坦布尔》中帕慕克家族的衰败源于社会的动荡;《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城市化进程在带来改革红利的同时,也在损害着大多数像麦夫鲁特一样“小人物”的生计;《红发女人》中诉说的是现代化进程中象征各组政治力量的人物关系的裂变:身不由己、父子相残。通过这三部作品,帕慕克让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在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小人物”命运和“大历史”进程互相纠缠的痛苦和迷茫,同时这三部作品也是帕慕克在几十年的人生时光里思想和文化心理变迁的表征。
一、家族的衰落和帝国的忧伤
2002年,帕慕克决定“写一本题材新颖的书,融合自己对故乡的情感和对自己22岁之前人生的思考。”一年之后,《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以下简称《伊》)出版。这本书的出版一度让他的家族成员倍感尴尬,她的母亲谢库瑞非常伤心,他的哥哥怒不可遏,并因此和他断绝了往来。在《伊》这部近乎纪录片式的作品中,帕慕克除了描述了各种纠缠不清的家庭恩怨,更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成长记忆以及家族的发展秘史融合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忧思中,同时古老的伊斯坦布尔的废墟苍凉、城市居民的贫困和街道的肮脏又穿插在福楼拜、戈蒂耶、纪德以及19世纪伊斯坦布尔本土作家——雅哈亚、坦皮纳、希萨尔的描绘中,通过东西方作家共同的目光见证着这座伟大城市的衰败,从而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土耳其式的“呼愁”情绪。
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的沉沦与衰落,是伴随着作为城市上流阶层的帕慕克家族的衰败渲染和由此产生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情而展开的,在《伊》中这两者之间必然的联系首先通过这个大家族的家庭关系体现出来:“这些在节庆欢宴上有说有笑的亲戚们,在对金钱和财产问题起争执的时候同样冷酷无情。在公寓里没有旁人的情况下,母亲老爱跟我和哥哥诉苦,埋怨‘你们的伯母‘你们的伯伯‘你们的祖母苛刻狠毒。一旦在所有权、制绳索工厂的股份或公寓哪一层楼给谁住等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唯一能肯定的是,永远得不到任何解决。这些裂痕或因合家欢宴而消除,但从小我就知道,欢乐背后是堆积如山的旧账和波涛汹涌的责难。”帕慕克家族曾经在土耳其共和国时代显赫一时。帕慕克祖母的家族在19世纪俄土战争期间移居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都有田产;帕慕克的祖父在1930年因为投资铁路建设工程而发了大财,后来又开办了制造麻线、绳子、干烟草等产品的工厂,直到1934年他过世之前,他留下的大笔财产“让父亲和伯父怎么用也用不完,尽管他们有一长串失败的商业冒险经验。”他然而随着帕慕克父亲和他的伯父投资的一次次失败,他们硕大的家业也日渐凋零,家庭矛盾陡起,“为钱的争执越来越厉害”,帕慕克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失落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我们的家。”在此,帕慕克将自己的家族命运同奥斯曼帝国的兴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曾经盛极一时,其疆域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疆土面积超过550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包括现在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高加索人等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帝国。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民族政策也开明包容,各族人民可以徜徉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说着各自的民族语言和平共处。但随着西方世界新航路的开辟,原来奥斯曼帝国靠截断陆路交通来垄断亚洲贸易和财富的局面被打破,西欧各国绕道海路直通亚洲,同时欧亚大陆大量白银涌入土耳其也使其国内货币急剧贬值,这直接加深了土耳其国内各个阶层之问的矛盾。而且,帝国的不断对外扩张,以及同沙俄在地中海地区无休止的争霸战争等都使土耳其内忧外患。真正让奥斯曼帝国走向末路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同盟国而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其势力范围很快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1924年随着哈里发制度被废除,奥斯曼皇族成员也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被驱逐出境,奥斯曼帝国彻底灭亡。帕慕克在《伊》中不断哀叹的帝国忧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2000年的历史中從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伊》这部书就像是一曲挽歌,它哀悼着帕慕克失落的孩童纯真与快乐,哀悼着一个盛极一时家族的衰败,哀悼着一座城市曾经的辉煌和落寞。唯有凝视这座城市的断垣残壁,阅读关于她辉煌历史的记载,观看书中古老的版画和照片,才能感受到她往昔的荣耀。
帕慕克把这种“忧伤”用“呼愁”一词来概括。帕慕克在《伊》中认为“呼愁”一词来自《古兰经》的“huzn”或“hazen”,“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哈蒂洁和伯父塔里涌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tilhtizn,即‘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不仅仅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不再,更在于帝国解体之后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对奥斯曼文化传统的遗弃和对西化之路的尴尬追寻,“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土耳其人找不到自己的文化之根。1923年10月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同时也结束了政教合一的苏丹政权在土耳其长达数百年的封建统治,土耳其人在国父凯末尔的领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西化改革,资产阶级主权在民的思想开始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废除伊斯兰教的法律和教育体系、关闭大小宗教学校,建立议会制、大力宣扬西方的民主化制度等,凯末尔以后的土耳其领导人也基本延续了这样的西化政治风格。但是过激的世俗化改革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世俗化对服饰、圣徒、墓葬、朝圣、节庆等关系到民间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等因素的改革所导致的愤怒和抵抗运动,远比废除哈里发、长老院、宗教学校等正统的伊斯兰制度所激起的愤怒更甚。这一行为切断了世俗主义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连续。”同时,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借势抬头,国内其他的民族主义分裂势力也此起彼伏,最后演变为20世纪70年代的库尔德人和政府军的多次武力对抗,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内战,致使土耳其的政治、经济都受到重创,土耳其从凯末尔时代就跃跃欲试想成为欧洲强国的念想也因为连年的战乱而变得遥遥无期。而且为了进一步推进西化改革,土耳其在1946年从一党制转向了多党民主制,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因此被坚持下来,这就为日后伊斯兰主义的再次抬头埋下了隐忧;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迅速崛起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世俗化政权两相博弈,致使土耳其军队为维护西化成果分别于1960年5月、1971年的“3·12”、1980年的“9·12”和1997年共四次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连年的军事动荡严重打击了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民风凋敝,整个社会陷入了长久的哀伤与忧愁的氛围之中,帕慕克家族也再也没有回到当初的荣耀。“在过去150年间(1850—2000),我肯定‘呼愁不仅统治着伊斯坦布尔,而且已扩及周围地区。”这也正是帕慕克在《伊》中不断书写“呼愁”的原因。
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无法把控自己命运,只能在江山日下的帝国衰落中顾影自怜,帕慕克家族的衰落、父母的不和,作品中到处都弥漫着凋敝的气息,“对时局的恐惧和未来的难以把握是土耳其人共同的心里内景。”时逢乱世,人心思定,帕慕克也不例外,这个时候的土耳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整肃凌乱的人心和混乱的国情,帕慕克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帕慕克说:“读者若留意到我在描写自己的时候描写伊斯坦布尔,在描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描写我自己,也就已看出我……是为其他事做安排。”这样的“其他事”,正是帕慕克所期待的“大时代”的到来。历史在呼唤、帕慕克在等待,一个新的时代和政权——埃尔多安和他的正义与发展党是时候粉墨登场了。
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小人物命运与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
2002年11月3日,土耳其举行大选,伊斯坦布尔前市长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获得34.9%的选票,赢得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550个议席中的179个。帕慕克振奋不已,他马上发表演讲:“我希望埃尔多安当选总理,也希望军队不要干政。埃尔多安正在狭缝中开道前行,如果能顺利通过,那么土耳其必将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宽容的国度。”帕慕克对埃尔多安的上台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待,而埃尔多安执政时代推行的被称为“土耳其模式”的政策尝试也让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帕慕克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以下简称《怪东西》)里小说通过主人公麦夫鲁特一家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经历,串起了2012年以前土耳其房地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也记录了作为“小人物”的麦夫鲁特在飞速发展的大时代裹挟下的命运多舛。
“土耳其模式”是政治领域的一个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观点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土耳其模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产物,但阿拉伯世界却普遍认为,“土耳其模式”是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产物,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东方伊斯兰主义在一个世俗主义国家相结合的成功模式,这一模式缓和了宗教和政治的冲突,推动了经济的飞快发展,使土耳其在国际环境中越来越有发言权并很快成为地缘政治的领袖,具有很强的可模仿能力。尤其是2010年中东爆发大变局以后,这一概念再一次被热议和推崇。但还有观点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土耳其模式”看似光鲜,但极容易走向政治的独裁和统治者的威权,因此在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可复制性。帕慕克从2008年开始创作《怪东西》,用了6年时间,于2014年完成,正是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模式”呼声最高也争议最大的时代。帕慕克以小人物麦夫鲁特和他的父亲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经历,呼应了“土耳其模式”运行过程中的光芒与阴暗,也写出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潮流中不能主宰自我命运的迷茫与艰辛。
麦夫鲁特曾经是“土耳其模式”的受益者,第一件让麦夫鲁特受益的事情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高,作为西化改革很重要一部分内容的电力配送实现了私有化,电力公司承包了国家电力资源的销售和电费的收缴,并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对用户欠费行为实行高昂的罚款惩罚。麦夫鲁特因为接受了电力公司一个小老板、中学同学费尔哈特的邀请和帮助而成为一名光荣的电费收费员,并成为土耳其轰轰烈烈西化改革洪流中一分子。因为搭上了国家改革大潮的列车,麦夫鲁特“口袋里有了余钱”,他也能“赶在女儿们睡觉前回家,陪她们一起继续看电视”,得以享受天伦之乐。那些以前和他一样的“酸奶供应小贩,他们用大多数挣来的钱买了地皮,因此现在他们很有钱。”第二件让麦夫鲁特享受到“土耳其模式”红利的事情是:2009年因为旧城改造,麦夫鲁特和他父亲曾经住过的地方将被“乌拉尔建筑公司”建造成“一栋十二层的公寓楼”,麦夫鲁特欣喜地意识到以后“从自家院子往上爬六层楼,便可以远眺海峡”。2006年土耳其宣布伊斯坦布尔的诸多街区“被划人特别旧城改造区,鼓励建造高层公寓楼。消息一出,街区里的人们全都欣喜若狂。……这简直就像是在往大家的口袋里装钱。”这使得“正义与发展党本就居高的得票率……更是直线飙升。”“但让麦夫鲁特最为震撼的是,这些楼房的后面也是一片由快速躥高的摩天楼和塔楼组成的楼宇汪洋。它们中的一些遥不可及,麦夫鲁特分辨不清它们是在城市的亚洲部分,还是在这边的欧洲部分”,土耳其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前进。土耳其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盘活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持久活力也带动了土耳其的多元化外交,这为土耳其政府和正发党在土耳其领导地位的巩固获取了丰厚的政治利益和外交资本,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也变得异常顺畅:2004年在《土耳其进步状况报告》中,欧盟同意启动2005年的土耳其加人欧盟的谈判。
但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拖着沉重病躯负重前行的古老国度来说,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暴露出来的问题就会越多。这一点帕慕克在《怪东西》里也同样提到了。麦夫鲁特的父亲穆斯塔法是上一辈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务工者,他和自己的哥哥哈桑以及侄子最早来到伊斯坦布尔,和所有迁居而来的乡下人一样,因为要“早上比别人更早进城”以“找到工作和生活”,他们“都在距离道路最近的地方,也就是山脚下造房子”,被称为“一夜屋”。这里不通水电,冬天的晚上为了节省柴火一定要灭了炉火才能睡觉。在土耳其的房地产业刚刚起步阶段,土地管理混乱,进入城市的人想要拥有一问“一夜屋”,只要“去区长那里给点钱”(《怪东西》56)、获得区长手写的一纸“承诺书”就可以了,如果“再给他多塞一点钱”,区长“还会加上一些夸大地皮虚幻边界的词语,然后在纸的下角盖上他的图章。”在大量无业又无家的人“纷纷从安纳托利亚涌向城市的时期”,区长写的那些纸条“身价陡涨,越来越贵的地皮被快速分割后细分。伴随着移民潮,区长的政治势力也日益扩大。”在此,帕慕克用讽刺的手法描述了土耳其社会管理混乱、政府职能缺失、底层“小人物”生活艰难并备受盘剥的境况。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如果再缺乏完善的监督体制必将导致制度的腐败,如此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激化、生态环境恶劣,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就只有任人宰割的命运了。所以进入城市的麦夫鲁特在享受过短暂的改革红利的同时,遭遇更多的则是噩运连连:夜晚卖钵扎遇到野狗攻击、随即又被街头流氓抢劫、去“宾博快餐店”打工被其他员工排挤和陷害、与连襟费尔哈特合开钵扎店倒闭、做停车场管理员遭遇黑社会流氓团伙的暴力、妻子拉伊哈自行堕胎失败而大出血死去,等等。帕慕克通过麦夫鲁特的这些奇特经历历数的是土耳其治安的混乱、小生产经营者生存的艰难、妇女恋爱和生育权利的不自由等一系列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急功近利,社会发展的实际能力跟不上城市化跳跃式发展的脚步和房地产业的好大喜功,再加上小私有者天性中的爱占便宜的陋习等纠缠在一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就不可避免了:“在一些地方,尽管合同上标明这个施工期限为两年,但事实上承包商没能按时完工,从而导致一些业主流落街头。”因此一些地皮主人会觉得把合同的签订时间拖到最后会更安全,另一些人也会用延后签订合同来讨价还价,所以工期一拖再拖,“致使钉子户和老街坊邻居之间发生了挥拳动刀、登上报纸的打斗事件”。而精明狡猾的开发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也会趁机煽风点火,“分裂这些地皮主人而私下煽动了这些打斗。”最后受伤害最深的一定还是那些没有金钱傍身、没有权力撑腰的小人物。但小人物的厄运还远远不只是如此,当资本和政治合谋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碾轧过来的时候,小人物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1999年,土耳其政府在地震之后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法律规定为了安全起见,在获得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房主同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拆除一栋老旧危房,所以2009年“国家和承包商利用这个法律来排挤那些阻碍建造高层大公寓楼的小房主。”最为可悲的是,这样的掠夺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借用国家机器明目张胆地进行。而且,在这些被盘剥的房主之下,还有更为底层的房客:“地皮的价格和房租瞬间暴涨,像麦夫鲁特的老房客里泽人那样艰难度日的人,开始逐渐离弃山头。……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未来。”土耳其以它自己的方式把最底层的小人物赶离了城市。
在小说的前言帕慕克引用了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一句话:“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在这句话里,卢梭批判了私有制的产生,并认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并让权力的集中成为可能,私有制的建立者因此成为社会的主宰者。帕慕克在采访中提道:“本质上小说就是非常政治的。……麦夫鲁特带领读者走进伊斯坦布尔众多的政治角落。”很显然,从小说开始到最后指向政治——这才是帕慕克的最终目的。在全世界都對“土耳其模式”一片叫好声中,帕慕克从一个文学家的视角和立场来反思“土耳其模式”的问题和弊端。《怪东西》成书于2014年,这一年埃尔多安的总理任期届满,并在大选中获胜成为土耳其第一任直选总统,土耳其的一个新的时代——“威权主义”时代到来,专家学者们对“土耳其模式”曾经的质疑与担忧终于应验了。
三、《红发女人》:“弑父”和“杀子”循环中的
权力斗争与威权主义时代
帕慕克在谈到《红发女人》的创作的时候说:“我关心政治更因为我是一名小说家。”同时,他还引用了布莱希特的话说:“当他们问起你的政治观点时,不要给读者看你的党牌,而是看你的作品。”很显然,《红发女人》的立意是离不开政治和权力指涉的,或者说帕慕克用《红发女人》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在这部作品里“小人物”的命运又和“大时代”的政治较量纠缠在一起。《红发女人》构思于30年前,写成于2016年,这一年7月15日,土耳其再一次爆发军事政变,但是不到8小时就被埃尔多安强势镇压,大街上随处可见被群殴的政变士兵;接下来的3年,埃尔多安对军队和异己力量(主要是已逃到美国寻求庇佑的政敌居伦和他在土耳其国内的势力)展开了清洗。政变的爆发说明土耳其国内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顶峰,同时也说明埃尔多安的统治出现了危机,也就是说曾经让土耳其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引以为傲的“土耳其模式”出现了危机;但埃尔多安政府对政变镇压及以后的清洗,也意味着帕慕克一直担心和抨击的“威权主义”政治正在上演,土耳其国内多种力量和权力的争斗愈演愈烈。因此,帕慕克便在《红发女人》中用具有高度象征性寓意的“弑父”与“杀子”的关系来完成现实政治中权力斗争的指涉,同时也实现了他通过记录“小人物”的命运纠缠来隐喻大时代政治斗争的目的。
2017年,《红发女人》的英文版刚面世的时候,帕慕克在哥伦比亚特区St.Pauls Lutheran Church的政治与散文书店(Politics and Prose Bookstore)接受了美籍伊朗女作家纳菲西的访谈,并谈起了他创作《红发女人》的初衷。帕慕克提到,1988年当他在写作《黑书》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对既是师徒又像父子的挖井人,师傅对待徒弟有时候和蔼慈祥,有时候又威严专断,这让帕慕克感觉“很着迷。所以当我要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决定特别强调挖井师傅身上那威严、专断的一面。”帕慕克同时强调:“30年后,当我看到土耳其变得越来越专制,我就想写一个节奏明快的故事来讨论这对父子关系。我们的人民依然选择现在的统治者,并投票给他,虽然他们非常清楚他是一个独裁者。”很显然,帕慕克所说的“统治者”和“独裁者”是指埃尔多安。在2016年帕慕克接受土耳其《每日新闻》(Hurriyet Daily News)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埃尔多安政府的专制统治,他甚至把土耳其的政治局面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做对比,并激烈抨击埃尔多安政府操控媒体和言论自由。所以反对“专制”,警醒世人看清“独裁者”的真实面目才是帕慕克写作《红发女人》的真实目的。
《红发女人》着重刻画了三对父子关系、分别由象征着当代土耳其不同政治力量的四个人来两两构成:主人公杰姆的亲生父亲阿肯是一个左翼革命主义者,因为阿肯常年在外流浪所以杰姆从小缺失父爱;少年的杰姆为了贴补家用便跟随有浓厚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的马哈茂德师傅学挖井,两人等同于精神上的父亲,但从小有着土耳其西化主义思想倾向的杰姆很快便和师傅产生了世界观上的分歧,后来失手差点将马哈茂德砸死在井底,自己逃逸;杰姆因为和红发女人的一夜情而有了私生子恩维尔,长大后的恩维尔成为一个宗教极端主义者,他痛恨杰姆的遗弃和西化倾向,最后枪杀了杰姆。小说中关于“弑父”与“杀子”的命题始终纠缠在一起:古希腊“弑父”的《俄狄浦斯王》和古波斯《列王纪》中杀子主题的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被反复言说,这两个古老的东西方故事穿插在马哈茂德师傅对杰姆的教诲和杰姆对马哈茂德师傅的反抗中,也穿插在杰姆和恩维尔的互相试探和伤害中。在小说中,杰姆非常反感师傅的权威和独断,所以当红发女人问他:“你师傅特别专横,特别严厉吗?”杰姆回答说:“他总是希望我服从他的所有命令,事事顺从他。”因为童年父爱的缺失,以及少年之后师傅的专横,让杰姆产生了反抗“父亲”的本能:“我不太喜欢提到父亲,正如不喜欢谈论马哈茂德师傅。”所以当他失手将灌满水泥的桶砸落在井底的马哈茂德师傅头上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找人解救师傅,而是选择了逃逸。30年后当杰姆重新反思当年的事件的时候,他把他的失手“弑父”看作一種潜意识行为。他认为,当年对师傅权威和专断的反感表现在了他和师傅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马哈茂德师傅待杰姆如亲子,但同时他又想用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去左右和控制杰姆,他每天都会给杰姆讲“宗教故事和《古兰经》典故”,用宗教圣典中的故事让杰姆“引以为戒”,警告他不要犯下像故事里一样杀父忤逆或者欺师灭祖的事情。这让杰姆“心神不安”,因此为了报复师傅的警戒,“为了让他也不自在,我讲了俄狄浦斯王子的故事。并在最后做出和故事主人公一样的举动”,也就是像故事主人公俄狄浦斯王一样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马哈茂德师傅。他说:“马哈茂德师傅因为一个故事、一个传说留在了井底。”也就是说,他承认自己潜意识中受到俄狄浦斯王故事的影响:“又或许,我决定让马哈茂德师傅死掉,好让罪过无可挽回。”所以帕慕克借助红发女人的口总结了世世代代父子之间恩怨情仇的本质:“我知道他们会杀死自己的父亲,也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不论父亲杀死儿子,还是儿子杀死父亲,对于男人来说是成就英雄。”帕慕克在此是要说明:无论是“弑父”还是“杀子”最终都是为了成就自我的英雄地位,其本质就是一种权力的争夺,是“父子”关系中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这也是帕慕克在小说的叙述中一再强调的问题。
在“弑父”和“杀子”循环的权力斗争中,帕慕克还反复提到了德国汉学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是德裔美国历史学家,1957年他在新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到,东方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家大都可以称为“治水社会”,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和互助——干时抗旱、涝时抗洪,以此保证供水和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关于纪律、等级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等就显得异常重要,所以容易产生“东方专制主义”。帕慕克在评价《东方专制主义》的时候直接说:“这种组织唯有借助专制、严酷的皇帝和统治者方能成功。这些统治者不喜违抗和顶撞。……因此,统治者在自己身边,也就是在官僚和后宫当中,想要的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是完全服从自己的奴隶,整个机制便是如此运作。”很显然,帕慕克的这一段论述有现实的指涉。自2014年埃尔多安成功当选为第一任民选总统以后,土耳其的政治由议会制迈向了总统制,埃尔多安的个人影响超越于政党统治之上而使土耳其的政治带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2016年,帕慕克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的时候直接说:“我对2015年的大选结果非常失望。”当时土耳其《共和报》的主编邓达尔(Can Dundar)因为该报的一篇报道被捕入狱,这让帕慕克非常愤慨,他谴责埃尔多安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并且强调:“当我们的总统说‘去抓邓达尔的时候,法官就会按照总统所说的去做。我们的行政和法制系统都惧怕总统,没有人敢大声质疑总统的命令。”所以当2016年军事政变爆发以后,帕慕克很快通过西班牙的《国家报》发表声明,他直接提道:“我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任该党主席)的批评者,我有很多的理由批评土耳其的这个执政党。……土耳其的未来,在于实现完全的民主。”在此,帕慕克再一次强调民主、反对专制政治,也就是反对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一人包办”式的家长制、父权制作风;帕慕克对土耳其政治的如此评价在美国著名学者、犹他大学土耳其问题研究专家哈坎·雅乌兹(M.Hakan Yavuz)那里也能得到印证,雅乌兹曾从三方面论证过土耳其的保守民主制,并指出“父权制的家庭观念”是正发党的保守民主制努力想掩饰的伊斯兰主义倾向的第一根源。所以帕慕克在《红发女人》中借助作为“小人物”的父子关系来影射现实政治生活中“大时代”的权力高压,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对此,帕慕克在访谈中也确证过这一点,他说小说“通过故事和意象对‘父与子‘权威与个体‘国家与自由‘阅读和观看等理念进行了探索。这本短小但引人入胜的小说……是对东西两大基本神话的对比: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弑父情结)和菲尔多西的《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弑子情结)。”
2016年政变之后因为埃尔多安对大量异己人士进行逮捕和清算,也使土耳其和欧盟本就磕磕绊绊的关系降到了冰点。11月26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无约束力决议,建议暂停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土耳其的威权主义政治已经影响到了它的外交口碑和政策。同时,国家经济也呈现出衰败的态势,2016年土耳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已超过10%,青年人的失业率也突破24%,原来引以为傲的“土耳其模式”已面目全非。2019年11月初,埃尔多安声称,如果欧盟继续非议土耳其国内事务,土耳其将开放叙利亚难民通向欧洲的大门,土耳其正在成为区域安全最不稳定的因素,土耳其的政治和命途走向也变得扑朔迷离。很显然,不仅经济衰退,权力体系的合法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权与民间不同阶层间的利益争夺导致土耳其权力阶层关系的对立,历史似乎又回到了第一个时期,甚至更早的危急时刻。
美国学者迈克尔·麦克加哈在他写的《帕慕克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土耳其时,帕慕克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一位寄居在东方的西方人,东方的很多东西与自己格格不入。……到了纽约,他才感到自己从根上是土耳其人。”帕慕克深深地爱着土耳其,作为土耳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帕慕克也让世界更加关注土耳其。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历史,甚至正在改变历史,帕慕克笔下的人物如此,帕慕克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有可能影响历史发展的作家,帕慕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书写历史。在创作中他无论是哀叹奥斯曼帝国的荣辱,还是吟唱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或者批评当代土耳其的政治威权,都是历史发展滚滚洪流的一种声音、一滴浪花,是他作为个体“小人物”在浩瀚的历史长空中对当代世界的贡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帕慕克是值得世人尊重的伟大作家。
(责任编辑 魏建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