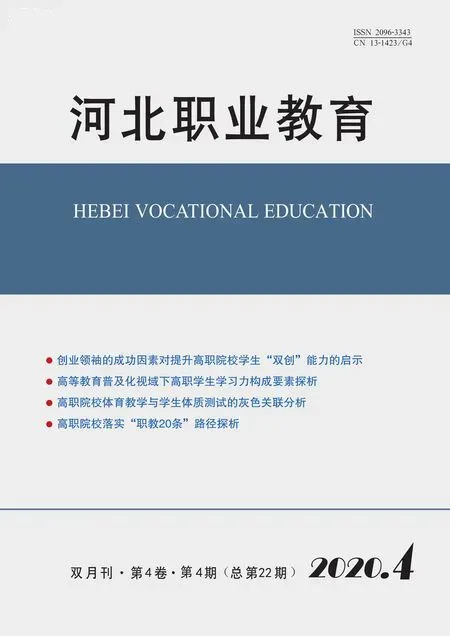创业教育研究的国内文献综述
2020-08-27钱华生
钱华生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一、创业教育的概念与内涵界定
国际首次以官方名义提出创业教育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 年11 月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l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是指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它对于拿薪水的人同样重要,因为用人机构或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正在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神,创业和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管理技能。”[1]创业教育(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在国外比较通行的是全美CELCEE 给出的定义,即创业教育指提供人们以概念和技能,辨别他人忽略的机会,具备洞察力、自我评估能力和知识技能,在他人犹豫不决时果断地行动的过程。[2]
国内开展创业教育的时间较晚,受国外创业教育理论的影响较大。2000年,彭刚在《创业教育学》一书将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总结为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创业心理品质。[3]郭洪认为所谓创业教育就是开发受教育者创业基本素质,提高受教育者创业能力的教育活动。[4]李艳艳(2015)认为创业教育是指以课程教学与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培养学生未来从事创业实践活动所必需的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并将其内化为大学生创业素质而进行的一种培养教育。[5]
目前创业教育的概念很多,但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人才说”和“素质说”。“人才说”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是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要自我创业。“素质说”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创业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创业者的素质,特别是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6]全美 CELCEE 给出的定义就是基于“人才说”,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内的定义则是基于“素质说”。由于创业教育的内涵难以界定,必然导致其构成维度混乱,难以测量。
二、创业教育的测量
美国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早,其创业实践提供了三种典型的创业教育模式,即以培养创业意识为主的百森商学院、以培养实际管理经验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培养系统的创业知识为主的斯坦福大学,这三种模式可以认为是创业教育的三个维度。徐少春(2017)根据视角的不同,将创业教育分为创业者特质教育、创业过程教育、创业认知教育和创业方式教育。[7]
朱红、张优良(2014)将创业教育形式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基础性教育,包括创业课程和创业讲座;第二,模拟性教育,以创业大赛为主要形式;第三,实践性教育,学生真实地进行创业实践;第四,观察学习性教育,学生通过和企业家、创业导师进行交流,对创业榜样进行观察和学习。[8]
创业教育的多种类型构成其不同的维度,维度的不同,导致创业教育开发出来的量表就会有所差异。整理近年来文献中所使用的创业教育量表,如下表1 所示:吕荣(2011)对创业教育的测量采取了11个测量项目,11个项目得分的加总再平均后,就得到创业教育的测量值,这种测量方式没有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可信度较低。宁德鹏(2017)的创业量表分成了个人因素和学校因素两个维度,并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但两个维度的划分过于粗糙,没有对创业教育的内容进一步区分,在实际使用中价值不大。李静微(2013)的创业量表分为三个维度,也经过了信度与效度检验,但其内容区分不太合理,如创业教育内容中就不包括创业者或企业家定期讲、创业技能培训或模拟演练以及参与创业大赛,而这些往往是高校创业教育的重要内容,所以是否可以理解创业教育内容满意度与创业教育学习效果这两个维度是对创业教育内容的不同区分,创业教育参与维度要不就是不完整,要不就显得多余。郭洪等(2009)借鉴了国外的量表,其测量的创业教育的内容明显较少,不符合中国创业教育的现状。
三、创业教育评价体系与作用机制研究
(一)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研究
高校创业教育评价体系一般是采用单变量进行研究,研究方法多采用描述分析、因子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调研的对象多是在校大学生群体,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被调查者最为关心的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创业教育评价体系。下表2 是根据知网查询较为典型的研究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的文献。
商光美(2012)在通过福建四所高校579 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发现政策颁布与宣传(社会因素)、高校创业教育(学校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资本对创业教育影响显著。[11]宋之帅等(2012)所构建的创业教育评价体系是由课堂教学体系、课外实践平台和创业教育环境三个一级指标构成,其通过安徽某高校学生问卷调查及专家评判发现,该高校在课程设置及师资背景等方面工作较好,但在资金支持和社会协同方面做得欠缺。[12]余瑞玲(2006)通过对高校参赛学生、自主创业学生、经济类以及中文系学生的分层调研,收回727份有效问卷,经过分析认为大学生创业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系统实施;大学生创业教育要关注差异;针对不同需求分层分类进行;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目前主要是培养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以及大学生创业教育应以科技创业为导向。[13]吴俊清等(2011)通过对30 个创业大学生的访谈和100位创业型企业家的问卷调查发现,创业大学生与创业型企业家对于创业课程的选择、风险认知、创业目标、团队认知等方面都存在差异。[14]

表1 创业教育测量指标

表2 创业教育评价研究的比较
通过对以上样本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其研究对象差异很大,有创业学生、在校学生和创业型企业家,在不同的时点研究创业教育的影响,结果自然会有差异,而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的创业教育评价体系就会存在差别,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的不同,就无法比较不同高校创业教育水平的高低,高校之间也难以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交流,从而无法带动高校整体创业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创业教育作用机制研究
创业教育作用机制是研究创业教育是如何对大学生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的机理进行研究的,但仅通过创业教育与创业行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是比较困难的,目前研究较多的是通过创业意向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下表3是通过知网查检索典型的关于创业教育作用机制研究的文献。
李静微(2013)将创业教育作为自变量来研究对因变量创业意向的作用,创业教育分为创业教育参与度”“创业教育内容满意度”和“创业教育学习效果”三个维度,研究发现,创业教育参与度和创业教育内容满意度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呈显著正相关,创业教育学习效果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呈显著负相关。另外,学校的不同地理位置、学校的不同类型对创业教育与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10]宁德鹏(2017)以创业教育为自变量、创业能力和创业动机为中介变量、创业行为为因变量,对全国26 个省102 所高校展开问卷调查,获得30887 份有效样本,研究发现创业教育直接正向显著影响创业行为,同时也通过中介效应间接正向显著影响创业行为。[1]吕荣(2011)通过对大专三年级、本科大四年级以及读研的创业大学生进行86 份问卷调查(专科比例为42%),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创业能力与创业教育进行了分析,发现创业能力中的机会识别能力,自主学习能力,领导决策能力,管理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挫折承受能力与创业教育呈显著的正相关,创业教育能够有效促进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提升。[9]郭洪等(2009)通过对四州四所高校在校大学生322份问卷调研,发现学生的个人特质对创业态度的影响显著,创业态度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也显著,而个人特质受在校经历(创业教育)的影响显著。[4]
通过对以上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对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是通过创业意向和创业能力进行的,吕荣虽对已创业学生进行调查,但根据郭洪的研究,创业能力不仅受创业教育的影响,还受个人特质的影响,研究中并没有将个人特质进行控制。李静微将创业教育分为不同维度,分析了不同维度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同时以职业价值观为调节变量,来考虑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宁德鹏的研究中也将个体特质作为前置变量。但李静微、宁德鹏都是通过在校学生的调研来研究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不妥当的,因为在校学生对创业行为的问卷回答完全是基于主观判断,而无客观事实。郭洪的研究中虽仔细分析了个人特质对创业知识、创业态度以及创业能力的影响,但其对创业教育(在校经历)的测量只采取四个项目,即是否参加创业设计大赛、是否接受创业指导与培训、实习经验以及参加创业团体。[4]这四个测量项目能否完全表达创业教育的全部内容,是值得商榷的。从上述总结发现,当前创业教育的实证研究方法总体上比较单一,无法有效的解决作为前因变量创业教育和结果变量创业行为与其他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创业教育内涵的界定与实际科研工作的矛盾
关于创业教育的内涵,国内学者将其定义为“素质学”,或者是“人才说”加“素质说”的比较普遍,但在科研过程中,采集的调查样本更偏向于“人才说”,即采用已创业的大学生作为调查样本来研究创业教育对其创业行为或创业能力的影响,而公司中创业型的管理人员由于在实践在难以识别,所以也就很难纳入调研范围。所以这就造成了科研实践中采用“人才说”与理论中采用“素质学”相矛盾。

表3 创业教育作用机制研究的比较
(二)创业教育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
创业教育的测量,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测量指标体系,仍有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首先,现有的测量维度缺乏理论的支撑,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清晰,因此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为创业教育测量提供理论支持,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也需进一步明晰。
其次,现有的一些测量指标能否表征创业教育尚存疑问,需要选用更精准的指标进一步进行完善。例如,创新精神培养采用五点量表,来表征创业教育内容满意度就不恰当,因为受访者可能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创新精神,或者对创新精神的理解上差异很大。
(三)创业教育评价体系没有考虑“时滞效应”
国内创业教育评价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短期效果角度进行分析的,没有考虑创业教育的“时滞效应”,即在校参加过创业教育的大学生、已创业在校大学生(包括毕业5 年之内的大学生)和毕业超过5年的创业大学生,他们对于创业教育问卷调查中同样的问题答案是有所不同的。吴俊清等(2010)通过对30个创业大学生的访谈和100位创业型企业家的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对于创业教育的认识在好多方面有所差异。这说明,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创业教育的效果在短期内和长期内是有所不同的。同时,徐岩松等(2017)曾对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仿真创业实践项目的调查发现,参加仿真创业实践项目的有245 人,占总体的61.4%,都准备以后创业。[15]这就是“时滞效应”存在最明显的证明。
(四)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研究不够深入
国外对创业教育效果的研究是通过分组来实现的,如Matlay对8所高校的64名学生分组进行为期10 年的追踪调研,发现接受创业教育与没有接受创业教育的相比,其创业知识和技能有显著提高,职业有显著性变化。[16]但Matlay并没有对64名学生进行随机分配,所以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分组。就国外对创业教育的研究方法而言,我国的创业教育研究还不严谨,那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研究自然就不够深入。
五、创业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创业教育的未来研究可以在对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的情况下,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按时间划分为在校大学生、毕业后1-5年的大学生以及毕业后6-10 年的大学生。以5 年作为时间节点,这与国家创业大赛对在校创业大学生的时间认定是一致的,毕业后以10年为终点,这是因为毕业时间越长,影响创业行为的因素就越多,对创业教育效果的测量就越困难。在随机分组的情况下,对不同时间段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进行研究,就可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创业教育评价体系。
不过,就创业教育的整体而言,对大学生进行完全的随机分组来研究创业教育在现实中是很难进行的,因为高校不可能随机让一部分学生接受创业教育,一部分不接受。但如果把创业教育分成多个维度,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仅对单个维度进行对照试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上文提到的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仿真创业实践项目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因为仿真创业实践项目的摊位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大学生都能接受到这样的锻炼,此时研究者就可以从多个班级选取学生随机分成两组进行对照试验,并跟踪观察其毕业后5年内的创业情况,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就可以发现仿真创业实践项目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依据同样的道理,可以依次研究创业教育的其他维度,最终勾画出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