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桥夜话
2020-08-15张翎
张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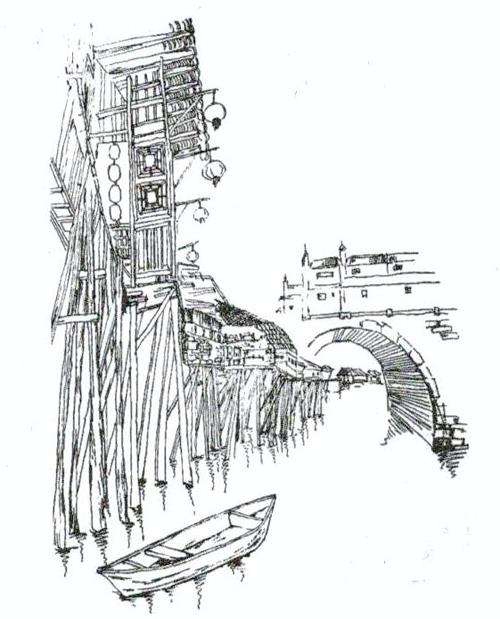
“阿爸,你怎么才回来?阿妈说你不要我们了。”小树说。
“她知道个屁。”
阿贵把儿子托举上来,放到后座上。小树摸了摸绑在摩托车上的那个厚厚的黑色塑料袋,冰凉,带着潮气,手指碰上去有一些坚硬的棱角。
“阿爸,我不要苹果。阿妈说苹果放老了像棉花,我要杧果。”
阿贵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把个嘴巴惯得,还卡亡果呢,吃个屁。”
小树觉得今天阿爸的脸有点长,见着他不是平日的欢喜模样,就噘了嘴,坐在后边不敢出声。
“你阿妈这阵子,出过门吗?”阿贵问儿子。
“去过集市,和奶奶一块。”小树说。
“有谁来看过她?”小树低头想了半天,才说:“只有阿秀表姨。”
阿秀是阿珠的表姐,嫁在邻村,是阿贵和阿珠的介绍人。
“说了些什么?”阿贵警觉地问。
“没听见,她们关着门,我和阿权哥哥在外边玩。”小树说。
阿权是阿秀的儿子,比小树大两岁。
阿贵腮帮子一鼓一瘪,像在嚼豆子:“这个烂女人,要是下回让我看见,立马赶出门。”
“她给我带了蛋糕,奶油的。”小树小声替阿秀表姨辩解着。
“你就知道吃!”阿贵呵斥。
小树从没听过阿爸用这个腔调说话,瘪了瘪嘴,想哭。
阿贵伸出手来,撸了撸儿子的头发:“阿爸让你做件事,下回你要是看见你阿妈一个人出门,立刻给阿爸打电话,用奶奶的手机。记住了?”
小树看了阿爸一眼,点了点头,嘴巴抿得很紧。
“下次回来给你买水枪,天热了,打水仗。”阿贵说。
小树的嘴角立刻松了,欢天喜地问阿贵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父子俩骑着摩托车进了家门,只见阿贵妈和阿珠正在院子里晒被褥。窗架和桃树之间拉起了一根粗绳子,阿贵妈和阿珠一人扯两个被角,晃平整了,晾上去,再夹上几个夹子。太阳在云里进进出出,天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似乎撑不太住。小河正坐在一把竹圈椅里,用手指头追着天上一路小跑的云朵,嘴里咿咿呀呀。
阿贵放下小树,走过去抱起小河。小河怔怔地望着他,面无表情。
“没良心的,叫你认不出我,叫你认不出我。”阿贵把小河高高地举起来,在半空转了几个圈。小河哇地哭了,哭了几声,又咽了回去,咯咯地笑了起来。
阿珠迎上来,怯怯地问:“我去开热水器,你,洗澡?”
阿贵没理她,只对他妈说:“你别瞎操心了。我跟你说过,阿意住家里不合适,她带着她男人,就咱这个条件?”
阿贵妈拿起藤条拍着被褥,院子里扬起细细的一片粉尘。
“新娘子头次回娘家,怎么也得住一夜,这是规矩。”她说。
“人结婚都快两年了,还说这话。”
“只要她没回来过,她就还是新娘子。”
阿珠进去开热水器了。家里的卫生间,是阿贵结婚的时候盖的,在后院,另起了一套走水系统。阿贵妈见眼前没人,就斜了儿子一眼。
“你这么久不回家,总得打个电话回来吧?就算不打电话,家里给你打电话,你也得接吧?爹娘你可以不管,我们自生自灭拉倒,那老婆孩子还是不是你的了?”
阿贵没回话,只是把小河放回到圈椅里,自己去卸摩托车上的东西。阿贵妈过去搭手,却被那个重量吓了一跳。
“皇天,這足足有五十斤吧?这么多水果,吃不完就烂,你不怕糟践天物?”
阿贵打开塑料袋,往外拿东西。塑料袋里还有塑料袋,大的套小的好几个,都沉甸甸的,口子用细铁丝扎住。
“不是水果,是稀罕物件,等着阿意他们来吃。”
阿贵妈拿过一个口袋,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有股隐隐的血腥味。
“赶紧放冷冻室,放不下就匀几个口袋到世华茂盛他们家,借他们的冰箱使一使。”阿贵交代说。世华和茂盛都是他们家的近邻。
“什么东西?别是牛肉?不是说好要宰牛的吗?”阿贵妈问。
阿贵不答,只问爸去哪儿了。
阿贵妈说在地里呢,刚把牛弄下山来。阿贵说怎么不等我回来。阿贵妈说昨天等了你一天。阿贵拔腿就朝外走去。
阿贵拐过小道,远远就看见他阿爸杨广全蹲在自家那块地边上抽烟,头发被风吹起来,哆哆嗦嗦的,像一朵扬着絮的蒲公英。
牛拴在一棵树身上,还没驾辕。五进士村的牛,一年到头都放在山上散养,到了耕种时节才找回来,用完了再送回山上。山替人养着牛,山也替人看着牛,第二年上山找牛的人家,丢了牛的少之又少。偶尔有牛跑到邻村去了,辗辗转转,迟早有人送回来。一个穷得只长毛不长肉的地方,却居然不出盗牛贼,也是一桩奇闻。只是如今村里已经没有几户人家还在认真耕种,养牛的,居多只是为了卖肉。
好一阵子没见着,牛老了,身上的皮起着灰黑的皱褶,乍一看,像一块脏石头。阿贵拍了拍牛背,牛漠然地看了他一眼,眼神混浊如泥。阿贵不禁想起了小青。“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是小时候在学校读书时,语文老师教给他的话。那时听着挺好,现在想着难免有点酸牙。不过,牲畜大概也真是有心的,只是他看不见它们的心,他只看得见窗口。窗口和窗口各不相同。
“如今的牛,太他娘的享福了,耕一两天地,玩儿似的,下山还老不愿意。”杨广全说。
阿贵脱下鞋袜,将袜子揉成一团,塞进运动鞋里,卷起裤腿下水田试了一试,咝地抽了一口气。
杨广全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来,扔给站在水里的儿子。
“先抽一支再说。”他说。
今年的天冷,但是草木有根,根只听土的。土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土有自己的信息系统。土告诉根时令已到,一山的树木便都郁郁葱葱。桃花开得粉一丛白一丛,衬在绿上,很是醒目。
阿贵从水里爬上来,在杨广全身边蹲下,借了他的火,两人一口一口地抽起烟来。
田埂上有一只鹅,不知是从哪家篱笆里钻出来的,大摇大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颈子一伸一缩。阿贵扔了块石头过去,正正地落在那爿肥臀上,鹅嘎地惊叫了一声,翅膀拍着地,半飞半跳地逃走了。
“小时候妈总吓唬我,说鹅逼急了,能啄死人。我没少作弄鹅,可鹅从没追过我。”阿贵说。杨广全笑了:“禽兽也知道欺软怕硬。”
“阿爸,今天不用急,等太阳再把水晒一晒。咱不杀牛了,耕完地就卖了,听说今年的市价,一头整牛,能卖到三万多块。”阿贵说。
杨广全急了,嗓门都变了调。
“这不行。你妈说的,阿意出国的时候,全村都送过路菜。她在外边结婚,家里也没摆过酒。这酒席是省不了的,你若省了,你妈得急死。”
阿贵见他爸脸上的褶子都挤成了一堆,就拍了拍老爷子的肩膀,说:“我敢吗,省那个钱?我带了驴肉回来,五十多斤,黄棵蘸红烧驴肉汤,叫他们吃得认不得家门。”
杨广全又吃了一惊。
“驴肉那是比牛肉还金贵啊,你钱多了烧啊?”
“运输队里有头驴,皮肉烂了,流脓发炎。老板不敢用狠药,怕万一死了卖不出去,就宰了。我买了一大块,比市场上便宜一半。”
杨广全这才不吭声了。
“真是头好驴啊。”阿贵叹息道。
小青被拉走的那天早上,他不在。等他回来的时候,小青已经成了案板上的肉。他以为自己会多伤心,但是他没有。小青活着是长痛,死了是短痛,他倒情愿小青早死,能少遭些罪。再说,小青的肉,他不吃,也是别人吃,一样是吃,他至少也得着了小青的最后一点好处。装驴肉的时候,他觉出了自己的心硬,只要他没看见小青的眼睛。
“阿爸,以后田里的事,还是可以叫阿珠来做的。她现在整天在家,能干些什么?”阿贵说。
杨广全看了儿子一眼,只觉得这话的语气有点奇怪,像是质问,又像是打听。他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一个女人,带两个娃,一天也够她忙的。”他含含混混地说。
阿贵哼了一声。
“我妈当年,也是两个娃,还有一大家子人,她照样下地。”
杨广全没吱声。他把一支烟抽到头了,又掏出一支来,接在那支的尾巴上,续着了火。他抽烟的时候,吸得急,吐得却很慢,烟从他的鼻孔里钻出来,变成一个一个环环相扣的圆圈。渐渐升高了,圆圈涣散开来,各行已路,扁扁长长的失去了形状。
“所以,你妈才,走了两回。”杨广全轻声说。阿贵觉得阿爸老了,不仅话少了,而且说话的腔调也变得绵软了。阿妈的事,全村人都知道,阿爸从前说起来,从来不忌讳使用“逃”这个字。
天终于稳住了,云彻底散了。露出一片朗朗的日头。阿贵舒了一口气,却想起小时候,每天夜里躺下,就期盼着早上能下雨。只要下雨他就赖在床上,不下地也不上学。阿妈喊了又喊,终于喊不动他,就自己披着蓑衣出了门。他躺在床上,想到阿妈裹着蓑衣穿着高筒胶鞋在泥路上一步一滑的样子,很想爬起来追上阿妈,可是脑子愿意,身子却不肯。年轻的身子有力气,年轻的脑子打不过年轻的身子,身子十回有八回赢。
“阿爸,你当年在外边揽活儿,待久了,回家习惯吗?”他问。
杨广全嘿嘿地笑了,眼睛里飘过一丝轻狂:“你天天在外头,这话用得着问我吗?五进士这么个地方,一眼看过去,就到底了。那时候,家里又是这么个烂摊子。在外头,能叫人张狂啊,有时也真想过,就死在外头算了。”
“可是你……”
阿贵原想说“你没死在外头啊”,这话在肚肠里走过一遭,就改了道,变成了“你,还是回来了啊”。
“女人能走,男人走不了。女人是被子,男人是屋顶。被子盖在哪张床上都行,屋顶挪不了地方。”杨广全叹息道。
阿贵怔了一怔。阿爸这话是把冰凉的刀子,钝钝地捅了他一下,就像那天小青看他的那一眼,叫他心中突然生出一丝栖惶。
“那一回,我妈走了那么久,你就没想着去找?”他问。
“没用。那回我知道她铁了心了。一个人要是铁了心要走,那是天也拦不住。”
“哪怕有了孩子?”
“哪怕有了孩子。”
阿贵把一支烟抽到了头,扔进水田,哧的一声,水破了一个洞,烟头沉下去了,冒起一缕细细的青烟。阿贵怔怔地盯着烟头栽下去的那个地方,额头上有一根筋在微微颤动。
“你妈没想扔下你,她只是不想活了,她不想你跟她一块儿死。”杨广全似乎猜出了儿子已经滑到舌尖的那句话,就把那话堵了回去。
阿贵掏出烟盒,自己拿了一支,也递了一支给阿爸。这是他回到家之后的第二支,他阿爸的第三支。
“她丢得下我,却不会丢下阿意。”阿贵说,“要不是阿意,这个家就散了,也就没你了。所以你妈偏待阿意,我从来没说过半句话。”杨广全说。
偏待?仅仅只是偏待吗?阿贵在心里暗暗地问。假如,那年家里没有因为阿意上大学,而杀了那头存着给他做聘礼的牛;
假如,那些年阿意没有出去上学,而是待在家里帮着干活儿,或者像别的女孩那样,找个家境好些的男人嫁出去了,不仅给家里省一张吃饭的嘴,或许还能悄悄地往家里塞几个体已钱。那么,他也许早就娶下了一个知根知底、说得通话的女人。那个人肯定不从越南来,也肯定不会有一个像阮氏青明珠这样的名字;
那么,他的儿子不会是四岁,也许会是十三岁,也许不叫小树,而是叫杨衍康,或许杨衍运,或许杨衍成——衍是他们那一代的辈分字。
假如。也许。
是他们那一代的辈分子。
假如。也许。
阿贵把攒在心里的那口气,在胸腔里咕噜咕噜地运成一口痰,惊天动地地吐了出去。几只鸡扑过来,争抢着那个被尘土成一团的黑球,仿佛那里头藏的,是一只肥硕的死知了,或是一只活着的大青虫。
“我留了点钱,你妈不知道。”杨广全从烟盒里窸窸窣窣地掏出一张纸头,“户头和密码都在这里。这些年,家里亏待了你。”
“你結婚的时候,我都没敢拿出来,怕娶的那个人不知底里。现在看阿珠那样子,倒是老实规矩,肯跟你过日子的。”杨广全对儿子说。
阿贵冷冷一笑,说:“知人知面。”
杨广全正要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阿贵已经站起来,赤着脚,过去竖边上套犁。牛吃饱了,正有力气,老老实实地背上了辕,和主人一起哗啦哗啦地下到了水田。
阿贵妈跟阿珠多次提过的“第二回落进同一条河里”的事,发生在阿贵七岁那一年。那年阿贵刚上小学一年级。
一年级是城里人的说法。阿贵上的学校,就在村里的一个破院落里,最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学生,其中有的来自邻村,从七岁到十二岁不等。教书的只有一位民办老师,手里捏着一摞六个年级的课本,从这本里翻几页,从那本里挑几节,讲到哪里是哪里。
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媳妇和婆子们也会拿着针线活儿,坐在院子里听老师说几句大舌头的普通话。到了农忙,连老师自己都回家种地去了,学校就空无一人。城里人说的几年级,到了五进士村,就成了村里人区分孩子大小的一个模糊说法,只为偷懒,跟学校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那时候刚开始落实分田到户制,杨家分到的几亩地,虽然远一些,却都还是平地,比起那些分到山地、有牛也使不上的人家,自然幸运了许多。那一年快到春耕时节,婆婆好像打了兴奋剂,让人扶起来靠在墙上坐着,将全家都喊齐了商量事。
商量其实是一种含混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告诉,或者说,指令。婆婆做得了杨家每个人每只碗的主,婆婆唯一需要商量的人,只是她自己。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