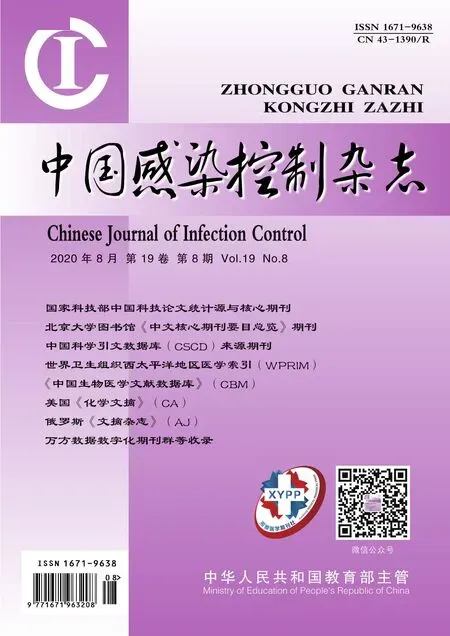一起医院同事混合家庭成员感染新冠肺炎事件的调查
2020-08-14田克卿姚梦雷蔺茂文曾旻敏雷若倩黄继贵
田克卿,刘 天,姚梦雷,苏 斌,江 鸿,蔺茂文,曾旻敏,殷 俊,雷若倩,王 丽,廖 强,黄继贵
(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息组,湖北 荆州 434000)
2019 年12 月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2020年1月7日此不明原因肺炎的致病原被鉴定为新型冠状病毒[1]。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正式命名为COVID-19[2]。荆州市自1月9日报告首例COVID-19病例后全市病例逐渐增加,1月22日辖区内多家医疗机构被市政府指定为发热门诊及收治定点医院[3]。截至2月13日,既为发热门诊又为定点收治医院的某医院,报告医护人员COVID-19病例13例,家庭成员关联病例11例,医院医护人员罹患率为0.62%(13/2 093)。为还原事件发生始末,为今后类似事件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现将此次事件发生、流行病学特征、传播链等情况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年1月13日—2月13日,某医院医务人员诊断为COVID-19的疑似病例、确诊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中(主要是家庭成员)疑似病例、确诊病例。
1.2 相关标准、定义 诊断标准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4]。密切接触者的判断标准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5]。聚集性疫情判断标准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聚集性疫情中的“首发病例”定义为本起聚集性疫情中最早发病的病例。发病时间定义为首次出现临床症状的日期。暴露时间定义为密切接触者与病例发病前2 d至病例隔离的接触日期。确诊时间定义为病例标本核酸检测呈阳性结果的日期。
1.3 调查方法 采用面对面或电话调查病例及家属,询问重点部门负责人、公卫科负责人等方式,调查病例的基本信息、发病与就诊、危险因素与暴露史、密切接触者等信息。通过继发病例与首发病例首次暴露时间、末次暴露时间、继发病例发病时间,计算最短潜伏期、最长潜伏期。
1.4 统计方法 采用计数、中位数(最短/小~最长/大)、构成比等统计指标对数据进行描述,应用Excel 2016建立数据库及作图。
2 结果
2.1 时间特征 共收集25例COVID-19病例。首例病例在2020年1月16日发病,两个发病高峰分别为1月23日、1月26日。末例病例在1月30日发病,首、末例病例发病时间间隔为14 d。见图1。病例的最短潜伏期中位数为4 (0~9) d,最长潜伏期中位数为7(3~14) d。全部病例发病至就诊时间隔中位数为2 (0~9) d,1月23日前发病病例为4(1~9) d,1月24日及之后为2(0~3) d;医务人员病例为1.5(0~8) d,家庭成员病例为3(1~9) d。见图2。

图1 某医院COVID-19聚集性病例流行曲线

图2 某医院COVID-19聚集性病例发病潜伏期时间分布
2.2 人群特征 25例病例中位数年龄为38(23~76)岁,男性11例,女性14例,性别比为0.79∶1。医护人员占52.0%(13例),干部职工占12.0%(3例),家务及待业占12.0%(3例),农民及商业服务分别占8.0%(2例),离退人员与学生分别占4.0%(1例);医院职工占56.0%(14例),其中医生20.0%(5例)、护士32.0%(8例)、管理人员4.0%(1例),职工亲属占44.0%(11例)。
2.3 地区特征 该医院共92个医疗相关科室,2 093名医护人员,医护人员COVID-19罹患率为0.62%(13例);1例在医院的一个管理部门,罹患率为11.1%(1/9)。13例COVID-19医护人员分布在4个科室,罹患率为:W科26.5%(9/34),X科6.9%(2/29),Y科3.7%(1/27),Z科11.1%(1/9)。
2.4 临床症状及严重程度 25例病例中,发热20例(80.0%),咳嗽10例(40.0%),肌肉酸痛8例(32.0%),咽痛7例(28.0%),乏力6例(24.0%),气促4例(16.0%),头痛及关节酸痛3例(12.0%),寒战与胸闷各2例(8.0%)。临床分型:轻型4例(16.0%),普通型18例(72.0%),重型3例(12.0%)。死亡1例,该患者既往有慢性肾病40余年,平常1周进行1次血液透析,死亡原因为COVID-19感染引起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2.5 聚集性疫情及传播链 本事件由4起聚集性疫情组成,2起病例中有3例存在交叉接触(调查核实后无交叉感染可能性),另2起病例均无相互接触史。
2.5.1 聚集性疫情1 本起聚集性疫情起始场所为W科,首发COVID-19病例医生1有武汉旅行史,回荆后在上班期间(1月16日为工作日)发病,工作期间(16、17日)与同科室医生、护士接触。随后(1月18—26日)同科室8名医护人员陆续发病,再之后护士1、护士3的家庭成员分别出现病例。W科继发的8例病例均无外地旅行史,1月1—30日W科未接诊来自武汉/其他外地旅行史的病例。见图3。
2.5.2 聚集性疫情2 本起聚集性疫情中,A某长期居住武汉并于1月20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发病。自诉在武汉期间可能接触过类似症状的人,A某在1月22日回荆,随后参加2次家庭聚餐(1月22日中餐、晚餐),聚餐者中X、Y科医护人员及家属共计7人陆续发病。见图3。
2.5.3 聚集性疫情3 B某常年在武汉工作,对武汉工作期间与回荆途中(1月21日)接触情况回忆不清。A某1月23日发病,随后B某的密切接触者“医院管理人员1”及其母亲相继发病。见图3。
2.5.4 聚集性疫情4 本起聚集性疫情中,Z科的护士6在1月19日回荆途中在汉口火车站转车存在被感染可能。护士6于1月24日发病,其母亲1月22日从潜江抵荆与其共同居住并于1月27日发病。见图3。

图3 某医院COVID-19聚集性病例接触史及传播链
2.5.5 筛查及密切触者排查 1月26日—2月13日该医院以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为指标对全院职工开展监测,异常者前往发热门诊排查,共发现发热9人、腹泻4人、咽痛4人,经血常规、CT检查及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后均排除COVID-19。1月28日—2月3日对发热门诊、预检分诊、乳腺外科、肿瘤科、重症监护病房(ICU)、眼科和放射科的172名医护人员进行血常规、CT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筛查,结果均为阴性。4起聚集性疫情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90人,21人发病,续发率为23.3%,其中W科室的续发率为24.2%(8/33)。
3 讨论
2020年1月20日新华社报道,首次证实有医护人员感染[6]。索继江等[7]认为医院感染现象在COVID-19疫情发生初期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意大利报道20%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被感染[8],很可能是因为医务人员防护物资储备不足所导致[9]。该医院共2 093名医护人员,COVID-19疫情以来该医院作为指定的发热门诊及定点收治医院,出现医护人员COVID-19病例后,各级领导高度关注。最后调查结果显示聚集性疫情1是因1名医生在武汉感染回荆后带病上班,通过接触感染同事,感染的同事随后与家人接触引发家庭内传播,属于医院同事混合家庭传播的聚集性疫情。本起聚集性疫情发生时间处于全国疫情初期,社会普遍防护隔离意识不强,再加上医护人员平时接诊过程未穿防护服,不能阻止微生物渗透[10],故无法避免本次疫情发生。疫情发生后该医院迅速开展重点科室全科筛查,每日全覆盖监测病例发生,及时关闭W科室,所有病例与密切接触者均居家隔离。通过一系列强力筛查和控制措施后,疫情被迅速控制。该医院在后续承担COVID-19病例救治任务过程中,采取强力防控措施,如一线医护人员整体轮换制度,严格执行个人防护措施,划分风险区域针对消毒,规范管理其他疾病患者及探视者。监测资料显示截至3月18日该医院参与防控的一线医护人员均未在救治患者过程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与国内文献[11-12]报道一致。提示在行政防控意识增强,防护控制措施落实的情况下,一线医护人员COVID-19医院感染风险降低。
本事件由4起独立聚集性疫情组成,2起聚集性疫情中3例病例的交叉接触不具备交叉传染可能。具体分析如下:聚集性疫情2 调查初期错误获得A某(实际为首发病例)发病时间为1月30日,由于其他人均无武汉旅行史。前期将传播链考虑为护士4、医生5在医生2发病前1 d(1月21日中午)聚餐接触感染,护士4、医生5再通过1月21—22日参加家族聚餐传给多名家族成员。支持这一传播链的前提是假设医生2在潜伏期(发病前1 d)传染给护士4和医生5,护士4和医生5也在潜伏期(发病前4~5 d)传染给6名家族成员。Rothe等[11]报道一起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案例,不过该报道后期补充材料显示该无症状者在接触之前已有疲倦、肌肉疼痛并服用了退热药,目前未发现文献支持发病前4~5 d具有传染性的明确证据。后期调查发现A某实际发病时间为1月20日,并且该病例自述可能在武汉接触过类似症状的人,最终聚集性疫情2的传播链得到合理解释。笔者认为在流行病学调查过程如遇到传播链不清晰时,需要在尊重疾病普遍规律的前提下保持质疑态度,通过多次调查获取真实可靠信息,从而还原出科学合理的传播链。
国内有研究显示,深圳市家庭范围续发率为11.2% (95%CI: 9.1-13.8)[12],Yang等[13]研究推算出密切接触者的续发率为35%,本次疫情中W科室的续发率(24.2%)处于居中水平。本研究的最短潜伏期中位数为4(0~9) d,最长潜伏期中位数7(3~14)d,与Linton等[14]通过模型推算的结果(5 d,2~14 d)以及研究[15-16]计算的结果[分别为6.4 d,5.1 d (95%CI:4.5~5.8)]类似,同时与国内部分地区如天津[17]、武汉[18]的报道相符。本调查显示1月23日之前发病就诊间隔中位数较1月24日及之后长,医务人员发病至就诊间隔较非医务人员短,提示随着全国疫情发展以及全国范围启动应急响应,病例发病后的就诊意愿、健康意识较前增强,医务人员就诊意愿、健康意识较非医务人员强。
本组4起聚集性疫情的调查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尤其是首发病例受到舆论压力及本人不配合,未获得其接触史详情,未进行采样检测,调查工作主要以定性与控制优先。事件发生时市面上未推出抗体检测试剂,后期无法利用抗体检测结果支持溯源,今后类似调查建议可采样留存,以备后期新试剂推出能复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