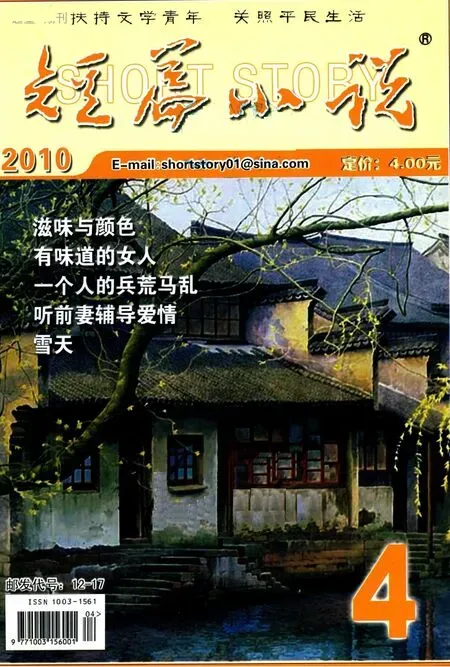旧时血案
2020-08-13陶诗秀
◎陶诗秀
责任编辑/乙然
1
陈国荣消失的那个夏天,铁城下了一场持续了七天的雨。
因为这场雨,未名巷里怨声载道。邹叔一边用木棍通堵在下水道里的一只死猫,一边骂:他姥姥的,这雨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我跑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叫住我:陈晓晓,去把你家的铁钳子拿来。我应了一声,飞快地钻进屋檐下,全身都已经湿透。
这片棚户区,就是不下雨,下水道也老是堵。一年四季,整条巷子里都泛起异味。门没锁,一推开,我叫了一声“爸”,没人应。这样的天气,陈国荣应该在家。一居室的房子,一眼就能望到头,空气里泛着异样的气息。整间屋子整齐得过分。每只碗、每个盆、那张缺了一个角的桌子、那个摇摇欲坠的组合柜和随时都会掉下一片墙皮的旧墙,都静谧得不祥。
爸,我又叫了一声,还是没人回答。我拿了铁钳子出去给邹叔,问他是否见到陈国荣。他摇摇头说没有,停顿了一下又说:中午雨大的时候见他收了摊,打了声招呼。我转身回到屋里,厨房里的剩饭还没凉透,让我三两口就吞进了肚子里。白花花的雨不停地下,屋里越发的暗。我打开灯,想起来今天是我妈的生日。
十年前,我妈病死了。陈国荣卖了房子凑来的医药费,最后还是没能救回她的命。葬了她以后,陈国荣把我们所有的家当都捆在了一辆三轮车上。小子,以后就剩咱爷俩了。陈国荣的脸上带着一丝苦笑。他的眼睛因为哭了太久,暂时变成了双眼皮。他推着三轮车,我跟在他后面,一路来到了未名巷。那之后的第二年,陈国荣下了岗,他蒙起被子睡了一整天。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去旧货市场买了些便宜的折叠桌子和小凳子,在巷子口支起了一个小摊,卖起了油泼面。我一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跑到摊上帮忙。
陈国荣做面的手艺不错,我们俩的日子也还说得过去。曾经也有流氓地痞找过陈国荣的麻烦,后来都让他一一摆平了。他的左眉上有一道一寸的疤,是啤酒瓶子的碎片割伤的。那些来找事的人渐渐领教了陈国荣的脾气,明白了老实人急眼了,也是会动手的。再说陈国荣一米八二的个头,拚起命来气势也很足。
就这样过了十年。
家里没有陈国荣的影子,越来越大的不祥之感包围了我。其实从今天一大早我出门上学开始,我的心就慌地厉害,眼皮一直不停跳。我几乎从没逃过课,可是那天我撑到下午却还是编了个蹩脚的理由溜了出来。我忽然很想见到陈国荣。
最近这段时间,我听到流传在未名巷里一些关于他和一个女人的传闻。沉默寡言的陈国荣在这些绘声绘色的描述里,成了未名巷里的风流人物。这些闲言碎语让他很恼火。晚上面摊收摊前,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他低着头,没有看我,声音低沉地说:晓晓,有些事情,听到了就当做没有听到。爸是什么样的人,你是知道的。我说:爸你放心,我明白。
他其实大可不必在乎我的感受。十年了,他独自抚养着我,这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继子,他并不亏欠我什么。
邹叔、邹婶陪我找遍了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我还坐车去了一趟城外我妈的墓地,可都没有陈国荣的影子。
雨下了一夜,淋透了铁城的各个角落后,终于停了。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邹叔替我报了警。警察调查了一番后,也毫无结果。他们联系了街道上的人,给我送来了一些钱,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投靠的亲戚。房东也过来问我,下半年的房租我准备怎么办。
邹婶替我打发走了房东,望着我,忍不住叹着气说:早就应该看出来那就是个没安好心的狐狸精,要不然也不会勾引着你爸,连家都不要,就和她跑了。她说的那个女人我没见过,可凡是见过的人都说她长得很美。
陈国荣没有带走多少行李,只有几件他随身的衣物。大衣柜里还有他留给我的一千块钱,我知道那是他所有积蓄的一半。邹婶说那个女人是南方人,也许陈国荣跟着她一起去了南方。虽然对他的不告而别有些吃惊,但是我并不怨恨他。我想起陈国荣失踪前的那个月,他频繁地提起我的母亲。他提起那年深秋他第一次见到她,她那双惊慌失措的眼睛,还有躲在她身后四岁的我。他说起他第一次拉起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他干脆拉开自己的外套,把她的两只手都捂进自己的外套里。他说起他们那几年的好时光。后来,母亲的例假迟迟不来,他们都以为有了孩子,去医院一检查,却是子宫癌。
我从技校里退了学,开始学着自己过日子。除此之外,我的生活似乎依旧,我继续守着陈国荣留给我的面摊子卖面。秋天的时候,鸟都飞到了南方,我望着鸟群离开的方向,想象着陈国荣在温婉秀美的江南与自己的新妻子一起生活的样子。也许,明年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个真正的、继承了自己血脉的儿子。
面摊的生意不错,未名巷的街坊们都可怜我,我以前技校的同学哥儿们有空了,也来面摊帮我的忙。原来在技校里学美容美发的江玉蓉,毕业后自己在公园西门口摆了个剃头的摊子,后来,她把摊子移到了未名巷我的面摊附近。
过了有半年,我和江玉蓉开始谈对象。我们把所有的钱凑到了一起,然后盘下了一间小店,自己粉刷墙壁、简单装修后,玉蓉的剃头摊子移到了小店里,我的面摊就摆在店外面。每晚收了摊子后,家什就放进店铺里。
江玉蓉说:咱们都好好挣钱,再过几年,手头宽裕点的时候,咱们就去南方旅游结婚。江玉蓉知道我一直挺挂念陈国荣,想去南方找找他。她从小就没爸,后来妈又出了车祸。就像邹婶说的,我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几个月后,一对南方口音的警察出现在我家门口,他们说:你就是陈国荣的儿子?我说是的。他们说:我们在旗城一个河沟里发现了一些碎尸,是陈国荣。
2
羊红袖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人好,名字也好。红袖添香,听着就多情。人长得美,追求的人也多,她像只高傲的孔雀盘踞在高处,望着下面的枝桠,看来看去,好像哪一个都不值得栖落。
日子久了,不少人也就散了。等到媒人领来顾小敦的时候,她已经快到三十了。三十岁就是女人的一个坎。媒人说,别看顾小敦长得不俊,可工作好,人也老实可靠。姑娘大了要出门,要找找个实在人,过日子嘛,当然是要找个靠得住的才行。羊红袖抬眼看了一眼顾小敦,目光一接触,他就吓得赶紧把眼神收回。羊红袖在心里笑了一下,这事就这么成了。男人太好看了没有用,多年前她曾经迷上过一个小白脸,全心全意地对人家,可后来还是被骗了,钱被花了不少,孩子也刮了两次。
和顾小敦结婚后,他一直都对她很好。吃的、用的都是他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就连单位发工资的存折也交给她收着。她很快怀孕,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她生下了一个女儿。顾小敦心疼她,不想她受累,女儿一满月,就被顾小敦送回了乡下孩子的奶奶家。
两年后,羊红袖下了岗,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事做,她开始去街口的麻将馆。三毛五毛的无论输赢都无所谓,只是打发时间而已。顾小敦劝过她,说去那里的都不是正经人,说多了,羊红袖开始嫌他烦。麻将馆里一年四季生意都很好,有的时候羊红袖去晚了,就只能坐在一旁等位置。她搬了板凳坐在靠麻将馆大门的地方,小镇的天一直都是灰蒙蒙的,日子平淡得像看不见的云。她感到自己快要被这灰色吞噬。
一个男人从背后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回头,迎过来的是一张干净的男人的脸。男人说着好听的普通话,对她笑了一笑说:这里有位置,你快来啊!他的笑像束光,冲走了霾,还带着甜。羊红袖在那甘甜里微微发愣。他坐在羊红袖的旁边,耐心地等着她出牌。羊红袖的麻将打得并不好,牌出得慢了就有人催,不知不觉,一手好牌打烂,进退两难,骑虎难下了。而那个男人似乎看出了她的尴尬,不动声色地喂牌给她,每张牌都恰到好处。羊红袖心跳加速,却不敢看他的脸,可是他洗牌、摸牌的手白净修长,连骨节都是那么好看。
羊红袖尽量掩饰自己的心情,但她觉得,他一定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的。否则怎么每次他对她笑,似乎都暗藏着深意。
半年后的一天,羊红袖在他的身边醒来,看见熟睡中的他那稜角分明的脸,心里泛起丝丝惆怅,她在心底笑自己没出息。原来时过境迁了,自己却还是会对长得好看的男人动心。小镇不大,他们俩的事情传得很快。顾小敦气得摔东西,非得从她口中听到有或没有。见她没有否认,又生气地甩了她两个耳光。她摸摸左脸,又摸摸右脸,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眼泪已经砸下来了。
她收拾东西,说要回娘家。顾小敦过来拉她,她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就在手腕上划了一下。她说:你要是拦我,我就去死。顾小敦的心底还是在乎她的,嘴上硬着说:有本事,走了就再别回来。可过了几天,他还是提着鸡蛋、点心,去了趟羊红袖的娘家。
羊红袖的老爹死得早,家里只剩下个气息奄奄的老娘和一个一无是处的痴肥弟弟。羊红袖和顾小敦结婚后,也很少回娘家。小舅子斜着眼睛说:我姐没回来啊!你把我姐怎么了?
从岳母家出来,顾小敦垂头丧气地走在街上。他觉得自己真是蠢。他失魂落魄,觉得街上的人都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笑他当了乌龟,连自己老婆跑去了哪里都不知道。他打听过那个男人。听说是个闲人,下岗后也没有个正经工作,自己在外面做小生意。羊红袖怎么会看上这样的人?自己哪点比不上他?委屈涌上心头,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他决定不再找羊红袖了。如果她还有一丝一毫在乎他、在乎这个家,那她迟早会回来。
过了半个月,顾小敦接到了居委会的通知,羊红袖去法院诉请离婚。传票经她委托,由居委会转交给顾小敦。
3
尸块是被一个拾荒者发现的。臭水沟里一半脏水、一半垃圾,那东西被层层的塑料袋裹着,装进了一个旧的旅行包里。包顺着脏水缓缓漂移,鼓鼓囊囊的,看起来比水沟里的其他垃圾干净许多。那人找了根棍儿,费了半天的工夫,才把旅行包勾上来。一股臭气扑面而来,他以为是包在水沟里泡久了,染上了垃圾的味道。没想到打开包一看,里面是一只已经腐败的人脚。
警察来了以后,迅速封锁了现场,一组人下到水沟里,把臭水沟里的东西过筛子似的翻了个遍,又找到了一只胳膊、一个男人的上半身和一条腿。在一个包裹碎尸块的塑料袋里,还有一张被剪开、只剩一半的身份证。
水沟离小镇的火车站不远,这一片鱼龙混杂,很多自建房屋,街街巷巷的,每个犄角旮旯里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现在闹出了人命,警察开始住家住户地走访清点,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半个月后,果然在离水沟步行二十分钟的一家小旅馆里发现了问题。小旅馆其实是黑旅馆,姓冯的中年女人是老板娘,也是拉皮条的。她对着警察支支吾吾,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让人生疑。后来警察看她神色不对,吓唬她说要把她带回警局盘问,这下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说三个月前,一对外地口音的夫妻来店里投宿。一开始说住上几天就走,后来住了一个多月了,也没有要走的意思。两口子很少和外人接触,每天就是在屋里不出门。房间也不让人打扫。一天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出来一个人倒倒垃圾,再去街上买点吃的。她和伙计趴在门上偷听过,一开始是干那事的声音多,后来就是吵架。到了后来,她也就不再留意了,反正房钱他们一直交着,没有欠过。
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他们预付的房费只够再住三天的时候。老板娘敲门,问他们还住不住了。明明听见里面有动静,可就是敲了好久,才有人过来给开门。那女的就露了半张脸,然后面无表情地说,明天会再续交一个月的房费。还不等老板娘回话,就把门给关了。三天后,老板娘再去敲门,就没人应了。拿钥匙开门,竟也开不开。叫了伙计来,硬是给撞开了。原来里面用棍子把门给死死地顶上了。屋子里收拾得挺干净,床单什么的好像也都自己换了。
窗户开着,下面就是一条后街。房间在二楼,想必这两口子是跳窗走的。老板娘百思不得其解,不住就不住嘛,又没有欠房费,为什么要逃掉?她也没有多想,直到发现了厕所里有血。厕所的地和墙都被水冲过,墙上的血星星点点的很多,天花板上都是。她吓坏了,经营小旅馆这么多年,她也是见过世面的。她知道这血不是什么好兆头,再联想到这两口子吵架的样子,她觉得八成是出了人命了。但是死的那个是谁,她却是不知道的。
警察查了当时的住宿登记。来住店的时候,用的是那个男人的身份证,叫陈国荣,是北方人。警方把现场血迹和尸块一对比,果然是同一个人。在现场找到的那半张身份证,也和陈国荣的对上了。
两个警察去了陈国荣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找到了陈国荣的儿子陈晓晓。本来打算抽血比对,确定被害人身份的,可陈晓晓却说,自己不是陈国荣亲生的,只是继子。陈国荣也没有别的血亲,只有当年入厂工作的时候,体检报告上的血型记录。在小旅店里收集到的血迹和尸块上的血迹都是 A型,陈国荣的体检报告上显示,他的血型也是A型。
4
羊红袖有的时候会梦见童年时候的一条狗。那时她还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舅妈对她不好,趁舅舅不在的时候总是打她。外婆瘫在床上,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她自己坐在院子里,望着天,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那只土狗不知从哪里摇着尾巴跑来,在她面前坐下。它湿漉漉的眼睛望着她,彷彿洞察了一切,那些她无以言表的情绪它都了解。她把狗抱在怀里,心里好受了些。后来那条狗挣开她,跑走了。
她在外婆家的那几年,那条狗会时不时出现,静静地陪她一会,然后跑开。离开外婆家回到城里时,她唯一的不舍竟只是那条狗。她觉得不会再有谁会有那样的耐心,用那样的眼神静静地望着自己。
后来她遇到顾小敦,他的眼睛里浮现出让她安心的一些东西。她也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可每次见到,都会感觉自己是在别人温柔的爱意里。那东西时有时无,后来也慢慢地消失了。顾小敦第一次动手打她时,他的眼神第一次看起来像是一个陌生人。她收拾了东西,搬去了那个男人的地方,她告诉他,自己要和顾小敦离婚。他吻着她,说好,只要和你在一起,那什么都是好的。她想起当年自己和顾小敦结婚,是为了安稳。可她要的不是安稳,安稳不代表幸福,安稳就仅仅是安稳而已。
她知道顾小敦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开她,协议离婚是行不通的。法院传票送到顾小敦那里的第三天,她等不及了,她要去找顾小敦,问问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同她离婚。
出门前,她想起了顾小敦的耳光,心里有些怕。可抱着她的男人说,快刀斩乱麻,越拖越不好办。他拿起桌上的水果刀递给她说:拿着这个,防身用。后来顾小敦是怎么倒下去的,她没敢看。她只记得顾小敦一见到她,就冲了过来,她想跑开,他追她,后来终于在门口的小街上拉扯住了她。
她缩着脑袋,不敢看他。他又急又气,打了她几个嘴巴,骂她不要脸,骂她是淫妇,骂那个男人是奸夫。他的眼睛红得像血,激得羊红袖也愤慨了起来,她记起了兜里的那把刀。顾小敦死于失血性休克,见惯了血光之灾的警察说,这娘们心够狠的,一刀就刺穿了心脏。
羊红袖失魂落魄地跑回去,见了他就哭。他见到她身上和手上的血,终于知道大事不妙。他问她刀呢,她茫然抬起头,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给了她一巴掌,她终于哭着说,扔了,扔到哪儿记不清了。男人让她快点收拾东西,再不快点跑,等警察来抓了他们,她就得挨枪子。他们俩一刻也不敢耽误,上了南下的第一趟火车。她跟着他,换了好几次火车,她发了烧,把头缩进他的怀里。
光怪陆离的梦里,那条狗又出现了,它湿漉漉的眼睛望着她,看得越久,那眼神就越像顾小敦的,后来又变成了那天她第一次在麻将馆见他时他的笑。狗起身要走,她正要喊,却被人摇醒。到了。他说。
这是哪儿?她问他。她向窗外望去,可是外面漆黑一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已经足够远了,他们一定找不到我们的。他在她耳边小声地说。
他们俩从火车上下来,已经是夜里。逃了好几天了,羊红袖还没有睡过一次完整的觉。他们在乱如迷宫的小街上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一家旅店。老板娘打着呵欠给他们拿钥匙,又让他在一个本子上,写下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羊红袖看见他在本上写了一个名字:陈国荣。
5
陈国荣的户口销了。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全,我只好把能找到的部分火化,并与我妈合葬。邹叔、邹婶和玉蓉陪我一起去给他们烧了些纸钱。回来的路上,暴雨将至,乌云低低地直逼下来,我坐在公交车靠窗的位置上咬着拳头,悄无声息地哭了。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警察局打听一下案子的进展,可那个女人一直没抓到。办案的警察总是说,一有消息就会跟我联系。可负责案子的警察换了好几拨,我却始终没有等来我希望的消息。警察说调查得越多,谜团就越大。他们从北到南追了几千里,却连那个女人真实的姓名都没有查到。他们手上仅有的线索,只有一张根据北方和南方两边见过她的证人的描述而得出的模拟画像。那张画像在未名巷附近张贴过,邹婶看了却觉得不太像。她说,这女人果然是狐狸精,有千种面孔。江玉蓉劝我想开点,她说,这样的妖孽,自有天收。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我明白,陈国荣的案子是彻底的凉了。我和玉蓉结了婚,第二年她就生了个儿子。我的面摊变成了小吃店,玉蓉暂时关了理发店。她在月子里落下了病,吃了很多中药,也总是不见好。
我说:要不然咱们找个保母带孩子,你也松快些。玉蓉嗔怪地说:你真当自己是大老板了?她说,保姆倒是用不着了,每个礼拜能有谁帮我看两天孩子,让我去店里给你帮帮忙就成了,我在家实在是闷得慌。
邹叔、邹婶去了儿子家里,帮忙带一对双胞胎孙女,身边也一时没有可靠的人。有一天玉蓉说,街口的澡堂子里新来了一个黄大娘,人实在,干活也麻利。玉蓉每次去洗澡,都找她搓背。她话不多,人总是笑咪咪的。玉蓉问过她怎么会来铁城,她说自己命苦,是个寡妇。父母也都不在了,也没有子女,只能自己浪迹天涯,过一天算一天。她苦笑着说:我就是命硬,让我帮你看孩子,你不怕啊?玉蓉说:我不信这个。上次正好听说你礼拜一和礼拜二休息,想要到外头再找个活干。你如果愿意,每个礼拜来家里,帮我看两天孩子。
黄大娘同意了。自从来到铁城,她总是闲不下来。吃住都在澡堂里,一睁眼就是干活。老板很喜欢她,如果不是怕她累坏了身子生了病,那真是恨不得她每天都来澡堂子里干活。每个星期黄大娘帮忙带孩子的那两天,玉蓉就来小吃店里帮忙。忙忙碌碌的烟火气倒是让玉蓉的精神好了很多,气色也红润了不少。
有一天,店里忙得不行,玉蓉帮着收拾碗筷、擦桌子的时候,突然望着店外惊叫了起来。她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指着马路对面一个倒在地上的老乞丐。
我说:玉蓉,你怎么了?
她转过头惊恐地望着我说:晓晓,你快看,那个人,是不是你爸?
我吓了一跳,心想怎么可能,可是果然是越看越像。我出了店门、过了马路,走到那脏老汉的身边,把他扶起来一看,心里“格登”一下,果真是陈国荣。我撸起他的袖子,左胳膊上的胎记不会有错。我叫他:爸,是我,我是陈晓晓。他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我通知了派出所,又赶紧找车把他送进了医院。大夫说他应该是在外面受了不少的苦,营养不良以外,神志也不是很正常了。他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然后我和玉蓉把他接回了家。我跑街道上派出所,又找了以前陈国荣单位的领导,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已经销了的户口给重新上了上去。
家里一下子添了好多事,玉蓉找到黄大娘,问她愿不愿意把澡堂的工作辞了,专门来家里看孩子,顺便照顾陈国荣,我们付双倍的工钱。黄大娘考虑了几天,同意了。玉蓉觉得,她能同意主要还是因为孩子,黄大娘对宝宝很好。虽然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过孩子,但是带起孩子来却还是得心应手。玉蓉每周有一半的时间在家里帮黄大娘的忙,剩下的一半时间就去店里帮我。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扩大了店面,又招了几个伙计。
孩子三岁的时候,玉蓉提议,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康复医院的大夫也总说,出去散心对陈国荣的精神恢复很有好处。我们给黄大娘放了假,一家四口坐上了绿皮火车。火车轰隆隆地由北向南,窗外风景也越变越美。火车经过一片油菜花地的时候,陈国荣突然开了口。他说:那一年,我们两个也是坐这种火车走的。
这几年偶尔他神志清醒的时候,会跟我说说他消失以后的事情。他说他在南方过得不好,别人欺负他是外地人。陪他一起私奔的女人后来和一个小老板跑了,临走还卷了他所有的钱。他为了攒够回来的路费,只能去工地上打工。
后来在工地上出了事故,人被撞了,头受了伤,包工头给了他一点药费就打发了他。他最后流落到收容所里,睡大通铺的时候,还被老流氓摸过。后来他从收容所里跑出来,又一下子记不清具体的地址,一路跌跌撞撞总算摸回了家乡。
玉蓉说:爸,后来呢?你们坐上这种火车,然后呢?自从陈国荣回来,我和玉蓉心里都有疑问,可是我们心照不宣地都没说出口。陈国荣回来了,那埋在墓里的那个人,是谁?
陈国荣看着窗外,他的眼睛象是在白色的迷雾里探索出路一样,过了好半天才说,他当初也不知怎么着了魔,迷上了那种女人,信了她的话,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可以握在手里的幸福的机会。所以他像个傻小子一样,不顾一切地就跟她跑了。可是他们一出门就开始吵,因为他告诉她,自己还给儿子留了一千块钱。火车开开停停,旅程长得似乎永无尽头。他记得他们对面坐了一对夫妻,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两个人都是神色严峻。
后来下了火车,陈国荣才发现,他的钱包丢了,虽然也把钱藏在了别的地方,但是身份证却没有了。因为这个,两个人又大吵了一架。
我和玉蓉都不说话,沉默地听着。陈国荣说:我似乎这辈子都只是在寻找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不再吃苦。他笑着伸出手,摸摸宝宝的头发,我现在就是最幸福的人了。我望着他。这是陈国荣这么多年来说过的,最长的、最动听的话。
6
黄大娘坐在澡堂里,等着给人搓背。虽然辞了工,可澡堂老板喜欢她,让她什么时候有空,就回来干上一天两天的。梁家人出去旅游去了,说是让她好好歇歇,可她怎么歇得住?
她是最怕歇的。最近那个梦又来缠她了。夜里睡不好,白天干活也没精神。梦里,是那年的麻将馆,她坐在门口的板凳上等位置,有人从后面拍她。
那人说:这里有位置,你快来啊!
那人还冲着她笑。她这辈子还没有见过,笑起来比他更好看的男人。
那个瞬间被拉得像部电影那么长,阴魂不散地尾随着她。在她心不在焉的时候、在她等着给下位客人搓背的空档里,都会像个贼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然后将她击垮。她一直不想再回忆过去,不想再想起那个男人。旅店里,他们不停地做爱,也不停地争吵,却总是寻不到出路。带出来的钱一天天用完,她连自己贴身保命的金首饰都卖了,可那男人却一点也没有想要出去找活干的意思。
她跟他闹,说:你说过你会养我的。
那男人说:怎么,你后悔了?后悔了咱们就回去。反正杀顾小敦的那把刀上也只有你的指纹,跟我没关系。她望着他,他看她的眼神太陌生了。那条小狗又不见了。
那天晚上,她等他睡着,她亲他,他厌烦地推开她,转了身又睡过去了。她终于在他的背后举起了刀。这次,没人递刀给她。
给梁家看孩子的第一天,她开始不再做噩梦,她觉得这都是孩子带给她的好运气。孩子嫩嫩的小手摸着她起皱的脸,像是把一切伤口都抚平了似的。她本来没打算在铁城长住,可现在,为了这孩子,她打算留下来了。
她抱着孩子,站在阳光下。孩子望着她,说:黄奶奶,你怎么哭了?
她说:奶奶这是高兴。人要是高兴了,也是会哭的。
孩子似懂非懂。她抱紧孩子,她想,一切都会好的。毕竟这世界上有两种药是包治百病的,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