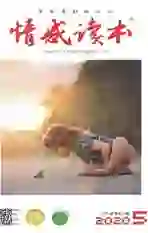我爹
2020-08-06兰若水
兰若水


回深圳的第一晚,清晨半梦半醒之际,我看见我爹,在老家的屋门口。他笑意满满叫我的名字,我答应他。他便朝门外走了。
少儿时的我爹,好惨的
我爹的故事一直跟随着我的脚步。学龄前是我家族里的人讲,上小学时是镇子上的人讲,上中学是县城里的人讲;上大学,是他自己跟我通信讲;等到我们姐弟几个都成家立业后,是我妈在电话里讲。
少儿时的我爹,好惨的。
他五岁丧母,丧母当年,他疼爱的小妹妹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我爷爷和我大伯——比我爹大三岁的大伯是我爹的死对头,他极聪明又极心狠,将自己所干的一切坏事都栽赃到我爹身上。而每天忙着在外面做砌匠活计、披星戴月赶路的我爷爷,也不会追问究竟,只会用一根粗木棒子,朝着床上睡得正香的我爹狠狠揍下去……
我爹六岁时,他有了个继母。这继母自己不能生孩子,迅速和被嫌弃的我爹组了团。但这个团队的武力值和经济值都比我爷爷和大伯的团队差太多,我爹依然是被坑被粗木棒狠揍的那个。我奶奶弱小的力量,是在他三更半夜被揍时抱住他挡两回,在他被揍后,抱住他伤心流泪,为他抚摸伤处。
大伯14岁就担任了村里的会计,16岁调到乡里做临时工,18岁病逝。
他骨头一直一直烂,怎么治都不好。死前一天,他想要喝鲫鱼汤。那是物质极困难的年代,我奶奶卖掉了她陪嫁的一只床头柜,才买到三条鲫鱼,炖成汤,端到大伯床头柜上。
大伯很镇定地喝着,完全无视他继母和弟弟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喝了小半碗,他喝不下了。看着还有一大碗鱼汤呢,他猝不及防地将那一大碗鱼汤一推,碗掉到地上,鱼汤倒在地上,迅速渗进泥地里……
他狰狞地笑,“就算倒掉,也不给你们两个人喝!”奶奶至死记得那一幕。要知道,我爷爷每天外出挣钱,照顾他的就是奶奶和我爹。
大伯去世后,我爹就不那么惨了。我爷爷意识到他只有这么一个赖儿子,下不去手了。可那个时候,我爹已经15岁,半大小子了。
我们会靠得住的
其实我爹只在我爷爷眼里赖。但真实的我爹,除了脾气大点、性格直点,相比他同年龄同环境的人,我爹还是蛮出色的。
我爹读书不错,他上完中学后,考上了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没做几天,他又到我爷爷手下学做砌匠。之后,他又經历了不少职业及许多跌宕起伏。
我念初中时,我爹已经领着他的建筑队广东广西湖南到处跑。那些年,我家的日子很不错。十几岁的我便有呢子大衣可穿,有电子表可戴,有很漂亮的女式单车可骑,可以自己去县城里挑喜欢的皮鞋款式。
但作为我爹最大的孩子的我,对这些并不敏感。我骄傲的是,我是我爹的女儿。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人都会指点我说,看,那就是谁谁的孩子,龙生龙呢。谁谁正是我爹的名字。
不过,在这一切的最初,是我爹和我爷爷无数次的对抗。他不干民办教师、不肯跟爷爷认真在周边做砌匠,而是自己拉起了一支建筑队;拉起建筑队后,又不老实做本县的工程,而是跑到广西广东去找工程。我们家和爷爷奶奶分家、断绝关系,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爷爷希望我爹做一个踏踏实实、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但我爹却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不断去尝试的孩子。
断绝关系当然是父子俩争吵最厉害时的气怒之言。但我初一开学时,正好家里的钱都用在一个新工程上,爹便向爷爷奶奶借我的学费,说明两月后还,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
我爹痛哭一场,还是凭着他同学是校务主任的关系,延迟了我的学费缴交期限。
他是躲起来哭的。无奈他哭起来比较忘我,我们家里人都听见了。哭完,他红着眼晴跟我说:“闺女,这世界上除了自己,没人真正靠得住,哪怕父母。”
我说:“爸你很靠得住呀,以后你老了,你靠我们,我们一定靠得住。”他看着我,看着同样担心他的我弟妹,拍了拍我弟弟的光头,笑了,“好,爸老了要靠你们哈。”
我爹就是个孩子
我爹不管教我们。饭桌上,他和我们嘻嘻哈哈,说说笑笑。这与我爷爷恰好相反。爷爷很注重细节上的管教,吃饭是铁定的食不言,筷子怎么拿、菜怎么夹,都有要求。
爹也完全不懂得帮我们规划人生。我弟我妹上初二时成绩下滑厉害,考高中明显无望,他们便跟村里其他孩子一样打算不读书了。
我爹说:“不读就不读了吧。”
我那时在读高中,和我同样在读高中的堂姑姑细细打算:我妹才13岁呢,也不见得是成绩非常不好,留个级就好;我弟15岁,但他英语老是得几分,实在不读也行。
我爸和两个上初中的小孩用一模一样的懵懂表情,听从了我与姑姑的建议。几年后,我妹高考上了一本线,而我弟则成了一个修理师傅,全村人家中有东西坏了都找他。
我高考失利,嫌复读辛苦而读自费大专,他一丝犹豫也没有,压根没想过那笔对农村家庭来说相当贵的学费。那时他厌了包工程,转做建材生意,结果我三年的学杂费全靠着我妈和我已经停学的弟弟,一个柑子一个柑子地从树下摘下来,再挑到县城里卖出来的钱支撑。
1990年代的种植村,我们那里每户人家的存款都超万元,除了我家。我爹的生意越来越差,我家的钱,除了给两个女孩上学,还要填他做生意的坑。
他在家时,有一次,遇上一对从东北来收桔子的父女。收完一大车桔子后,父女俩却没钱回东北了,借遍全村都借不到钱。我爹当时恰好有那么一点钱,他用一句话让我们一家人都同意了把钱借出去:“做生意,出门在外都不容易的。我也得过人家的好处。”
后来,那父女俩真的没还钱。不过我们全家人谁也没在意那笔“巨款”。1000多元,在1990 年代的农村,确实是巨款。
过分善良的人,或许真的不合适做生意吧。
老头儿各种索爱
糖尿病找上我爹的时候,他五十几岁。我妈已经称我爹为老头儿。老家得这种病的人不少,大家都不把它当回事。那时候他时不时还外出做施工员,收入还不错。
有了钱,就大包小包地往家里买东西,给我妈和他自己买衣服,给家里买电器,买摩托车,还大手大脚地打牌。
我们三姐弟每次打电话回去,都千叮万嘱地,让他注意饮食。我爹豪气干云,“不能吃喜欢的东西,不如早死掉?”气得我们不行。
没几年,老头儿的身体迅速衰败下来。包工程的老板们不敢请他了,问题也来了,他开始向我妈伸手要钱。我妈这回却不同意了,每次,我爹要去干什么,要先报备才能领到钱。当然,钱给得还是比较宽松,比如他要100元,她会给他150元。
但还是不够。于是,我们每年回家的团聚日,必定要处理这样一件事:我爹要求和我妈分开过。理由是,她老是不给他钱用。
我们三个过得都一般,所以我爹倒也自知,第一回,他要求每月给他300元。那是2009年,300元一个月啥也不够呀!我妈豪气,“你也不用说分开了,我就每个月给你300元打牌,你吃住穿抽烟摩托车加油买药都由我负担。”
不到半年,我爹再次要求和我妈分开。我们也懂得了他的套路,就是要加钱。他大约也知道这要求太过,也不说加钱,只说要分开,让我们给他一个月的全部开支1000元。
我们被吵得眼前发黑,当场就同意了。给他一个月1500元,让他管理自己的生活,我妈跟我们到城里生活。
三个月后,老头儿打电话来,说他生病了。我送我妈回去,推开门,以为来到了一个大型垃圾场:楼上楼下共六间屋子,全是东西:没有被套的棉内胎、衣服、含糖饮料的瓶子……老头儿瘦了一大圈,躺在一堆垃圾中,呻吟得很大声。
送他去医院一查,血糖高得吓人。住院,降糖。出院回家,我妈已经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老头儿看到老伴也高兴,两人在灶边柔声说话。虽然家常,却温情满满。
然而那年过年我们回家,老头儿又要求分开。我气急败坏,大声问他:“你到底要啥?”是呀,这么闹腾的背后,应该有别的原因。他别开脸,不回答我。
我妈倒是有点醒悟,“要不,你以后多给你爹打电话,多聊聊天。”
没办法,三个孩子中就我一个人话多点,其余两个都是闷葫芦。之后,我打电话回家总是打到我爹手机上,跟他瞎扯淡。慢慢的,倒也不太闹腾了。
时至今日,我回忆起这些事,忽然明白,老头折腾来折腾去,是想要清清楚楚地接收到我们对他的关心和爱。
也算是被温柔待过
一晃又是十几年,老头儿六十好几了。他依然不注重饮食,当着我妈一套,背着我妈立刻大嚼升糖迅速的食物。2018 年正月初六晚,我爹急病。原来是过年前他偷偷地买了两包汤圆,藏到冰箱的底层,等初六我妈出去走亲戚时,他在家煮了一大包做早餐,又煮了一大包做晚餐。
当天晚上,他非常不舒服,送进医院,立刻降糖。血糖降了下来,可是他的胸闷情形却没有半点好转。我坐高鐵赶回去,下车直接去县人民医院。他躺在病床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脸色苍白,胡子拉碴的。
我们拉着手,相互对望,两个人的眼泪都哗哗地往下掉。我将他的手在掌心里拢着:“我爹受苦了。”他说:“女儿呀,你回来了呀,我前胸后胸都好闷好闷。”
我放下他的手,将双手放到他前胸后背,反复地抚摸。他的呻吟声渐渐小了,然后求我,他不住院了,一定不住了,回家去。
医生将我叫过去通知了我爹的情况:有心梗、脑梗,再加上疑似肺癌。治心梗需要转院去上级医院,下一步是心脏搭桥。但是,就算做了心脏搭桥,他的肺癌也已到中期,撑不了一两年。
我和我弟陪我爹去了长沙的医院。从前我们不开心了会大声怂他,但那段日子,我们耐心超级好。他偷吃肥肉,我会跟他开玩笑:“吃一块哈。”夹走他碗里的另一块。医院里人山人海,我们去看病,做各种检查,去结账取药,每一次都被挤得不能呼吸。
因为住不了院,他便安安静静地坐在医院花坛的大理石上,看着我和我弟汗如雨下奔来走去。他盼着我们的眼神,就像婴儿看到母亲。
长沙相熟的医生建议我们不用再做更深的检查了,断定是肺癌中晚期,回家去好好陪他吧。我们决定,我弟留下来照顾他,我和我妹回各自的家。
回深圳的第一晚,清晨半梦半醒之际,我看见我爹,在老家的屋门口。他笑意满满叫我的名字,我答应他。他便朝门外走了。
我猛然醒来,心慌不已。打电话给我弟,我弟只说他又睡得不好,胸闷得厉害。
第二天上午,电话响起,我弟哭着说:“爹走了。”
“爹走了!”三个字,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心撕裂般的巨痛。
我写了无数文字,写失恋时的心疼,写失去亲人时的悲伤。但这是第一次,我真正感受到了心痛。
爹走了快两年后,我再来仔细回忆他的一切,依然会掉泪,却也有欣慰:我爹,被嫌弃过被怀疑过被伤害过,也被爱被信任被温柔待过;暗淡过也闪耀过;温暖过别人也被人温暖过。我爹这一趟人间,值得。
杨益庆摘自《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