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奎律髓》中诗论主张与选诗实际之间的错位
2020-08-04曾雪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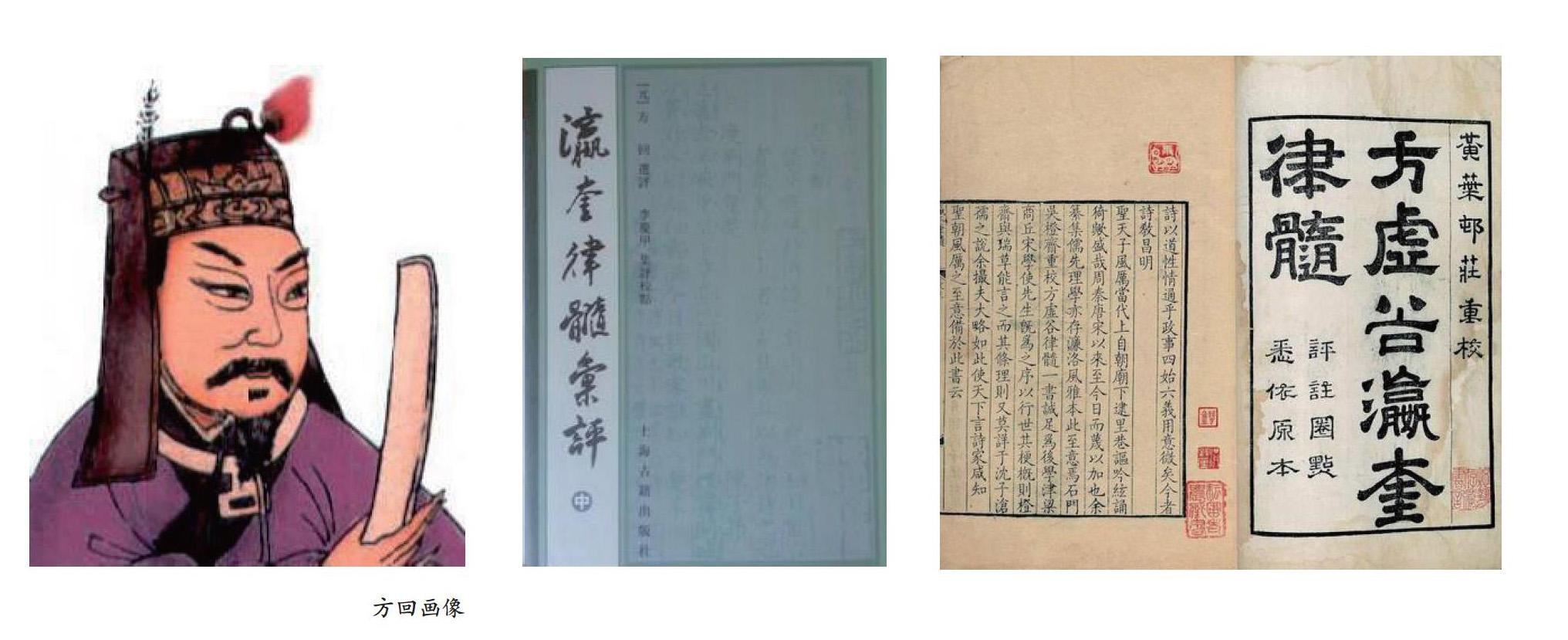

摘 要: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体现出尊盛唐而抑晚唐的强烈倾向,但在实际选诗时他却选取晚唐诗篇多过盛唐诗篇,使得《瀛奎律髓》中的诗论主张与选诗实际之间发生错位。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在于韩、吴融、杜牧等一部分晚唐人的诗歌自为翘楚,“不全似晚唐”;二是在于晚唐诗虽格卑却不乏佳句,方回常常因句存诗;三是在于方回将杜甫尊为“律诗之祖”,而由晚唐姚合、贾岛等人入手来学习杜甫是一条切实的学杜门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回秉承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选诗观,既看到了晚唐诗“格卑”的一面,也看到了晚唐诗有“细润”“工整”等可取之处。同时,他希望能以晚唐之“细润”济江西之“粗抹”,从而达到纠正江西缺失、重振江西旗鼓的目的。
关键词:《瀛奎律髓》;诗论主张;选诗实际;错位原因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体现出尊盛唐而抑晚唐的强烈倾向已是学界公论。评点盛唐诗歌时,方回总是极尽溢美之词,高扬盛唐诗之“格高语壮”[1]529、诗意“浑成”[1]1303。而对于晚唐诗歌,方回则往往痛批其“意思浅”“器局小”[1]364“诗格颇卑”[1]1660。一褒一贬中,方回尊盛唐而抑晚唐的诗论主张似乎已不言自明。但若细究《瀛奎律髓》中的实际选诗数量,我们却会发现一个与此相悖的事实。《瀛奎律髓》中共选1287首唐代律诗(重出12首),其中盛唐诗324首,晚唐诗488首①。从这一数据来看,晚唐诗入选篇数明显多于盛唐诗。这一情况与上文中所提到的方回的诗论主张并不相符。那么造成《瀛奎律髓》中诗论主张与选诗实际之间这一错位的原因究竟为何呢?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方回“晚唐诗歌观”。
一、诗论主张——尊盛唐而抑晚唐
首先要注意的是,《瀛奎律髓》中初唐的概念并不清晰。全书中“唐初”仅出现1次,“盛唐”出现17次,“中唐”出现5次,“晚唐”出现93次[2]。方回论诗时往往将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期等初唐诗人一并列入盛唐。如开篇首卷评陈子昂的《度荆门望楚》时方回说到:“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期,俱同时而皆精于律诗。孟浩然、李白、王维、贾至、高适、岑参与杜甫同时而律诗不出则已,出则亦足以杜甫相上下。唐诗一时之盛,有如此十一人,伟哉!”[1]1
身处乱世、身为二臣,方回对“十八学士登瀛州”的盛唐文治极为向往。在《瀛奎律髓》中,他不仅将杜甫尊为“律诗之祖”,对盛唐时期的其他诗人也都是赞誉有加、推崇备至。方回曾以洋溢的笔调表达自己对盛唐的追慕之情:“然则开元、天宝盛时,当陈、宋、杜、沈律诗,王、杨、卢、骆诸文人之后,有王摩诘、孟浩然、李太白、杜子美及岑参、高适之徒,并鸣于时。韦应物、刘长卿、严维、秦系亦并世,而不见李、杜相倡和。诗人至此,可谓盛矣。”[1]500方回之所以推崇盛唐律诗,首先是由于其“格高”。“格高”来源于诗人自身高洁的品格和深厚的学养以及作诗时所使用的“拗字”“变体”等手法,反映在诗歌中是一种“恢张悲壮”“苍劲瘦硬”的美学风格。方回认为盛唐律诗就是“格高”的典范,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杜甫的诗歌。《瀛奎律髓》卷二十三中评杜甫《狂夫》一诗:“然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1]992卷十三中又评杜甫《野望》:“此格律高耸,意气悲壮,唐人无能及之者。”[1]490除“格高”外,方回还一再标举盛唐诗歌之“浑成”。他在评陈子昂的《和陆明甫赠将军重出塞》及《送魏大从军》等诗中皆表示“盛唐诗浑成”[1]1303“唐之方盛,律诗皆务浑成”[1]1019。所谓“浑成”,如查洪德先生言:一是指诗歌浑若天成,无斧凿痕;二是指诗风的浑厚[3]。在方回看来,“浑成”是一种理想的美学风格,后辈学诗就应当将以盛唐诗为榜样,努力达到“浑成”的境界。
方回常常将盛唐与晚唐放在一起对比,从而表达对晚唐诗歌的批评。在他看来,与盛唐诗的“格高”“浑成”相对,晚唐诗显得“格卑”,透着一股小家子气。在评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时,他就指出:“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果,所以异也。学者详之。”[1]529评岑参《晚发五溪》时认为:“诗律往往健整平实,非晚唐纤碎可望。”[1]1392“格卑”一是由于诗歌在形式上刻意求工、对偶太切。方回多次指出许浑诗就是“太工”以致“格卑”。“丁卯詩格颇卑,句太偶。”[1]1660“所以高于许浑者,无他,浑太工而贪对偶,刘却自然顿挫耳。”[1]114方回认为,作诗时若不从诗歌的整体意境着笔,而是太注重格律的工整,“得一句即撰一句对”[1]111便会导致“诗歌前后不连贯,结构不浑圆。这就造成了诗歌气弱,给人以作者不是一气呵成,而读者不能一气读之,断断续续的感觉,所以气格就卑弱了。”[4]这与方回所倡导的“浑成”也是相悖的。“格卑”二是因为诗歌内容酸楚凑砌、意蕴贫乏。方回认为晚唐诗“只眼前事,自是凑合”[1]963“又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几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1]340在方回看来,晚唐诗人只关注自己的“小我”世界,诗歌意象都来自于眼前,写景时也不讲求寄托,纯粹是景物的堆砌而已,全不似盛唐诗歌,驰骋于宇宙天地之间,洋溢着悲悯的家国情怀。如同样是流泪,李商隐的《泪》:“永巷长夜怨罗绮,离情终日思风波。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全诗以堆砌典故来自伤身世,表达自己作为青袍寒士送迎达官贵人时的屈辱卑楚。而杜甫风烛残年之时登上岳阳楼“凭轩涕泗流”,不仅是哭自己的孤苦飘零,更是哭国家支离破碎,哭百姓流离失所。
总而言之,从《瀛奎律髓》的诗歌评点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方回极推崇“格高”“浑成”之盛唐律诗,认为晚唐诗则“皆晚辈之所不当学”,不然便是立志不高、从师不真,诗歌无法传世矣。
二、选诗实际——晚唐诗多于盛唐诗
虽然方回高扬盛唐旗帜而罢黜晚唐,但《瀛奎律髓》中实际入选的晚唐诗却多于盛唐诗。从整体上看,《瀛奎律髓》共选唐代律诗1287首(重出12首),其中盛唐诗324首,晚唐诗488首。晚唐诗比盛唐诗足多出164首。而且正如查洪德先生在《唐诗选本经典性及其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在这324首盛唐诗中,杜甫一人就选入221首(其中重出4首),除杜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共入选诗歌仅103首[5]143。由此可见,在入选数量上,盛唐诗与晚唐诗可谓相差悬殊。
此外,将《瀛奎律髓》中盛唐与晚唐两个时期里入选诗歌二十首以上的诗人进行统计并排列名次,可得下表:
由上表可见,盛唐与晚唐两个时期中入选诗歌二十首以上的共八人,其中盛唐三人,占比37.5%;晚唐五人,占比62.5%,幾乎为盛唐的两倍。从名次排列上看,杜甫独占鳌头,但随后的第二、三、四名均为晚唐诗人。更让人惊讶的是,方回所着力批判的姚合竟入选诗歌高达42首,胜过除杜甫以外的任何一位盛唐诗人。
对以上数据分析表明,晚唐律诗在《瀛奎律髓》中所占分量不仅不轻,甚至还要重过盛唐。这一情况与方回尊盛唐抑晚唐的诗论主张并不相符。《瀛奎律髓》中的诗论主张与选诗实际之间出现了错位。
三、错位原因——
方回“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选诗态度
《瀛奎律髓》之所以选入这么多晚唐诗歌,原因有二:一是并非所有的晚唐诗人都有“格卑”之通病。韩、吴融、杜牧等一部分晚唐诗人其实极得方回称颂。二是方回秉承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1]520的中肯态度进行选诗,看到了“格卑”的晚唐律诗亦有其可取之处。后者是造成错位的主要原因。
(一)韩、吴融、杜牧等人自为翘楚,不全似晚唐
方回曾评韩诗《幽窗》:“致尧笔端甚高。唐之将亡,与吴融律诗皆不全似晚唐。善用事,极忠愤。”[1]279这说明,在他心中韩与吴融是不同于其他晚唐诗人的。韩与吴融的诗歌皆沉郁顿挫、端重有体。方回曾多次在诗论中表达对这二位诗人的欣赏,认为“吴融、韩在晚唐之晚,乃颇参老杜”。在吴融的诗后,方回还屡次以“妙”“绝妙”“高矣”等字眼对其进行评价。这在他对其他晚唐诗人的评论中是比较少见的。最让方回赞赏的是吴融、韩“慨叹兵戈之间,诗律精切,皆善用事”。方回曾从江西诗派的诗论主张入手,批评晚唐诗不主用事以致诗意浅露。而韩与吴融二人却能做到用典工切,纪事与述怀相结合,使诗歌隽永有味。这无疑是符合方回的审美趣味的。除韩、吴融外,杜牧也是方回着力赞赏的晚唐诗人。在《长安杂题》后方回曾评杜牧曰:“盖颇能用老杜句律,自为翘楚,不卑卑于晚唐之酸楚凑砌也。”[1]192在方回看来,韩、吴融、杜牧等人自为翘楚,不全似晚唐,其诗歌自然是要选入的。
(二)晚唐诗“格卑”却不乏佳句
方回注意到,晚唐诗讲究“炼字”和“苦吟”,因此其诗虽整体“格卑”,却不乏佳句。早有学者指出,方回选诗时有“因句存诗”的情况。在《瀛奎律髓》中因某一联、某一句甚佳而被选入的晚唐诗歌比比皆是。方回评姚合诗《送李侍御过夏州》曰:“此诗以‘虏近少闲兵能道边塞间难道之景,故取之。”[1]1054评姚合诗《山中寄友生》亦曰:“五、六好。比贾岛斤两轻,一不逮;对偶切,二不逮;意思浅,三不逮。”[1]962可以看到,方回对《山中寄友生》全诗基本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仍因五、六句好而选此诗,其“因句存诗”的选诗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如“三、四句佳”“第四句好”这样的评语在方回对晚唐诗的评点中更是随处可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晚唐诗歌中的佳句源自于晚唐诗人们所倡导的“炼字”“苦吟”。而这种好“炼字”、重“苦吟”的诗法恰好也是方回所提倡的。他在《瀛奎律髓》第三十六卷论诗类开卷即选杜荀鹤《苦吟》一诗,并认为诗人之诗若不能传世,必是由其“用心不苦也”。贾岛是晚唐诗人中“炼字”“苦吟”的代表,其“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已成为“炼字”的典范之作。方回极推崇贾岛这种“争精微于一字”的作诗态度,赞曰:“学者必如此用力,何止‘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耶?”
(三)自晚唐贾岛、姚合入可至老杜
方回编选《瀛奎律髓》的原因之一是接引后学。在《瀛奎律髓·序》中方回自言:“所选,诗格也。所著,诗话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方回希望通过《瀛奎律髓》树立一个诗学典范,供后辈学人学习借鉴。这个诗学典范就是杜甫。杜甫是唐代律诗的集大成者,被方回尊为“律诗之祖”,其诗沉郁顿挫,形式上工于格律却又能为“变体”,不拘诗法;内容上能心怀天下、关注民间疾苦,而不是仅仅囿于自身遭遇。“格高语壮”“诗体浑成”的杜诗自然是学习的典范,但正如陈亚飞所言:“学杜诗如果直截了当地去学,常常会仰之弥高、望之弥远,入不了法门,不知从何下手。”因此,方回“指出了切实的学杜门径,后世学诗者通过阶梯式的学习,亦能达到学杜的目的”[6]。从贾岛、姚合入便是其中一条门径。方回首先指出了贾岛对杜甫的继承关系。他多次在诗评中认为贾岛诗与杜甫诗有相似之处。如卷二十三评贾岛诗《马戴居华山因寄》第五、六句曰:“一句上本下,一句下本上。诗家不可无此互体。工部诗‘林疏黄叶坠,野静白鸥来亦似。”[1]946卷二十六又评贾岛诗《寄宋州田中丞》曰:“‘相思深夜后,未答去年书。初看甚淡,细看十字一串,不吃力而有味。浪仙善用此体……老杜有此句法,‘每语见许文章伯之类是也。‘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亦是也。”[1]1133在评《病蝉》时方回更是直接点出了这种继承关系:“贾浪仙得老杜之瘦劲而用意苦矣。”[1]1157在诗风上,贾岛善用“拗字”,以艰涩之语状离奇之景,于有限的景物中蕴含无限幽思,继承了杜甫的“瘦劲”与“幽微”;在诗法上,贾岛与杜甫一样讲究苦吟。杜甫自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亦有诗曰:“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其次,方回又指出了姚合对贾岛的继承关系,认为“姚合学贾岛为诗”[1]399。评许浑诗《春日题韦曲野老邨舍》时明确指出:“晚唐诸人,贾岛别开一派,姚合继之。”[1]338由此,方回便构造了自姚合至贾岛再至老杜的学杜门径。方回在对《题李频新居》一诗的评点中对这一门径表达得最为清楚:“予谓学姚合诗,如此亦可到也。必进而至于贾岛,斯可矣;又进而至老杜,斯无可无不可矣。”既然由姚合、贾岛入可学老杜之诗,那这二人的作品自是不容不选。
(四)欲以晚唐之“细润”济江西之“粗抹”
方回曾在评许浑诗时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君子于待人宜然,予之评诗亦皆然也.”[1]520方回在此表达自己评诗时客观公允的态度。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才能看到“格卑”的晚唐诗亦有“细润”的长处,甚至能摒弃江西诗派的门户之见,提出以晚唐之“细润”济江西之“粗抹”。他说:“大历十才子以前,诗格壮丽悲戚。元和以后,渐尚细润。俞出俞新,而至晚唐。以老杜为祖而又参此细润者,时出用之,则诗之法尽矣。”[1]14李庆甲先生在《瀛奎律髓汇评》“前言”中指出,《瀛奎律髓》反映了“方回崇尚‘江西诗派的立场”。“重振‘江西旗鼓,纠其缺失,维护、发扬其创作主张和美学原则,以改革‘四灵派、‘江湖派所造成的颓俗卑弱的诗风,是方回编选《瀛奎律髓》的根本宗旨。”[1]3方回的确崇尚江西诗派,欲重振江西旗鼓,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江西苦于粗而冗”[1]386,欲纠其缺失。江西诗派主张“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好尚生新,一味追求险韵险字,以致诗歌往往诘屈聱牙、晦涩难读,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意境美。晚唐之“细润”恰好是治江西的一剂良药。方回曾在诗论中表示,晚唐诗虽然“格卑”,但其纤细工夫却是作诗时不可缺少的:“盛唐人诗气魄广大,晚唐人诗工夫纤细,善学者能两用之,一出一入,则不可及矣。”[1]1485晚唐诗的“细润”在形式上主要表现在对仗工整和文字清新巧丽。如张祜的《题杭州孤山寺》:“楼台耸碧岑,一径入湖心。不雨山常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藓合,空院落花深。犹忆西窗夜,钟声出北林。”此诗在内容上则表现为写景摹物极为细腻。如赵嘏的《长安晚秋》:“云物凄凉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残星几点雁横秋,长笛一声人倚楼。紫艳半开篱菊净,红衣落尽渚莲愁。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江西诗派以老杜为祖,格高瘦硬,若能再参此种“细润”以济“粗抹”,便“不可及矣”。
四、结语
尽管方回的诗论主张在总体上尊盛唐而抑晚唐,但他秉承着切中肯綮的选诗观,看到了晚唐诗也有诸多优点,“其细润而工者,亦不可泯没”[1]1055,所以《瀛奎律髓》中选入了不少晚唐诗篇。正如查洪德先生所言:“选本呈现的选家诗学主张,有显性的,有隐性的。研究者看到的往往是其显性的,亦即其声称的选诗标准;容易忽略的是隐性的,亦即实际选诗中体现的诗学倾向。”[5]142我们认为,在对诗歌选本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选家所声称的显性诗论主张与其选诗实际发生错位时,我们不应当忽视其选诗实际所体现出来的隐性倾向。唯有将诗论主张与选诗实际二者相结合,深究细辨,方能了解选家最真实的诗歌观。
注释:
①此处数据依据查洪德、袁梅发表在《中州学刊》2018年第1期上的文章《唐诗选本经典性及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所得。查洪德、袁梅依据现代学划分,将贾岛、姚合视为中唐诗人,而在《瀛奎律髓》中,方回将贾岛、姚合视为晚唐诗人。此处在查洪德、袁梅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加上了贾岛诗67首,姚合诗22首。
参考文献:
[1]方回.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79.
[2]张红运.“四唐说”源流考论[J].贵州社会科学,2004(4):124-128.
[3]查洪德,罗海燕.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6):73-79.
[4]康莉.瀛奎律髓的晚唐观研究[D].广东:暨南大学,2007.
[5]查洪德,袁梅.唐诗选本经典性及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J].中州学刊,2018(1):139-144.
[6]陈亚飞.方回的唐代律诗演进观[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3.
作者简介:曾雪纯,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原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