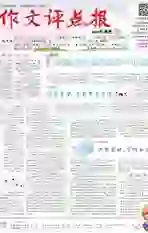烙馍
2020-08-04朱秀丽
朱秀丽
“从北京到南京,中间隔个徐州城。中原人爱吃烙馍馍,那么地个狠劲咬,那也不嫌牙根疼。”这个小曲唱得有趣,爱吃烙馍的徐州人听着不禁莞尔。
旧时,徐州地区的女子出嫁前除了学会女红,还要会做饭。而做饭的十八般武艺中,做烙馍是必不可少的。做烙馍的面要软硬适中,太硬,馍很难做薄;面软,做的馍容易烂。做烙馍的擀面杖两头尖,中间粗。手巧的女人擀面的时候,面皮会绕圈旋转,薄得透明。年轻的女子初学擀烙馍,对着面剂子直着狠劲下去,一杆子下去,中间薄两边厚,厚薄不匀,而且面皮也不转。倘若旁边是娘或婆婆,笨笨的女子免不了被竹劈敲几下头。其实这又何妨?哪个女子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做烙馍,日子久了,做得多了,手熟罢了。
擀烙馍是巧手活,翻馍也是技术活。鏊子支好,柴火烧旺,烙馍一翻,几秒钟就好了。在老家,母亲做烙馍,父亲烧鏊子翻馍,两人拉着呱,日子过得不紧不慢。母亲扬起擀面杖,挑起馍,覆在鏊子上,又快又准。待馍鼓起小泡,父亲眼疾手快,轻轻抖动竹劈,翻开绵软的馍。父亲总结他的经验:这第一翻最见功力,早了,馍不离鏊子,馍会破;迟了,馍会糊,黑眼圈的烙馍是败笔,没人愿意吃。第二翻的时候,馍会鼓起大泡,这是烙馍最好的火候。一生握笔的父亲,偶尔做点家务,做母亲的副手,配合默契,俨然是高手风范。
烙馍做完,鏊子下的余火未尽,母亲喜欢趁热炸芝麻。芝麻沾上滚烫的鏊子,疼得直跳。母亲扯起一张烙馍覆住蹦跳的芝麻。芝麻的香气在空气里荡漾,勾得屋子里的“懒汉”都跑出来了。我和两个哥哥一直被母亲斥为“懒汉”。倘若她让大哥去干活,大哥会告诉二哥,二哥这个二传手当得毫不含糊,皮球旋即传给了我。我说不会。一句不会,一了百了。母亲说:“大懒支使小懒,小懒支使不动。能让你们仨愁毁。”芝麻炸过,要在碓窝子碓碎。这样的美差,傻子才不会!我抢过碓头,大呼小叫地喊着号子碓芝麻,不时伸出手指偷吃,吸一下鼻子,那个香呀,渗到了牙缝里。碓碎的芝麻撒少许盐,用烙馍卷着吃,是难得的美味。
很多美食是独立的,比如螃蟹,比如鳜鱼,自成体系,独领风骚;也有很多美食一生都在寻找灵魂的伴侣,比如梅干菜遇上五花肉,剁椒恋上鱼头,彼此成就,演绎经典。烙馍的一生亦因寻找而精彩。烙馍不仅喜欢卷芝麻盐,还爱过撒子、土豆丝、羊肉串。这些美妙的“情史”让烙馍为人津津乐道。
鸡蛋韭菜盒在苏北极负盛名。韭菜和鸡蛋拌匀,摊在烙馍上,两张一合,在鏊子上煎熟。咬一口,烙馍因鸡蛋愈加柔软,韭菜清香缠绕齿颊,倘若再来碗鳝鱼面筋汤,幸福简直不要太多了。街边的餐馆若有了这鸡蛋韭菜盒和鳝鱼面筋汤,生意不会差。随性的苏北人对饮食没有太精细的讲究,烙馍和鱼汤足以饱腹。
我有时嫌韭菜出水,喜欢做鸡蛋烙馍。两面煎至金黄,外酥里软。煮一锅浓浓的白粥,弄些小菜,鸡蛋烙馍成了餐桌的主角,一家人围桌而坐,吃得眉开眼笑。
母亲进城二十余年了。起初,她舍不得家里的老物件,鏊子、竹劈都搬到了楼房里。天长日久,那些物件没有用武之地,只好送人了。偶尔吃一次烙馍,要么买的是机器加工的,要么是手工的,但厚薄和柔韧度总和母亲做的烙馍差那么一点点。
水烙馍是烙馍家族中的新生代。它无意中遇到了京酱肉丝,从此合体出镜,声名鹊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邂逅“京城阔少”——北京烤鸭,水烙馍的生命从此改写。灰姑娘与王子结合的版本成为餐饮界的佳话。烙馍从乡野的饭桌登上了国宴大厅。
一天中午,去父母家蹭饭。母亲端出了一叠水烙馍,一盘芝麻盐。七十九岁的母亲骄傲地说:“没有鏊子,我也能做烙馍了!”我一口气吃了三张水烙馍,忘记了节食和减肥那些无聊的事。遇到幼年一直爱吃的食物,除了报复性地狠狠吃,没有其他可以慰藉落寞的肠胃。
【赏析】
文章從烙馍的做法讲到烙馍的搭配,掺杂了童年回忆的同时也写出了一部浓缩的烙馍发展史,读之让人垂涎。七十九岁的母亲在没有鏊子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做烙馍,可见烙馍在母亲心里的重要性。其实,能慰藉落寞的肠胃的,不仅是记忆中的美食,还有美食背后的情感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