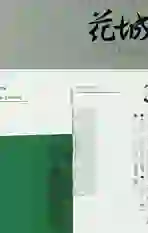猫将军
2020-07-30孙频
我把我的小饭店从县城的南街挪到北关,又从北关挪到东门,最后又从东门挪到旧车站附近。在巴掌大的县城里这么腾挪跌宕一番,好像我正一个人对着一张棋盘下棋,把棋子下到哪里,完全是我自己说了算,倒也过瘾。在小县城里,像我这样靠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的人不计其数。我们都是被永远留在县城里的人。
南街的路面虽然宽敞些,但一条路上几百米内就长出了几十个小饭店,雨后蘑菇似的,密密麻麻令人心惊,小老板们一里地之外就开始拉客。开张几天之后我就盘算,老子还是搬走算了,不在这凑熱闹了。到了北关又发现,这里藏着很多地头蛇,招惹不起,还是赶紧滚蛋。东门倒是热闹,从前老县城的中心嘛,至今还有府君庙、城隍庙、广生院,虽然都已经破破烂烂,广生院门口的那棵大槐树已经活了一千五百岁,老妖精似的,还活得挺精神。据说住在这片的居民,连厕所都是拿明朝老城墙的砖垒起来的。可是房租贵哪,开业一月有余,发现连房租都赶不出来,只好再次把我玩具一样的小饭店折叠起来,雇个三轮车,又连滚带爬地迁到了旧车站一带。
经过考察,我发现这是个好地方。首先,房租便宜,荒凉嘛,自然就便宜。其次,这一带几乎看不到饭店。再者,旧车站属于半废弃状态,虽不算热闹,但至少还有客车经过,有人来往。于是直到此地,我的小饭店才算正式开张。说是饭店,不如叫面馆更合适。因为我主营桃花面,辅以凉拌三丝、西芹花生米之类的小凉菜。桃花面的名字听着绚烂夺目,其实也就是一碗刀削面加些浇头,浇头倒是有些讲究,里面必须有肉丸子、红烧肉、小酥肉、油豆腐、海带这五样东西,一锅炖得烂熟,浇上去,才能配得上桃花面这一称呼。刀削面我更是练得炉火纯青,站在两米之外,把面团顶在头上,都能把面准确地削到大锅里去。因为几乎没有人来欣赏我的绝技,我在削面的时候时常暗自落寞。小时候成绩不出色,没有考上大学,父亲原打算把我塞进他们厂里,结果厂子先倒闭了,众人遣散,找不到个去处,没办法,我只好苦练刀削面。时间久了,觉得做饭的时候都像在耍杂技,我就是那个杂技演员。
空闲的时候,我时常站在饭店的玻璃门后往外瞅。我饭店前面的视野相当好,门口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旧国道,斜对面是旧车站,旧车站旁边是一大片荒野,杂草丛生,几乎看不到建筑,荒野上只有一片稀疏的枣树林,枣树林的后面有一处孤零零的红砖院子,我知道那院子里住着一个养鸡的老头,姓刘。我之所以能认识他,是因为老刘时不时会来我饭店里吃碗面,就着生蒜,喝着面汤,一来二去,不想熟也熟了。
有时候,倚在玻璃门后便能看到客车路过旧车站,放下几个乘客来,有的乘客会来我店里吃面,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但我又生怕遇到从前的同学,在外地工作的,一回老家就是衣锦还乡的架势,我对他们避之不及。有时候,小饭店里只有老刘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面,吃完面哧溜哧溜地喝汤。我解下围裙坐在他对面,一边抽烟一边问,味道咋样?他使劲吸吸鼻子,用手抹抹嘴,嘴里喷着刚猛的蒜味,还可以。我说,老刘,你怎么不住到城里,一个人住在这野地里不害怕?他咽下满嘴的面条,又喝了口面汤才说,养鸡嘛,臭得很,把别人都熏着了,就要躲到这野地里来养。我想想也是,便又问,那你家三宝呢?又出去玩了?他一个人住在那红砖院里,养了一只大黑猫,取名叫三宝。我有些奇怪,并没有看到大宝二宝,何来的三宝,但也不好意思多问。
三宝是一只极其威风的公猫,浑身漆黑如炭,毛皮溜光水滑,只有两只前爪是雪白的,两只眼睛则是绿色的,祖母绿一般。三宝从小到大只吃过两样东西,生鸡蛋和老鼠。鸡舍里碎掉的蛋统统喂给三宝,鸡舍里上蹿下跳繁衍兴旺的老鼠一直是三宝的主食,所以除了鼠肉,三宝从未吃过别的肉,也不认得鱼,更不知道鱼肉可以吃。有一次我拿鱼肉喂它,它只是很鄙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踱到窗前晒太阳去了。有时候老刘喝酒的时候,还会喂三宝一点,三宝喝了酒很快醉倒,躺在炕上四仰八叉地睡着了,呼噜声比老刘打得还响。
大概是因为鸡蛋比较有营养,三宝比一般的猫雄壮魁梧很多,简直不像一只猫,而像一只小型的黑色老虎,虽然都是猫科动物,但毕竟气场有别。它身手极其敏捷,可以像闪电一般从房梁上忽地跃到地上,又可以像蛇一样无声地游走在天花板上,据说它一天可以抓一串老鼠,然后纷纷进贡到主人的炕头。它吃不完的老鼠,老刘就帮它做成鼠干,挂在房檐下,替它储存着。这都是听老刘说的,他那院子我一次都没进去过。人家从没邀请过我,我也不好厚着脸皮硬要进去串门。
有时候他来我店里吃面的时候,三宝会跟着他一起过来。我饭店的玻璃门正对着荒野里的那条羊肠小径,所以他们一出门就在我的视野里。三宝走路的姿态,简直就像一匹老虎坐骑跟在他的后面。我喂它两颗肉丸子,它也并不知道吃,只拿爪子拨来拨去当球玩,时而抛到空中跳起来接住,时而扔到柜子下面,再用爪子使劲勾出来。我叹道,你这猫当得真亏,除了老鼠什么肉都没吃过,白活了。老刘和三宝共盖一床被子,三宝前半夜出去云游四方,后半夜回来,钻进被子睡在老刘的脚边,还打着震天响的呼噜。
老刘来吃面的时候,有时候会给我拎两只死鸡当礼物。他拎着死鸡的爪子递给我,说,放心吃你的,不是药死的,没毒。我看着两只血淋淋的鸡,其中一只轻飘飘的,但体形完整,好像是缺了内脏。我有点心惊胆战,悄悄问,它们是怎么死的?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搭起二郎腿,慢慢抖着上面的一条腿说,这鸡吧,啊,有个爱好,就是个爱好,就像你喜欢抽烟,我喜欢喝酒,就是个爱好。它们喜欢红色,不对,是不能见红色,一见红色就会发疯,所以嘛,你知道关在鸡笼子里的鸡最怕什么?最怕有伤口,不管是什么部位,只要受了伤,流了血,别的鸡就会哗啦全围上去,使劲朝着那个流血的伤口啄,有时候伤口越啄越大,内脏都被啄出来了,那受伤的鸡有时候就这样被啄死了。虽然死相不好看,但毕竟是肉嘛,炖熟了都一样。早和你说了,不是老鼠药药死的。把心放宽,加点干蘑菇,就是个不赖的菜。
我看着死鸡,皱着眉头说,你自个儿怎么不吃?他要了一瓶二两装的柔绵汾阳王,拧开盖子喝了两口,继续抖着腿说,我从来不吃鸡肉,不对,是自从养鸡之后,就再不吃鸡肉。我说,为什么?他叹气道,你自己养养就知道了。我说,那就给三宝吃嘛。他得意地说,我家三宝打小在鸡笼子里长大,小鸡们都是它的亲戚,它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亲戚还能吃。
走的时候他一般还要再打包一份小碗面带走,开始时我很是疑惑,怀疑他并没有吃饱。我说,不够吃早说嘛,我给你加面就是。他却说是留着给自己晚上吃的。不过通常他吃完也并不急着走,总要慢慢啜两碗面汤帮助消化,一边找些话和我说。到最后,小饭店里只剩了我们两人,分别坐在一张桌子的两旁,我抽烟,他喝汤,半天找不出一句话来。
我猜想,他一个人住在这县城边上,只有一只不会说话的猫做伴,到底还是孤单了些。我便找话说,老刘,最近鸡蛋卖得咋样?他说了等于没说,时好时坏,不好说。我又说,老刘啊,你以前是干嗎的,怎么跑到这里来养鸡?老刘说,以前是机床厂的工人,后来厂子散了,总得想法子挣两个钱,要不吃什么喝什么。我朝空中慢慢喷了几个烟圈,看着烟圈渐渐消散,感慨道,可不,一天抽一包赖烟都得十块钱,现在钱不好挣哪,你说我当初要是考出去了,怎么也比现在强吧。
老刘忽然面色铁青,一语不发地看着玻璃门外。我吓一跳,心想自己哪句话说错了?我们俩半天没再说话,长长的沉默,都呆望着玻璃门外。门外走过去一个胖女人,又走过去一个光头男人,光头男人还趴在玻璃门上往里看了看。我没话找话,问道,老刘,你家三宝为什么叫三宝呢?莫不是它上面还有别的兄弟姊妹?他神情依然冷峻,看着门外点点头,嗯,它上头还有俩哥。我说,怪不得。像是怕冷了场,又赶紧问了一句,你家儿女呢?也不见来看你,莫不是都在外头上班?
我注意到他摆在桌子上的那只手忽然握成了拳头,关节突出,大如核桃,我在空气里都能闻到一种类似金属的味道。我忍不住一阵害怕。只听他叫了一声,三宝,过来。三宝闻声,噌一下就跳到了他腿上,然后眯起眼睛,像只小老虎一样卧在他膝上。他一边用大手抚摸着三宝的头,一边倨傲地说,我家那小子还算给我长脸,念完博士就留在北京啦,在大学里当老师。我啧啧惊叹,博士都念完了,真是长脸,老刘你是怎么培养出一个博士的?他慢慢抚摸着那只硕大的猫头,忽然从鼻子里冷冷笑了一声,当年我和我的连襟在一起喝酒,我连襟工作比我好,那天他喝多了,指着我说了一句,你一个烂工人。我说我这辈子就是个烂工人了,不过烂工人也有后代,对吧?时日长着呢,咱们慢慢走着看。
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长得足以让人昏睡过去。我觉得自己应该再说点什么,说什么都行,只要不让我们之间就这样荒着。但奇怪的是,我一句话都不愿再多说了,我心里什么地方隐隐觉得不舒服。直到老刘站了起来,他把三宝高高举过头顶,然后放在了自己脖子上,让三宝骑在那里,自言自语道,我们回家喽,喂鸡的点到了。
在他站起来的一瞬间,我发现他的裤子拉链又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红色裤头。有时候他这样堂皇地敞着拉链就过来吃面,我一直不敢告诉他,怕他觉得我在看笑话。这次我忽然下定了决心,小声提醒了他一句。他连忙低头查看,一愣,赶紧拉上,抱歉地对我笑笑,说,这裤子不太合身,一坐下去,拉链就容易开,站着就开不了。说完他赶紧驮着三宝出去了,笨拙地左顾右盼了一番,看没有车辆经过,这才穿过国道,向荒野里的红砖院子走去,三宝像顶黑色的帽子戴在他头上。我倚在门后,一直目送着他的背影彻底消失。
没有顾客来吃饭的时候,我经常这样,倚在门后,叼着一根烟,看着面前的人来人往。除了长途客车,县城的公交车每天也要从我门口经过六次,我数了一次又一次,不多不少,整整六趟。县城的公交车极小,看起来像长着轮子的大面包,车上只有四五个座位,一路大声放着儿歌,所以每次只要远远听到有粗暴的儿歌声传来,就知道是公交车快来了。在县城里开车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因为刚踩了一脚油门,就到目的地了,实在没有什么快感可言。公交车又是踩着点晃过来的,所以更多的人还是选择电动车。电动车开起来无声无息,又可以在马路上快速游动,一不小心就窜到了背后,幽灵一般。到冬天的时候,寒风刺骨,为了保护膝盖,大多数的电动车上都要加个挡风的垫子,骑车的时候,把厚厚的垫子盖在腿上,简直像一人裹了一床棉被在赶路。
我注意到有个老头,经常用自行车带着一只硕大的音箱,一直骑到我对面的荒野里,然后取下音箱,拿起麦克风,开始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得极其投入,每次唱完,都要对着无人的荒野深深鞠躬,大声说谢谢。我还注意到有几个女人经常在旧车站前面的空地上跳舞,其中有一个烫着钢丝头的女人每次必在,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她都会按时出现在旧车站旁,像上班一样准时。身上穿的也永远是同一套行头,迷彩裤,马丁靴,冬天是黑皮衣,夏天是黑半袖衫。我奇怪的是,她们在早晨跳,上午跳,下午跳,晚上跳,深夜跳。似乎是除了吃饭时间,剩下的所有时间都在那跳舞。
有一次和隔壁五金店的老板蹲在一起抽烟,说起跳舞的事,他笑眯眯地说,这两年县城里就流行跳舞,好事,总比耍钱强,跳舞又不会跳得家破人亡,我老婆现在麻将都不打了,天天忙着跳舞。我抽了口烟,说,我看这跳舞一旦上了瘾,比别的瘾都大。
除此之外,进入我视野的便是老刘的那座红砖院子。每次只要他一出门,就铁定在我的视野里。有时候他会开着他那辆三轮车出门,估计是去卖鸡蛋。三轮车只有火柴盒大,蹦蹦跳跳地跑远了,回来的时候,车里装着一大袋玉米,车顶上还绑着一大袋玉米,玉米袋看起来比三轮车还大,把三轮车压得像块三明治。大约是喂鸡的饲料。还有的时候,他会带着几只少了鸡冠或少了内脏的死鸡出门,把它们便宜卖给一些饭店。我亲眼看见了那些死鸡的惨状后,曾有一段时间给所有的亲戚都打了一圈电话,只叮嘱他们一件事,去了饭店千万不要点鸡吃。
天气越来越冷,初冬到了,路边白杨树的叶子已经落光,树干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眼睛,猛地看过去,还真有些恐怖的意味。对面荒野里的杂草都枯死了,变成了衰败的黄色,阳光好的时候,则会变成金色,整片荒野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近于璀璨。我的小饭店里生了个铁皮炉子,炭烧得通红剔透,炉子上坐了一只大号的白铁茶壶,水煮开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雪白的水汽,人的脸都消失了,几个无头人坐在桌前吃面。
老刘还是隔三岔五地过来吃碗桃花面,心情好的时候就多要一瓶二两装的汾阳王,就着一碗面慢慢喝酒。天一冷他就把自己一层层地裹起来,毛衣外面穿着棉背心,棉背心外面是棉衣,棉衣外面是军大衣。我之所以能一层层地看到最里面,却是因为,不管天多冷,他总喜欢敞着怀,所有的衣服都不扣扣子,好像又是不怕冷的气概。我猜测,大约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敞着比较时髦。不过他天天如此敞着我也就习惯了,裤子拉链倒是再没开过。
我坐在炉子旁边打起了瞌睡,好像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刘推门进来,要了一碗桃花面。声音过于真切,就在耳边,我从梦中惊醒一看,老刘真的就站在我眼前,那个女孩跟在他身后低着头玩手机。我看了看表,已经下午两点钟了。老刘在桌前坐下,把大手往桌上一拍,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泥垢,食指和中指上还缠着胶布,他大声说,来两碗桃花面,一大一小。这次连凉菜都不要了。
两个人还是一言不发地吃完了面,又面对面呆坐了一会儿,但还是没说一句话,随后便出了饭店,依然是一个朝东走,一个朝荒野里走。
下午饭店没人来吃饭,我坐在炉子后面,一边烤火一边琢磨着这件事。忽然再次想到一个问题,老刘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到这荒野里呢?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于是便给亲戚朋友打了一圈电话,打听老刘的底细。在一个馒头大的县城里,要打听一个人太容易了,只要拐两个弯便打听得一清二楚。老刘原来确实是机床厂的工人,他老婆和他是一个厂的,早早得癌症死了。老刘一个人带大了三个子女,子女都十分有出息,上学的时候都是好学生。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工作,可是工作一年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也一直没找到。二儿子读完博士后留在了北京一所大学里当老师,挺有出息。最小的是个女儿,学习成绩也特别好,可是这个女儿在十四岁那年爬上教学楼的楼顶,跳楼自杀了,据说是因为学习的心理压力太大。这件事当时被学校给压下来了,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直到晚上十点,实在没顾客了,我才关了小饭店,拉下卷闸,准备骑着电动车回家睡觉。整个县城在冬夜的寒风里缩成一团,街上鲜有行人。开始有拉煤的大货车借着夜色的掩护狂奔在国道上,因为白天是不允许大货车上路的。货车庞大诡异的黑影不时在我面前疾驰而过,我站在路边眺望着对面的荒野。夜晚的荒野看上去阴森可怖,如被一场黑暗的大雾笼罩着,依稀能看到一点微弱的灯光,飘动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那是老刘的窗口发出的灯光。
一连五天,一到中午,老刘就带着那女孩来我的小饭店吃面,到后来他们已经不再做任何交流,只默默地吃完面就离开了。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又来了,这次都不用吩咐,我就知道要两碗面,一大一小。我在厨房做面的时候,忽听见老刘说了一句,你有这钱每天住旅馆,不如干点别的。那女孩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又听老刘说了一句,我和他也联系不上,你打他的手机嘛,能打通?你说让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女孩还是没说话,像是睡着了。我把面端出去一看,女孩还是坐在那里低头看手机,老刘正笨手笨脚地给自己剥蒜,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泥垢。
吃完面走出饭店,我看到他们站在门口忽然激烈地争吵了一番。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嘴唇在动,却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争吵完之后,女孩没有向东走,而是跟着老刘过了国道,向荒野里的红砖院子走去。我倚在門后看着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荒野里,背上忽然一阵紧张,我意识到可能要发生什么了。整整一下午,我都没挪地方,一直紧张不安地盯着那条荒野里的羊肠小径,从红砖院子里出来的话,只能走这条路,而只要走在这条路上,就能收进我的视野里。那女孩一直没再出现在这条路上,那就是说,她还在老刘的院子里,还没有离开。
到天快黑下来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出现在这条路上。我一下午抽完了一包烟,抽得喉咙发痛,整个人却既兴奋又紧张,一条腿站麻了都不觉得。随着夜色的降临,我的恐惧感在一点一点增加,那条小径上依旧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影。我甚至几次拿出手机,想着要不要报警。最后我没有报警,却走出了小饭店,穿过国道,向那片荒野走去。我不敢去敲老刘的院门,只是围绕着那红砖院子慢慢转了一圈,试图想发现点什么。荒野已经在半透明的夜色里渐渐狰狞起来,我什么都没发现,只在院子后面发现了一座小小的坟堆,坟堆没有墓碑,长满荒草,却在坟前摆着些五颜六色的纸花,还是簇新的,在萧索的寒冬里看上去十分炸眼。我心想,老刘把院子就建在坟墓旁边,晚上也不觉得害怕?
直到我晚上十点打烊的时候,都没有见到那女孩再从红砖院子里走出来。那院子已经亮起了灯,一点幽幽的灯光,像荒野里的鬼火一般。我站在路边徘徊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还是先回家睡觉。
第二天上午,我骑着电动车来到小饭店前,连卷闸都顾不上拉开,就急忙走到那条羊肠小径上细细察看,想看出些痕迹来。结果,就在这条小径上,我发现了几点血迹,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看到那几点血迹的时候,我的脚都开始发软,头在寒风中忽地变大。我想,我可能是这件事唯一的证人,只有我看见了什么,但又什么都没看到。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没什么本事,开着一个小饭店糊口,没见过什么世面,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却忽然之间亲眼看见了这样一个秘密。我又顺着血迹跌跌撞撞走了几步,发现路上还有不少散落的鸡毛。在小径的尽头,红砖院子静静地站在那里,如坟墓一般,没有任何动静。我停住了,不敢再往前走。
中午一点多的时候,饭店里顾客渐少,我正收拾碗筷,忽然有两个人推门进来,夹着一股冷硬的寒风。我一看,吃了一惊,来人是老刘,跟在他后面的正是那女孩,那女孩又摘下眼镜,拿脖子里的围巾随便擦了两下便戴上了。她看上去毫发无损,和前几天没有任何区别。我又是惊喜,又是失望,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来,只呆呆地看着面前的两个人。
老刘坐下来,搓了搓两只又大又硬的手,对我说,桃花面,一碗大的一碗小的,多加几个肉丸子,再拼一盘凉菜,多放点五香花生米,再来一瓶二两装的柔绵汾阳王。在听见他说多加几个肉丸,再拼一盘凉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忽然就没有来由地湿润了,我拼了满满一盘凉菜摆在他们面前,又给他拿了一瓶二两装的柔绵汾阳王,两个酒盅。老刘咧开嘴对我笑了笑,露出了一嘴黄牙。不知为什么,我不敢多看他,赶紧进厨房做面去了。
等我把两碗面端出来的时候,老刘正就着凉菜喝着汾阳王,那女孩第一次放下手机,手里也捧着一个小酒盅,她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点,皱起眉头,赶紧吃了粒花生米,然后又舔了一点,又赶紧吃一粒花生米。老刘看着她笑,但两个人始终没说一句话。我把两碗面轻轻放在了桌子上,我竟然有些紧张,因为我在每碗面的最下面埋了一个卤蛋。我怕他们马上就发现了,又怕他们吃到最后也没看到藏在底下的卤蛋。
老刘很快把一碗面全吃完了,包括埋在下面的卤蛋,女孩还是吃了两口就不吃了。我躲闪了半天还是不小心碰上了他的目光,我们相互对视了一眼,又很快闪开了。他走过来付钱,身上还背着一个样式陈旧的人造革包。他把五百块钱放到我面前,我大吃一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老刘,你这是什么意思?两碗面大的六块小的五块,一盘凉菜八块钱,一瓶汾阳王三十五块钱,你又不是头一次在我这里吃饭。
老刘把几张钱压到筷子盒下面,又掏出两把钥匙和钱放到一起,然后终于看着我的眼睛说,老张,我问你,你是开饭店的,每天有没有剩菜剩饭?我说,那还用问,每天都有剩菜剩饭。他用大手一拍桌子,说,那就行,有一碗剩饭就够了。老张,我要出趟门,去找我家那小子,我不在的时候,你端碗剩饭,多去我家里看看。
我说,你是让我帮你喂三宝吧,放你的心。他略一犹豫,说,还有大宝。我诧异道,原来你养了两只猫啊,怎么从来没见过那只,放你的心,一只是喂,两只也是喂,包在我身上。说着我拿起那五百块钱,硬要往他包里塞。他突然发怒了,用力把我推开,后退几步,眼睛明亮异常,嘴里却呵斥道,你这人怎么这样,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我不再说话,手里捏着那几张钱,呆呆地目送着他和那女孩一起离开了饭店,他们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倚在玻璃门后,看着他们一前一后穿过国道,走到了旧车站的前面,那是长途客车路过的地方,经常会有人在那里截车,看见车过来了,远远就招手。如果客车还没拉满人,就会停下,如果已经客满,客车就毫不犹豫地疾驰而过,不做片刻停留。我看到他们两人在那里默默站了一会儿,彼此间并不说话。一辆大客车过来缓缓停住了,挡住了两个人的身影。等到客车开过去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已经不在原地了。
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我可能再也见不到老刘了。一种奇怪的恐惧感压迫着我,让我幾乎喘不过气来。我呆呆坐在一把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中途有两次拿起手机想报警,也只是拿起来便又放下了。
一直到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半透明的夜色已经在荒野深处悄悄生长了出来,我破例提前打烊,拉下卷闸,拿着那两把钥匙,穿过那条羊肠小径,朝着小径尽头的红砖院子走去。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神秘的院子。院子的北面有三间红砖瓦房,盖得很粗糙,靠西面的一间还拉着窗帘。院子中间是一块小菜地,因为是冬天,菜地里什么都没长。菜地旁边还打了一眼井。院子南面是一排简陋的鸡舍,我走进去一看,只有空空的鸡笼,里面居然连一只鸡都没有了,槽里的玉米粒还没有吃完,满地都是鸡粪和杂乱的鸡毛。
这时天色更暗了,夕阳即将沉入群山之中。我终于朝那北面的三间房屋走去。最东面的那间是做厨房用的,里面有灶,灶上有一口铁锅,旁边站着一口一人高的大水瓮。墙角立着十几棵大白菜,用破棉被小心盖着,桌子上摆着两副碗筷和一只电磁炉,还有半只吃剩的白萝卜放在案板上。中间那间应该是老刘睡觉的屋子,屋里有张炕,还是热的,炕洞里烧着柴,炕上是一卷油腻枯瘦的被褥。在这里我看到了三宝,那只大黑猫正缩在这被褥的缝隙里睡觉。地上只有几件家具,一个立柜,一个平面柜,一把折椅,墙角立着自己做的洗脸架,架子上摆着一个搪瓷脸盆,还有半块肥皂。椅子下有一个篮子,里面盛着满满的鸡蛋。平面柜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老照片。我拿起来一看,照片里是一对夫妇,他们身后站着两个男孩子,女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女孩。我认得出来,那照片里的男人正是年轻时候的老刘。
我走到了最西面的那间房前,房间里面拉着窗帘,房间居然从外面锁上了。我看了看手里的两把钥匙,试着用那把小的开锁,结果,锁开了。门嘎吱一声推开了,屋里立刻散发出一种浑浊难闻的气味,但屋里一片死寂荒凉,像是根本没有人住在里面。
我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夜色正在加重,屋里又拉着窗帘,所以我走进去之后,一时难以辨认出屋里到底有什么,便茫然地站在那里。等到眼睛终于开始适应黑暗,我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影正静静地立在我面前看着我。我吓得转身欲逃,刚转过身就听见那人影对着我叫了一声,爸爸。我惊恐地回过头来看着那人影,只听他又说了一句,爸爸你看,我把作业都做完了。像是把一个小孩的声音嫁接在了一个大人身上,狂乱稚嫩,带着点哀求,让人听了忽然想流泪。
我摸索到墙角把灯拉开,这才发现,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身上裹着一件旧棉袄,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一手拿着作业本,一手握着圆珠笔。我发现他看人的眼神不对,直勾勾的,一眨不眨,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又举起作业本说,爸爸,我把作业都做完了。看起来应该是个傻子或精神病人。我忽然想起老刘临走前对我说的话,还有大宝。我背上一阵发冷,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弥漫在我全身的每个角落。
我开始慢慢靠近他,看他并没有攻击我的架势,他甚至有点怕我,我往前的时候,他往后躲了躲,温顺而畏惧地站着,依然坚持把手里的作业本举了起来,对我说,爸爸,你看,我把作业都做完了。我向他伸出手去,他使劲盯着我的眼睛,盯了一会,把手松开了。我看到自己的手在发抖,我看着他所说的作业,是一幅画,用圆珠笔画的,如儿童画一般简陋,画上有三个小孩手拉着手,都没有面孔,最小的那个扎着两个小辫,看得出应该是个女孩,那女孩手里还拉着一只小猫。他们的头顶有太阳,身后有一座木头小房子,女孩的脚下还长着一朵花。
我举起作业本,看着他的眼睛,试着问他,你画的这是谁?他盯着我又看了半天,忽然说,我带着我的弟弟和妹妹一起玩,这是大宝,这是二宝,这是三宝,这是我妹妹养的猫,我妹妹最喜欢的就是猫。我几乎有些站立不稳,我说,你就是大宝?他又往后退了一步,把两只手藏到身后,这时我听见他对我说,爸爸,我把作业都写完了,明天就要考大学了,你不要打我,也不要打妹妹。
我后退几步,一直退到门口,好不容易才站稳,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打量这间屋子,也有一张炕,几件简单的家具,屋里收拾得倒还算干净,只是到处扔着书和作业本,每一本打开的作业本上都画满了奇怪的图像和符号,似来自另一个世界里的语言。忽然,我注意到柜子上有一件奇怪的摆设,是一只白瓷猫,四脚着地,昂着头,尾巴高高翘起,神情骄傲,在这瓷猫的背上,骑着一个用泥捏出来的小女孩。小女孩骑在猫背上,也高高地昂着头,神情欢快,似乎随时等待着和她的坐骑一起奔跑。
责任编辑.许泽红
孙频,江苏作协专业作家,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小说集《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疼》《盐》《裂》三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