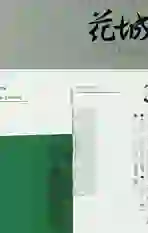鸟兽草木之名
2020-07-30阮夕清
赵爱国深吸口气,神情也阴沉下去,压低声音,仿佛老电影里大街上接头的特务,他告诉李荣一个秘密——前天晚上,九点钟十点钟的样子,前进粮油店的刘师傅提着一篮子山楂片、话梅、饼干、面包还有果冻飞上了半空,篮里塞着几大包食品店刚出样的口香糖,零食包装袋反射出迪斯科舞厅里才有的、球状转灯的彩光,草莓味口香糖闪红光,香蕉味闪黄光,刘师傅的大肚子都飞到云层里去了,可光点还在闪,越来越小的刘师傅就像一架夜航飞机飞远了。
赵爱国说几句,掩嘴张望四周,再说几句,眼角抽搐,愈加证明了他是冒着随时祸从口出的危险。可如此重要的时刻,李荣并没有见证,李荣继续用水彩笔涂抹语文书,他在西门豹腰畔佩了驳壳枪,额头上画了第三只眼,正细心地给它添上长长的眼睫毛。窗外,干净的大晴天,教室像被封在琥珀里,万物如拭,他们的脸有窗明几净的光泽。显而易见,李荣对这个秘密不感兴趣。赵爱国沉吟一番,像是下定决心结束试探接头人,交出手中的密码本了;他带着毅然的神情说了另外一个秘密,悄悄凑到李荣耳边,声音压得更低了,仿佛一条老鼠尾巴——居委会隔壁的吵架大王李奶奶是猫精!
一到雨夜,十一二点的样子,她假装喊几声“有老鼠,有老鼠”,没人答应,说明家里人睡死了,她就脱下人皮,卷好,扔进樟木箱里——下次碰到她,你凑近闻闻,她身上总是有股樟脑丸气味的。她伸出小脚爪,支开窗,看看外头没有人,嗖一下跳出去,像运动员跳水。李奶奶和其他猫精的接头地点是防空洞。有的猫骑着条帚来,有的猫骑着拖把来,还有猫骑着书包来,小猫骑文具盒,再小的猫骑圆珠笔,等所有的猫都到齐了,李奶奶喵喵几声,发出一声指示,它们一齐仰头,同时蹬脚,朝天空蹿去。它们在比赛谁飞得快,密密麻麻的雨线在它们身前自动分开,让路,它们在真空中飞驰,牵动周围雨水的弧迹,形成一支支猫箭头,战争片地图上代表部队推进的那种空心箭头,猫眼忽转,探测到前头有热带气旋,扫把也自动转弯,它们一滴雨都不会淋到,“这些猫啊,像裁缝手里的剪刀,嗤、嗤、嗤,帮天在开边”。
赵爱国看李荣还是没抬头,他又说了第三个秘密,故意压低的嗓音,反而带了特殊的吸引力,类似蚊子叮人时的小心,只会使人注意力十足:前排的刘丽娜被身后的鬼祟吸引,掉过头来,睁大漂亮的眼睛望着他。赵爱国忽然有些心虚,抬眼偷觑,讲台上空飞满了明亮的灰尘,闪烁幻变,每一颗星球都在熠熠生辉,里面舞动着太阳系,也静止着银河系,十几万光年后的朱老师斜坐靠背凳,垂着头织毛衣,中指、小指反复地一勾一挑,像唱戏的手势。看来,短时间内,身处织女星座的朱老师还回不了地球。
从我房间里看出去,不远处是一座水塔,上面长满野草,半吊着许多鸟窝,你们知道的,就是印花厂那座摔死过人的水塔。我爬上去过的,在水塔值班的是个放出来没几天的劳改犯,吃住都在里厢,外号叫“大兴”,身上文青龙白虎,听过是贩黄色录像带抓进去的,他还请我抽了支烟——“良友牌”——前天夜里,我失眠,什么叫失眠?失眠就是困不着,我就趴到窗口,发现整个水塔的藤萝全飘起来了,像浸在朱老师杯子里的胖大海,我想,要么是黄梅天,空气中潮气多的原因吗?路灯光里,那些藤萝的飘拂加快速度,好像有人偷偷帮地球调快了速度,那一蓬蓬的草,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人影要离开水塔,却又被水塔拉牢,脱不了身,知道地心引力吧,这叫“塔心引力”。肯定被谁用力扯了下,我没看清,但千真万确,一小撮藤萝挣脱了水塔,几乎同时,变成一只大鸟,飞起来了。先是试飞,悬在原地扑翅膀,扑了几十下,慢慢飞,飞到你家屋顶时(赵爱国指指好奇的刘丽娜),它慢慢降下来,踱来踱去,尖嘴埋进胳肢窝里拱拱,再啄啄瓦,觉得不好吃,伸长颈根到处张望,估计是刚生出来,肚子饿,找东西吃,它肯定看见我了,对我叫两声,弱弱的,像小麻雀叫,所以大人们都没有听到,哪怕听到了也不会注意,朱老师骑自行车正好从你家门口经过,她也没有发现,它对着月亮叫几声,挥挥翅膀,升上去了。
狗屁,吹牛大王,还停在我家屋顶上呢?刘丽娜没得到想象中的乐趣,回过身继续做作业。李荣却放下手中的书,若有所思;赵爱国看着他,眼睛得意地发亮——这个秘密有悬念了吧,咱们说好的,一个秘密换一本书,我奉献了三个秘密,你就要借我三本书,我要看《东游记》《南游记》和《北游记》。李荣回过神来:“我们的确是说好的,可要让我觉得好玩的、有悬念的秘密才算,你的秘密根本就不好玩,太假了,一听就是编的。”他翻开书包,掏出三本图画书递给赵爱国:“书你拿去看吧,记住,你欠我三个秘密,下次说几个真的秘密我听听,比如,你喜欢哪个女同学?”赵爱国赶紧摇头,没有没有,又补充道:“我发誓,我说的那些秘密都是真的,那个看水塔的‘大兴,练过武功,能翻十七八个空心跟斗。”
学校由两座红砖小楼组成,两座楼的中间都竖着一人高的铁质五角星,红漆零落,露出黄褐色锈斑,像密集放大的老人斑。两座楼之间是一块正方形水泥操场,平时用作学生们早午操和体育课的场地。此时,场地操场中间有其他班的学生在上体育课,跳绳、踢球、打闹,迎面走过来校工施伯伯,他头发花白,脸上爬满了老树皮般的皱纹,微笑疲惫而慈祥,眼袋肿如金鱼。他手里拎着两只热水瓶,水瓶上印着模糊的“工会”字样。他边走边哼着歌,赵爱国听过这首歌,是《歌声与微笑》,施伯伯和那些学生一样开心,好像有什么好玩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就瞒着自己一个人。
他走在遍地树荫的细碎阳光中,仿佛走入万花筒,眯起眼,那些纤丽的线条光影随意拼凑成自己想要的图案。栀子花香沉重地袭来,浓腻如煮好的肉汤,可看不到栀子花在哪,弄堂转角處是两棵大香樟,叶影层层,压得一大丛灌木也成了更深的树影,一缕缕更瘦的光在灌木中漏出微径,破碎的蛛网轻摇,仿佛有一只虫子刚刚脱身而去,那些光是虫子游走的路。赵爱国奇怪,那几株栀子花明明种在学校操场上,香气怎么会飘到这么远?
这辆奇怪的黑色小轿车,停在破败的棕棚店门口,仿佛从电影里开出来的。轮胎上粘满黄泥,挡风玻璃裂了一处口,形似佐罗划出的“闪电”;可这里半个月没下雨了,这辆车是从哪来的呢,破掉的玻璃是谁砸的?车门的扶手上还缠了根红丝带,明明是女孩子用来扎头发的,现在缠在了车门的扶手上,这会不会是一个接头暗号?
那个突然出现的卖金铃子和无花果的小摊,那根电线杆上刚贴上去的纸头“专治梅毒淋病,一针见效,无效退款”,梅毒梅毒,用杨梅提炼的毒素吗?淋病淋病,下雨淋出的病吗?“萎而不举,举而不坚”,这句话又暗示着什么,万物枯萎的季节不要举火把出门,等举起来的时候,只举一下就可以了,天气冷,手会冻着,不要太坚强;现在谁还会举火把,说明那个人一直在边上守候着呢,等着冬天接头,可怕的老军医,一肚子坏水的老军医,百分之百是潜伏特务的老军医!那个低着头赶路的青年,穿绿色灯笼裤,戴着军帽、露半截手指的霹雳舞手套,他是流氓吗,穿得这么奇怪,怎么还没被严打掉!
之前对李荣讲述太过于投入而形成的恍惑久久不去,赵爱国沉浸其中,成了一面会走路的照妖镜,看到哪,哪里就充满了秘密,哪怕是一片叶子,一张烟壳,一个对他客气地微笑,问他吃了没有的邻居,也在阳光中投射出了千丝万缕的痕迹。
李荣追上赵爱国,他发现了不同秘密中相同的结尾:“你那些秘密里的人啊,猫啊,鸟的,怎么最后都是飞向天空,你也可以编他们钻进地里或者平地消失啊?”
赵爱国一字一顿、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事实上都是飞向天空了。李荣夸张地哈哈大笑,好像在表演给别人看,的确有路过的别人看了他们两眼,他大声说,你果然是吹牛大王,怪不得你要看“四游记”,等你把“四游记”看完,你的牛会吹到天上去的。
赵爱国拍拍他的肩膀,我再说一个秘密你听听吧,我们学校的栀子花香气,可以提炼出一种特殊的化学武器,潜伏的外国特务最近来运了这好几次了,他开辆小轿车,每次都运走好几公斤栀子花香气,你知道怎么运的吗?他轿车排气管是可以吸气的,吸进去,储存在后备厢里,他把这些香气藏在运河对面的窑洞里,再交给接头人,他们之间用老军医广告来联系,不过,我们的侦察员最近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动向了。你注意到刚刚摆出的水果摊了吗?还有那个穿灯笼裤的“青头”,都是侦察员假扮的。赵爱国特别欢畅地挥了下手:该死的特务,已经被我们包围啦!他抡起书包,再一抡,越抡越快,直到抡成一只绿色的风车,哗地松手,书包飞到屋檐那么高——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游街!李荣拍拍他肩,喂,你正常一点,小心让老师送到青山医院去。
第七百货商店那边走过来一群年轻人,带头的几个人都戴着眼镜,他们举着横幅,白布上写着几个鲜红的大字,布很干净,初夏的阳光打在上面,像是刚刚亮起的电影屏幕。他们表情激动,嘴里喊着话,这些话赵爱国最近经常在电视新闻里听到。一个最多十八九岁的青年额头上缠了日本武士似的白布条,他举拳头,叫几句,身边的几个同伴也整齐地举起拳头跟着叫几句,他憋红了脸,眼睛因怒气而发红,赵爱国认识他身边的几个家伙,他们是技工技校和工业学校的。还有几个也许是脸皮薄,也许是怕亲戚朋友看到,低着头跟在大伙后面走,也不朝周围看。两个派出所的警察缓缓推着自行车,跟在旁边,面无表情。
街两旁原先在打麻将的、斗纸牌的、说闲话的,好像是有人吹了声哨子喊集合,几乎是同时搁下手上的活、嘴边的话,纷纷跑出门来看热闹,有个大妈吃饭吃到一半跑了出来,手里还端着个饭碗,被人挤了,摔在地上,破碎声中两块完整的红烧排骨躺在地面,她心疼地破口大骂,骂了几句泪都出来了,身边几个人见情形不对,往边上避避开;其实就一些年轻人走路,最初的兴奋劲儿过后,街上的人们也和那两个警察一样,面无表情地看着。憋红脸的青年可能是喊了大半天,嗓子喊干了,他走出队伍,去水果摊买甘蔗,讨价还价一番,等摊主削好皮,掰成几段,又跟上队伍,分给同伴们啃,他们就啃起甘蔗来,暂时顾不上喊口号,也腾不出手举拳头了。不知为什么,他经过赵爱国的时候,赵爱国觉得他的白衬衫挺好看,特别想要一件,其实自己也有白衬衫,但还是觉得他的好看,这件白衬衫与其他的白衬衫都不同,难道因为上口袋别了支钢笔?他决定回去也别支钢笔试试。
李荣说,真的,跟电影里一样。
他们的家相隔不远,和其他几幢小楼一样,身上缠着爬山虎、牵牛之类,一成不变地在树荫下趴着,相守相望,外面的新闻与它们无关,那些口号声早就被知了声挡在千里之外。门前的树影就是家吐出的舌头,轻轻地摇晃着。皮虫们也在摇晃,如果时间放慢,皮虫一根一根依次撩开,能看出风正往东南方向缓步而去。李荣忽然指着赵爱国家门口的那棵树,很认真地问,赵爱国,你知道这一棵是什么树吗?
赵爱国耐心地告诉他,这盆叫太阳花,那丛叫夜来香、万年青、大青叶、月季、葡萄,这一盆叫葱。
我问你,这棵,这棵大的,你自己家门口的叫什么树!
叫作扇叶树。
你胡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而且我刚刚问的就是这棵树,你故意乱说一通。
你看,它的叶子像小扇子,所以它就叫扇叶树。
李荣的口气忽然变得严肃了:“你都十一岁了,连家门口种的是什么树都不知道,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什么秘密,先把你自己家门口的树弄清楚,再来跟我吹你的各种秘密吧。还记得你说你爬过非洲的一棵莲花树,树上开满了莲花,结拳头一样大的莲子,你也真敢吹牛,怪不得你考试一直不及格。”
赵爱国觉得李荣的语气正式得奇怪,但没当回事。他按按书包,包里的“四游记”让他很踏实,他没搭理李荣,径直向家走去。让他说几句就说几句吧,我先忍着,等看完“四游记”后再来和他计较。他拍拍粗糙的树身,无数薄绿的“小扇子”在半空中沉默着,部分密集之处,阳光遮遮掩掩,仿佛藏了什么东西。这棵树,就长在我家门口,我凭什么不能叫它扇叶树!
媽妈做饭时做了糖醋鱼、糖番茄、红烧茄子、咸菜豆腐汤,赵爱国左手持着《北游记》,只要夹筷,洒得到处菜汁淋漓。闷头吃饭的爸爸实在看不过去,骂了两句,爸爸的骂像是提醒,赵爱国想到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具体什么事,又朦朦胧胧地想不清楚,他痛苦地拍拍脑袋,事情就像一粒嵌在大脑皮层间的黄豆那样颠出来了,他怕等下就忘掉,着急地指着门外问:“爸爸,那棵是什么树?”
赵爱国爸爸嘴里有饭,他没抬头,含糊着说,大概是泡桐树吧。妈妈在一旁补充道,就是泡桐树,一到天热就掉毛毛虫下来,回头要找人锯掉它,你快把书放下,好好吃饭。
如果爸爸说出一个其他的树名,赵爱国也许就信了,偏偏他认得泡桐树,在他认得的不多的几种树里面,泡桐树是一种,三四月间开紫花,半空中灿灿晃晃,紫杯盏簇拥相伴,半空中举办着紫色舞会,淋几场春雨,泡桐花一掉,地面像受了伤,涂了一摊摊的紫药水,春天也就结束了。门口的这棵树,绝不是泡桐,它从未开过花,到初冬,就早早掉光了叶子,剩下干黑的细枝,抓向灰灰的天色,如九阴白骨爪,就等着哪只鸟雀飞过,迅速抓牢,捏扁,塞进树身的凹坑。
一个可怕的答案正在赵爱国的脑子里形成。他放下《北游记》,也没心思管真武大帝和天、地、日、月、年、时六个妖物的斗法结果。爸爸今年四十二了,妈妈比爸爸小两岁,也有四十了,他们是返城知青,他们一直很厉害,知道肥皂快要涨价了,然后及时排队,知道找熟人开病假条,也知道如何找关系弄到一张彩电票——可他们竟然不知道家门口一棵树的名字。赵爱国心里很不好受,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为爸爸妈妈;饭菜吃进嘴里也没味道,胡乱嚼着。问题不仅仅于此,做作业时他想到和这有关的另一件事,心里更为苦闷,爸爸妈妈明明不知道树的名字,还认为自己知道正确答案,并把这个正确答案告诉自己,完全是不负责任地乱说,偏偏还那么心安理得,甚至还不如自己编的扇叶树,至少叶子像;他笔下的数学应用题也随之奇怪刻薄,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恶搞:一个水池有一条进水管和一条出水管,单开出水管40分钟可将满池水放完,单开进水管30分钟可将空池注满水,现池中有2/5的水,如果同时打开两条水管,多少分钟能满?
为了找回点安慰,睡觉前,赵爱国问了爷爷,爷爷是乌龟车司机,刚刚光荣退休,问了奶奶,奶奶退休前是第一纺织厂的挡车工。不出所料,他们也不知道家门口这棵树的名字,爷爷六十五岁,奶奶六十四岁,在弄堂里住了快五十年了——可他们不知道家门口一棵树的名字——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他们竟然没想到去了解一下家门口这棵树的名字,爷爷知道两伊战争,知道阿拉法特,知道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弄堂居委会主任的名字,可就不知道家门口、每天都看得见的、好像也应该算作知识的这棵树的名字。赵爱国最喜欢看的杂志是《飞碟探索》和《奥秘》,他画过想象中黑洞和银河系的形状,就是树轮的形状,也是石子投入水中荡起涟漪的形状;他能背出《小朋友》里的大多数故事,比如,在冬天的蒙古大草原上,牧民姐弟们如何消灭田鼠。令人羡慕的是,那些田鼠都有着集体共享的美妙地洞,里面分了好几个房间,一个房间堆着花生,另一个房间堆着麦粒和玉米粒,还有一个房间用来睡觉,他想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日子吧。他偷偷地梦想成为它们中的一只——睡在小地洞里,外面包着大地洞,再外面围着厚厚的牧草,再再外面压着暖暖的白雪——躲在俄罗斯套娃的最里面,多温暖啊。他和李荣争论白垩纪还是震旦纪离现在更远时打过两次架,他知道恐龙是被从天而降的小行星毁灭的,可李荣认为是因为地球变暖,他们都因为在黑板上画了恐龙被数学老师罚站过……可这一切现在都没了意义,因为他,他的爸爸,他的爷爷,连家门口的一棵树的名字都不知道。赵爱国想到了一句不太恰当的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好像是朱老师知道这件事后,对自己一家中肯的批评。
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窗外有连续的自行车铃响,伴着各种声势浩大的脏话,估计是隔壁弄堂的几个“青头”又跑到防空洞去聚会了。青头们喜欢戴军帽,扎武装带,骑自行车双脱手,青头们的自行车后面都坐着一个青头婆,有一次清扬公园门口车祸,撞了一对青头青头婆,青头死了,青头婆想青头,就爬印花厂的水塔往下跳……赵爱国索性爬出被窝,坐在床上,看着写字台上光滑的月光发呆,算术书的封面特别清晰,小女孩手中的地球仪开始转动,男孩手中的圆规也划出一条闪亮的弧线,他量着赤道的距离。他知道,不仅仅是一棵树的问题,弄堂里有五个同学邻居,李荣、刘丽娜、阮夕清、阮晓兵、李广,他们从小一起玩,一起上学回家,除了李荣家,其余四家他都没进去过,离得那么近,最远不超过一百米,可他从没进去过,这么近的地方都没进去过,自己还想着去北京呢!这些邻居家,爷爷奶奶应该也没去过吧,更别说爸爸妈妈了。再近一点的,隔壁的刘勇家,与自己家就是两堵墙厚度的距离,最多一米吧,可自己也不知道他家是什么样的,楼上有几个房间?刘勇住朝南还是朝北那一间,刘勇每天晚上做些什么?他有不少连环画,这些连环画是放在床底下呢,还是柜子里呢?
甚至不用那么远,就在自己脚底下,以前是个防空洞,听爷爷说过当年他们按八卦形状挖的洞,里面存着手榴弹和卡宾枪,还有几百箱的壓缩饼干,压缩饼干可以一百年不坏,每次看到院子里爬动的大蚂蚁和大西瓜虫,他就想这些是吃压缩饼干长大的蚂蚁,每次想到自己的身底下有几百箱压缩饼干,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仓库保管员。他几次向爸爸打听,何时可以进去看看,爸爸却还以讥刺的笑,恶狠狠地骂几声,说里面有个屁。爷爷奶奶的房间里有只漆黑的樟木箱子,沉默而严肃,仿佛包公的脸。他偷偷打开过几次,樟脑丸的气味冲进鼻子,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他翻到五六层,全是衣服,秋天的褂子、冬天的袄子,还有的确良衬衫和裙子,但他从来没见爷爷奶奶穿过这些衣服,难道是两个姑姑的?但她们为什么不带去新家呢?一件件衣物让自己失去了好奇,放弃探险了,可万一、万一第八第九层里有什么宝贝呢,仅仅少翻了一层,自己却失去了一个重大发现,或许箱底下有个“309暗室”呢,可以通过它走进黄金国。身上盖的被子,它是什么材料做的,来自什么地方,经过了谁的手缝制,那些绣的金色花纹是什么花,一年开几次……秘密是根本不需要编的,只要你想找它,身边平平常常的一切可以全变成秘密。
赵爱国很害怕再过二十年,再过三十年,再过五十年,他到了爷爷这个年纪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家门口的树叫什么名字,隔壁邻居家里是什么样子——这些手脚边的陌生,像人生经验大箱子底下的小孔,把他储存的知识和想象全漏光了。他悄悄起床,推开房门,踮脚走过客厅,托着锈锁打开家门,端详了一会儿那棵沐浴在月光、散发着脉脉清香的树,跳几下,又跳几下,终于揪下一片树叶,他凑着月光,手指沿叶面纹络滑动着,好像在写着自己不明所以的文字,奇异古老,比甲骨文还要神秘,充满玄机,之后,他将树叶贴近鼻端,深深吸嗅。
朱老师穿了一件灰色开司米外套,盘了发髻,金色蝴蝶发夹是上周去市里买的,五块钱两只,她和女儿一人一只。她对身上的这条裤子比较满意,蓝黑色,比较宽松,能遮腰腹,适合她的年龄,问题就在于裤脚不知何时沾上一点绿漆,用尽办法也无法洗净。想起裤脚的绿漆,她就觉得鼻子上蹲着一只苍蝇,有那么几天,她时常注意同事的眼神,凡是往她身下看的,捡支钢笔扔张废纸的,她就皱起眉头全神戒备。他们的不怀好意无比明显。
她今天的心情还可以,织了一个月的毛衣织完成了,还不错,菱形花样,目前流行款式。布置完课堂作业,朱老师翻着《针织花样100例》,有一眼没一眼扫视着教室。学生识相,安静地做着作业,几十支笔尖在纸上沙沙爬行,在她耳边下着一场细雨。灰白墙壁有几片叶影移动,天花板广阔,窗户映出数蓬树枝,对面黑板报上挂着老人家头像。目光往下移,是后排几个学生,他们的脖子弯得很温顺。赵爱国胳膊没动,头深深低下,躬着背,像要钻到课桌里去一样,本子摊开,笔半悬桌角。
“赵爱国——你在干吗,给我站好!”朱老师持起教鞭,快步到赵爱国课桌前,敲敲他的铅笔盒,你把东西交出来!李荣停下笔,紧张地看着朱老师,再看看双臂塞进课桌的赵爱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前后排同学不敢和朱老师眼神相触,整间教室弥漫着被连坐的恐慌。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在朱老师不停的催促中,赵爱国慢慢抽回手,起身站直。是一本没有封面的厚书,油渍泛黄,边角不完整,书脊处已经霉了。教鞭敲敲桌子,朱老师看赵爱国没反应,猛地一抽,直接从他手中抢了过来。她翻翻书,分明是一本《初中政治》,她惊疑极了,不敢相信地打量赵爱国,这时从书中掉下数片叶子。她没明白这几片叶子的用途,以为是书签,继续好奇地翻书,反复几次,确定这的确是一本普通的《初中政治》,满脸困惑地质询:“你作业不写,看政治书,看得懂吗?”
赵爱国知道朱老师误会了,他怕朱老师发更大的火,也不说破:“我看看玩玩的。”
“屌字不识几个,作文及格过几次?还看政治书,政治书看你差不多,赶紧做作业,要是让我知道你抄李荣答案,抄一百遍小学生守则!”朱老师怒其不争地摇摇头,觉得这学生脑子短路搭铁,也没多骂,“你给我站到下课。”
想到一个新针法,橄榄结,等下试试,好像五针能成结。她才往讲台走,身后传来一个怯怯的声音:“朱老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叶子吗?”
赵爱国举着一片树叶,瞳孔因激动而异样,神情陌生地问她:“朱老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叶子吗?“对了,还有这一片。”赵爱国又捡起一片树叶,临时起意,鼓足勇气询问,让他获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挑战权威的冲动快感。
橄榄结的针法才成形,又被赵爱国破坏了,原来的五针变成了六针、七针,脑子里的针法全乱了。“你吃屎吃昏头啦!你考我,我下乡八年,纺织厂出来的,什么人没见过,你来考我,你拎拎清楚!”不知道是生气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愤恨自己如此容易被人影响,她莫名羞怒,拎起教鞭,跑过去朝赵爱国身上横抽两记,教训过后仍不泄愤,又警告班里的学生,从今天开始,离赵爱国三尺远,不允许跟他说话!
剿工二校的操场上,暖风吹过学生追逐叫骂的身影,一小朵、一小朵的棉花虫静静悬浮,有些落到密集的树叶间,有些始终停在空中。几乎和棉花虫被孩子捉牢的速度一样快,中高年级的小朋友都知道有一个叫赵爱国的,外号叫“离他三尺远”,脑子不太正常,总喜欢拿着一片叶子或一根草问别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叶吗?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你知道这是什么草吗?施伯伯一开始还理他,但他的敷衍被赵爱国不留情面地戳穿:“你说的不对,你自己也不明白,瞎说!”后来再在下课期间见到这个孩子,他就避着走了。在朱老师布置的开放式主题作文“好人好事”中,李荣写了“借书”,内容是他一次又一次借书给赵爱国,赵爱国却在课上看课外书影响学习,所以为了赵爱国学习成绩跟上班级平均成绩,他不再借了,做好事也要“聪明”地做。作为朱老师钦点的优秀范文,李荣在课上声情并茂朗读的时候,赵爱国认真聆听,并根据朱老师的要求,抄下李荣作文中一个个好词好句“春姑娘”“书山有路勤为径”“诤友”“耳边响个炸雷也听不到”等。
两个月后的夜晚,月光抚摸着赵爱国的家,抚摸每一片瓦、每一丛檐松,窗台上晒干的鸡肫皮和橘子皮,也抚摸着铺好薄毯的床。床上空空的,台灯搁在床脚,亮出一片属于他的小世界。他蹲在地上,反复把玩着最心爱的植物标本集(一本硬面抄,十几枚树叶用透明胶带粘在其间,下角标注了树叶的名字,采集时间和地点),舍不得睡觉。银杏、槐树叶、月季、枫叶、梧桐、榆树叶、桑叶,他抚摸着这些叶子,十根手指头,每一根都长出了鼻子,闻到了遥远的青涩,说不出的充实,类似于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银杏、槐树、月季……在这样的美妙中,之前朱老师带来的委屈已经消散,不值一提,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也不值一提,当然,李荣对友情的捉弄也变得不值一提了。
在小學毕业之前,他要拥有十本这样的标本集,里面采集了世界各地的植物标本,其中一本全是侏罗纪的植物,另一本则是亚马孙雨林专集,第五本专集留给北极植物,第六本留给商周植物……家门口的那棵是什么树?自己还不知道,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搞清楚它的名字,等到暑假的时候,去问蜻蜓浜的表姐,她在北京读大学,等到暑假,她就回来了,她会坐着火车回来的;见表姐要穿上白衬衫,青裤子,衬衫口袋里别好钢笔,带好洗干净的树叶去找她;想象和表姐在葡萄架下翻看标本,讨论着那棵树的名字,他似乎就听到了暑假晴朗的蝉声,随着蝉声闪烁的葡萄叶和一颗颗的露水。
虫鸣渐歇,窗外响起奇怪的动静,似乎有人使劲地挥动蒲扇,呼呼生风。赵爱国拉开窗帘,推开窗户,运河的水腥气涌了进来,仔细闻,夜空中还有一缕植物的清香,从水腥气中分离了出来。台灯光变暗变小了,月光搂住它,仿佛担心它与夜晚格格不入,替它擦去过多的棱角。
三角尺量角器形状的屋顶上,有一只浑身发亮的大鸟,全身洁白,却长着漆黑的脑袋,它立于最高处的屋脊,不时轻拍翅膀,带起一蓬微亮的尘砾,仿佛一蓬星河,瓦楞熠熠生光,檐草缓慢地无风自动。赵爱国看得入迷,并不害怕。大鸟细足轻点,轻盈地纵身而起,一片白色瞬间跃上了浩瀚星空,心念忽转,赵爱国看到自己也到了屋顶,穿着白衬衫,别在胸口的笔盖精光锃亮,他高高仰起头,视线牢牢追踪大鸟的身影,生怕稍有疏忽就找不到它了。它在月光中继续往高处攀升,翅膀举放得特别柔软,像水母在水中舒展,借着须触的力,一纵一跃,往浅海而去……附近的漫天星星幻化成了磷虾和小鱼,它逐渐变小变小变小,那一点白如米如萤,慢慢消失,却把世界的夜晚变成了蓝色的海洋……
责任编辑.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