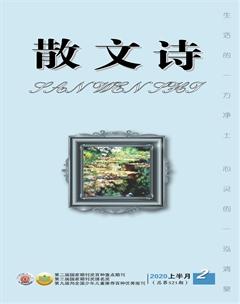窑乡纪事
2020-07-20晓弦
晓弦
刻板的砖事
在窑乡,你会发现,京砖们都站立着,紧挨着身子,像坦诚相见的哥们;
到了城里,则被放倒着,平铺直叙……这寻常的秩序。呆板的时间久了,难免会出现玩世不恭的塌陷。
这时,要将塌陷的那一块,挪一下,看身下有否爆芽的春事。慢慢扒开,周边受牵连的那些砖块。用力刨除上面根茎般青筋暴突的心事,以及凝结在上面的陈年伤痂,像逡查那些不干净的,阉人。
这不是人间的简单游戏,而是一场不经意的工事——画地为牢,抹上水泥,打上胶水,严防死守季节的苟延残喘,保持规整的形制,以及用梦幻般的橡皮榔头,轻轻叩平喘息的地平线。
沉默的瓦事
在江南,砖砌的烟囱,是稀罕的事物,上面总是顶着一块青砖。
太刻板了!我的爷爷,这乡村的泥水匠,用砖块筑成一个烟囱后,就要放下泥刀沉静片刻,像是为上帝做一场祷告,然后拿起身边那张瓦片轻轻盖上,像神谕,不让我们去触碰,那是为坚硬的生活,留出一个弧形的出口。
這细微的改变,为生活亮出好看的天窗,好让月亮在路过村庄时,弯下腰来,通过它,抚摸到堂前的神龛,以及祖先粗糙的脸,并以绒毛般淡淡的光晕作回音,好让走散的亲人,轻轻地团聚在一起。
窑墩的围城
遇见一个窑工,他说,窑乌龟!
这个砖一样坚硬的名字,曾是太爷爷的名字,这自虐的称谓,在窑乡是多么的平常!
风吹雨打的日子,窑膛是乌亮的天堂,是太爷爷的最爱!即便夜凉如水,也拼死抗衡蚁穴溃堤般的坍塌。
这清末明初的砖瓦窑,成了最接地气的文化遗产。太爷爷曾用九斗糙米盘来这个土窑,他说土窑是活气生根的祖宗,又像一个从小就缠不住小脚的大脚女人。
她是我的太奶奶,劈柴、烧饭,拾掇生活的碎瓦乱砖,蚂蚁般搬运着生活的劳顿——用时间的筹码计数,把每张砖瓦,当作火焰般优雅的儿女。日复一日,把长满萋萋杂草的窑墩,变作森严壁垒的围城。
幽默的窑工
进入窑乡,感觉每个来采风的人,都疾速地进入了白色的时光隧道。宁愿把眼前见的干窑误作千窑。
千窑!多么响亮而宏阔的名字。要是你逆着倒流的时光,随便掀开哪一座砖窑的大毡帽,里面,都埋有一颗涂抹着烟火色的巨大的心脏啊!
这样的大场景,这样的大气派,源自一块块京砖。打量,或者凝视,会像一个岁月长镜里的黑显屏,逸出窑乡淳朴而绵柔的民风。装窑,封窑,等候神祇般的吆喝。用新收的柴禾燃起第一缕火焰,迎候一摞摞带着浩荡皇气的订单,将庸常生活煨出嘉禾稻米的香来。
辽阔水乡,多情的水镇,稻秸升起的火,是世上最好的火,适合这里所有用善来命名的水。最好的火,遇到上善的水,木讷的泥巴会把自己叫醒。在京砖们或轻或重的磕碰声里,再孤寂的瓦当也会滴沥出三月的春情。
当一窑墩的砖瓦被煅烧,被封窑,像是俊逸的秀才在等待金榜题名。又像是足月的孕妇在等待黎明那缕殷红。而这时的干窑,便是一座希望之城。
这时的男窑工喜欢把女人比作瓦,这时的女窑工喜欢把男人比作砖,这时成叠的瓦,臣服于男人粗砺的手,像精美的手风琴,在空中舒展柔美的琴扇。
难怪他们愿意互相戏谑为窑乌龟,免得被坚硬的生活的棱角磕破头皮,免得被日常死寂般的单调灼伤内心。所以,理想的窑工,半是男人,半是女人,就像高耸的烟囱,与那密闭的窑膛。
这么神谕般的事物,只有在水乡,才可铸就黎明般高远而迷幻的风景。神奇的教堂
进得幽深的窑来,一眼认出,用耐火砖围砌成的窑壁,是某个反刍动物的胃。
粗陋浅显的火膛,是寻常日子的贲门,进食多了,难免会肠梗阻和胀气痛,产生生活的忧伤,与惆怅。
而耸立窑外的烟囱,是节并不柔软的十二指肠。
此刻,当我通过窑顶蒙尘的天窗,向窑膛探望,发现——这真是个黑色的教堂,那些沉默着搬运砖瓦的窑工,全是耶稣的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