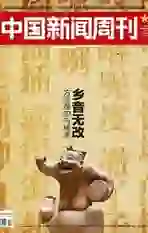贵州村民“涉恶犯罪集团”背后的墓地生意
2020-07-13黄孝光

一束白幡代表着一座坟墓,构成大方县林间的“坟山”盛景。摄影/本刊记者 黄孝光
森林覆盖率接近60%的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曾获评“中国最美风景县贵州十佳”。不过,如今在大方县的部分青山中,漫山遍野的墓地成为无法忽视的“一景”。
5月末,两起涉恶案件的宣判,打破了大方县的平静——来自九层衙村滥泥组的30位村民和红星村黄河组的10位村民,因为阻止他人埋坟而被判刑。
发生在九层衙村滥泥组的这起案件,于今年5月18日一审宣判,30位村民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涉恶犯罪集团”。被判刑村民中,60岁以上的有11人,其中年龄最大者已79岁。
“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04年时任滥泥组小组长段永全通过村委承包了滥泥组的荒山,之后多次把承包的荒山转让给别人建坟;村民不服,认为荒山是集体的,便纠集多人,通过堵坟来谋取利益。”大方县人民法院办案法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滥泥组30个村民在2011年到2018年期间,趁外村人到村中荒山安葬死者之机,实施了14次敲诈勒索,累计获利约14万元。
滥泥组村民的堵坟行动持续了7年之久。宣判后,部分被告人家属提起上诉。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堵坟事件背后的利益交织,远比判决书呈现得纷繁复杂。
坟头上的交锋
大方县至今没有火葬场。
该县民政局局长张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因为群众举报、环保督察等原因,大方县火葬场选址变更多次,历时多年至今尚未建成。因不具备火葬条件,当地仍然实行土葬,县城或周边缺乏土葬条件者,纷纷将墓址选在大方县的大山中,距离县城不远的九层衙村尤其受到青睐。
“外人”纷纷来村里下葬,成了当地村民堵坟的源头。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埋坟是看好时间的,过了时间不能下葬,会被认为非常不吉利。滥泥组村民就抓住逝者家属的这个心理,要求对方必须拿钱才能下葬。”大方县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表示,这些村民从一开始便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从巡山、堵坟、议价到记账,均有专人负责;他们还购买了摄像机、录音笔等作案工具。
一审法院287页的判决书,详细还原了滥泥组村民堵坟时的激烈场面。外村人彭兴华曾花费8600元向九层衙村大坪组村民购买了两个坟地。2011年12月16日,彭兴华在荒山安葬其母时遇阻,滥泥组村民坚称,埋坟所在地属于滥泥组而非大坪组的地盘。彭兴华家属一度跪地求饶,直到大坪组向滥泥组交出8600元才得以下葬。根据滥泥组村民张明军的记录,事后参与堵坟人员每人分得100元或200元的“误工费”,剩余钱款则用来购买了一台摄像机,供今后堵坟时取证使用。
这是滥泥组村民的首例堵坟行动。判决书记载,他们在分钱时达成一致意见:“荒山是集体的而非段永全(村小组长)的,段永全卖地给别人,大家没有分得钱,应团结起来去阻攔。”
几乎每次堵坟都会酿成暴力冲突,当地派出所为此频频出警,居中调停。2011年末,第二起堵坟事件发生,因为被堵坟地是段永全所售,段永全一方也到了现场。混乱中,段永全儿媳张莉打伤了参与堵坟的村民李平。后经法院判决,段永全家赔偿了李平3000多元医药费。大方县公安局对张莉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
“他们连公安局的人都敢敲诈。”一位买坟者在证词中提道。多名公职人员也出现在村民的堵坟名单中,例如原大方县看守所所长王某忠、原大方县城市管理局局长何某涛、原大方县供电局局长尚某生、原大方县城乡环境保护局局长郑某才等。判决书提到,郑某才生前在滥泥组荒山修建了活人墓,因担心死后不能顺利下葬,曾主动请村民吃饭并缴纳12800元。
滥泥组村民的堵坟行动持续了7年之久,最终在刘兴君事件中“出事”,继而引发牢狱之灾。刘兴君家在滥泥组的坟地,是段永全父亲段友明所赠。“他们专挑下葬的时候来堵。”刘兴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我母亲过世埋葬在那里,没有人过问;4年后我在母亲坟墓旁边修建父亲的坟墓,同样没有人阻拦;直到2018年6月我父亲去世要下葬,村民才不准我们下葬。”
刘兴君表示,村民以其埋坟地点占用了滥泥组集体荒山为由,索要12800元。当时,有村民跳入坟井,撕扯过程中意外受伤,矛盾进一步激化。后来,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协调,几名逝者家属也下跪求情了,但仍无济于事。判决书显示,参与堵坟的村民段习友辩称,村民是在打架时被推入坟井而非主动跳下去:“我们认为刘家过分了,所以不管他们给多少钱,我们都不同意下葬。”
错过吉时的刘兴君,后来向段永全之子段勇租了一块临时场地放置棺木,租金每月2000元,看管费每天500元,至今未能将其父亲正式下葬。事后,他向办案机关举报参与堵坟的村民,认为村民是实施敲诈勒索的黑恶势力。警方介入后,于2019年将参与堵坟的30名村民分批带走调查。
今年5月,大方县法院经开庭审理,将涉案村民认定为“涉恶犯罪集团”,将其区分为首要成员、重要成员和一般成员,并以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判处30位村民1年6个月至8年6个月不等的刑罚。
就在滥泥组村民涉恶案宣判后的第三天,红星村黄河组村民涉恶案也开庭了,黄河组10个村民同样因堵坟犯敲诈勒索罪,而被判刑。
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当地已对此案进行了宣传报道:“段习友等犯罪嫌疑人长期在大方城郊一定区域内利用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群众,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村干部的墓地生意
九层衙村位于大方县城东南面约5公里处,下辖滥泥组、水坝组等8个村小组。官方资料介绍,九层衙村2000年退耕还林1100亩,实施“天保”工程461亩,森林覆盖面积达90%以上;村中有两座人工水库,是县城的重要水源地,能够满足全县全年的饮水需求。
进入九层衙村地界,沿途坟墓随处可见,随机走入一条林间小道,总能看到梯田式分布的坟山。站在高处望去,山间飘扬着无数白幡,那是各家扫墓时挂上去的。“秋天叶落后更加壮观,漫山遍野都是裸露在外的坟墓,天色一黑小孩就不敢出门了。”滥泥组村民张明祥说。
一位在大坪组购买了坟地的大方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九层衙村除了“风水好”、离县城近,荒山也比较多,于是成为当地人建坟的热选之地。
据张明祥了解,过去大方县人相中某块坟地时,“送一条烟、一瓶酒或一包白糖就能搞定,不会有人过问”。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伴随坟地资源的减少,死者下葬也面临“人多地少”的窘境,坟地逐渐由赠送演化为金钱交易。而今坟市水涨船高,单座坟地价格已从21世纪初的两三千元涨至8000元以上。
因为有利可图,前述被判刑的滥泥组村民中,亦有人在自家林地卖坟。张明祥对此并不讳言,不过他强调,在九层衙村卖坟一事上,占大头的是村干部。
2000年9月,时任陇公村水坝组(现九层衙村水坝组)组长的陈生明,联合陇公村大坪组组长吴清友和大坪组村民吴清连向陇公村村委承包了250亩荒山,承包期限为50年,承包费用为一次性支付3750元。2004年6月,时任陇公村村主任的陈生明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将滥泥组150亩的荒山出让给滥泥组小组长段永全及其子段勇,出让年限为50年,出让价格为3000元。两份《荒山承包合同》均载明,若有人需在承包区域内葬坟,须经甲方和乙方的协商同意。
“正常承包的话,通常是植树造林,或种植天麻一类的经济作物,但他们没有造林,只是造坟。”水坝组组长先芝云表示。相关资料显示,陈生明和段永全各自承包荒山后,都有过倒卖坟地之举。两组村民指控称,陈、段二人所卖坟地均有300多座,获利超百万元。
段勇向《中国新闻周刊》否认了这一说法:“我家卖的只有六七十座,而且我们卖得早,当时一座坟地价格在1000元上下。”
一审判决认定被滥泥组村民“敲诈勒索”的买坟者,多数都是通过段永全家购买的坟地,段勇向记者承认了这点。“要买坟地的人,有的和村委谈,有的也会直接找到我们,跟我们讲好了,再去村委办手续。”段勇说。在具体的流程上,通常由村委会充当甲方同买坟者签订“坟地转让协议书”,并收取数百元不等的转让手续费;荒山承包人则按照坟地市场价,向买坟者收取“林木损失费”并开具收条。
九层衙村的山林里,目前到底有多少墓地?官民说法并不一致。

坐落在大方县水坝组荒山的“孙家坟”,是九层衙村最大的坟墓,占地面积近4亩。摄影/本刊记者 黄孝光
一年之前,民政部、公安部等12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违建墓地情况摸排行动,在此背景下,大方县把整治违规乱建坟墓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在去年5月排查出96座私建硬化大墓、1422座活人墓和224处坟石打造点;其中,九层衙村濫泥组的问题较为突出,被排查出坟墓154冢202座。
今年6月初,大方县殡葬管理局、森林公安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荒山承包人段勇带领下,又做了一次坟墓清点工作。不过6月这一轮统计的结果,据段勇介绍,“只有六七十座”。
滥泥组村民自发的统计结果则大相径庭。他们对该组荒山中的坟地进行逐一拍摄,并记录其建坟立碑时间。经村民统计,荒山共有317座坟墓,其中于2011年之后兴建的坟墓有167座,包括活人墓69座和未立碑的新基36个。
村民抗争十余年
水坝组和滥泥组的村民认为陈生明、段永全等人承包荒山、倒卖墓地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集体利益,于是相继走上了漫长的维权道路。
“村干部承包集体荒山,是在大多数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操作的。”滥泥组村民张明祥说,被承包后的荒山坟墓越来越多,引起村民的警觉和跟踪调查,后来发现承包环节上存在不少蹊跷之处。
2006年,贵州省政府发布《关于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林地流转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经与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依法完善或补签林地承包合同,发换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证。”在此背景下,陈生明和段永全等人均于2007年办理了林权证。
但村民认为段永全的林权证存在“作弊”。滥泥组村民张晓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办理林权证过程中,村干部在《羊场镇陇公村林改方案》《林权登记申请表》等多份文件上涉嫌伪造村民的签字。以段永全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为例,表中“接界人签名处”一栏有村民李堂明、段永祥等人的签字,然而李堂明早在1990年便已去世;双眼失明的段永祥亦向记者表示,他对林权登记一事并不知情。
段勇则回应称:“承包荒山不需要他们知道,只要村委会知道就行,我们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
大量被卖墓地,分布于村里水源地附近,也引发村民的反对。宋家沟水库是大方县的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库周围坟地密布。水坝组现任小组长先芝云搜集的坟地转让协议书中,有些明确写到建坟用地位于宋家沟水库边。对此,水坝组和滥泥组的村民均曾向有关部门举报称,村干部陈生明和段永全的大批量倒卖坟地,不仅破坏了林区生态,更是污染了当地的饮用水源。
被告人段习友的辩护律师李爱军提到,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大方县殡葬管理办法》均明确规定,禁止在林地、耕地、饮用水源保护区、水库周围等区域建筑坟墓。
对此质疑,大方县环保局一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应称,2017年《毕节市饮用水源保护条例》明确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葬坟这一规定;大方县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宋家沟水库水质进行监测,截至目前,水质能达到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至于破坏林地的说法,大方县林业局局长彭良信对记者称:“建坟其实就是挖个坑把棺材放进去,坟上还要种植草皮。坟地变成绿地,植被得到恢复,不会造成明显破坏。”
过去十年来,滥泥组村民持续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段永全非法承包山地、私卖坟地等行为,并提出撤销林权证将荒山归还集体、追究村干部倒卖坟地责任两大诉求。
2011年6月23日,滥泥组村民首度获得正面回应:大方县林业局、羊场镇政府在信访答复中,认为段永全对该村集体山林的使用权是合法的,但认定段永全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毁林葬坟属于违法行为,并对其从2009年到2011年5月卖出的12冢坟地处以林业行政罚款2400元,并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这次处罚之后,村民开始采取堵坟行动,并继续向市一级上访。2012年4月14日,大方县林业局和羊场镇政府再次组成调查组重新调查,并作出新的答复:根据段永全指认,对其承包荒山内的坟墓进行清点丈量,共有坟墓、新基113冢;处于追诉时效内的有30冢,其中12冢之前已作处理,剩余的18冢,每冢占用林地30平方米,总占用540平方米,对陇公村委会和段永全处罚10800元。
此外,大方县政府在2012年12月7日对滥泥组村民作出的信访复查答复,对滥泥组荒山承包问题作出了新的认定:争议荒山于1988年由段永全承包,到期后于2004年再次承包,两次承包均未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承包协议为无效协议。基于此,大方县政府要求县林业局,依法向县政府提出撤销段永全等人的林权证,将争议的荒山使用权确权给村民小组经营管理。
收到这一答复意见后,滥泥组村民频繁到省、市、县三级政府上访,要求执行县政府的信访复查答复意见,未料这一答复意见后来被大方县政府推翻了。
相关文件显示,2013年10月21日,大方县信访局、林业局、司法局和羊场镇联合向时任副县长章育做汇报:“经反复斟酌,如按县政府的答复意见执行,不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如按此答复意见执行,在全县涉及荒山承包的类似事件可能会引起连锁反映。”“建议重新作出复查意见答复信访,处理建议为由羊场政府引导群众走诉讼程序维权。”该报告得到了章育的签字同意。
县政府的意见出现“反复”后,滥泥组村民此后走上诉讼维权之路。
2014年6月,滥泥组村民张明军、段习友等11人联合起诉陇公村村委会和段永全、段勇,请求判决村委会与段永全父子签订的荒山使用权协议无效,法院以该纠纷应由政府处理为由驳回;此案二审、再审均维持了原裁定。2018年11月,滥泥组村民转而起诉大方县政府,要求县政府撤销向第三人段永全、段勇颁发的林权证;法院以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为由,驳回了起诉。村民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再次上诉没有结果时,村民就因为“涉恶”被抓。
2019年1月至3月,参与堵坟的30个滥泥组村民分四批被公安部门逮捕归案。
根据大方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8日向涉案村民下发的《延长审查起诉期限通知书》,村民涉嫌罪名经历了从寻衅滋事到敲诈勒索的变更。记者就罪名变更缘由咨询大方县公安局一名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涉恶案件在终审判决之前,不便对案情进行介绍。
“聽法院同志介绍完案情,我心里五味杂陈。涉案村民有60多岁的,也有快80岁的,他们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严厉惩处了这批恶势力,也是正当其时。”采访末尾,大方县副县长周登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为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待案件终审判决后,政府将在全县范围内继续加强普法宣传。
大方县的殡葬改革也在推进中,火葬场建设已经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