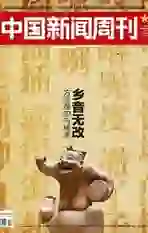语言学家刘丹青:方言是一种思维方式
2020-07-13杜玮
杜玮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刘丹青。图/受访者提供
刘丹青的父母是江苏无锡人,他在苏州吴江区度过了中小学时光,“文革”期间曾辗转于上海的亲戚家。十多岁时,刘丹青就学会了无锡话、吴江话、苏州话、上海话等四种方言,并隐隐觉得几种方言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1977年考上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刘丹青开始致力于方言的研究。身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对60多年来汉语方言生存境况的起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每一种方言都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感知和体验世界的独特视角,意味着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在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73%、大城市普及率已超90%的今天,他认为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日前,在位于北京东二环内的办公室里,刘丹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语言自豪感不足是方言危机的一大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你成长过程中语言环境是怎样的?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历经了怎样的转变?
刘丹青:我算是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即便在这样的地方,我小时候上学时几乎没有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这样,普通话只存在于语文课和一些文艺演出、诗朗诵之间。平时,老师们用各种不同口音的方言上课,大部分是吴语地区的方言,只有一些外地来的老师,会用普通话或者带有官话方言色彩的普通话上课。在校外,无论是孩子们之间,还是大人和孩子间,都说方言。如果一个外地人平日里说普通话,会被本地人视为一件奇怪的事情。那时候是一个方言盛行,而普通话推广不足的一个阶段。
1977年,我考上蘇州大学中文系,两个班共108名学生。除了1名从苏北地区移居苏州的同学说官话,其他同学都说吴语。我和同学之间交流用两种方言,一种是吴江话,一种是苏州话,因为苏州话比较容易懂,当时也是强势方言。
推广普通话在中国从1956年起开始实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推普初期政府行为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作用,尤其是电视普及后,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大。电视的普及使得普通话每天萦绕在大众耳边,收看电视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家家户户每晚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电视当时是新媒体,这一传播媒介的到来,对于中国普通话的普及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印象中,什么时候方言出现了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刘丹青:普通话的大普及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媒体的丰富使得推普有了加速度。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形态发生的重要变化。原来中国经济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因此经济生活的区域性比较强。改革开放及后来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各省乃至各国之间的这种区域性被打破,再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务工者大范围的流动,都对方言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方言出现式微的因素是多重的。
到了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通过,这是我们国家语言文字领域一个根本性的纲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非常重要,同时也赋予了普通话更大的影响力。但如果没能把握好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传承方言两者间的关系,就会出现过分压抑方言的情况。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不少方言面临的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哪些方言出现了危机,方言出现危机的表现有哪些?
刘丹青:方言生存现状的差异比较大,像粤语比较强势,在当地人中间认同感也比较高。而且,在广东韶关等非粤语区,粤语也在使用,它的强势远超过其他方言。这当中有个语言自豪感问题,我感觉到广州人的语言自豪感很强,上海人的语言自豪感属于中等偏上,南京、福州等城市,当地人的语言自豪感就不太强,具体什么原因我没有研究清楚。
我在南京媒体上做节目的时候,有观众问,我们南京话不好听怎么办?南京话在明清时期曾是一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标准语言,还是南系官话的代表,但什么时候南京人语言自豪感开始下降的,我没有专门研究。同时据我了解,福州人也不认为自己的方言很强。在泉州和厦门这些闽南语区,闽南话相对强势,而福州虽为福建的省会城市,但属于闽东方言的福州话却没能赢得很多人的心。
语言自豪感的强弱实际上会影响到语言或者说方言的保护程度。语言自豪感不强的方言,丢失起来更容易。联合国关于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的评价系统里面有好多项参数,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人们对于母语的态度。
另一个方言出现危机的重要表现,也是重要原因,就是使用环境的萎缩。以我的家乡吴江为例,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比例差不多是1:1,而本地人口中包含了很多老弱病幼,而外来人口大部分是青壮年,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你绝大多数打交道的青年人都是外地人,交流需要用普通话,这就使得方言的使用环境大大减少。
现在的小孩子一到入园年龄就会被送入幼儿园,家长自己带的情况比较少,在公共教育机构都是通行普通话。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从幼儿园开始到长大参加工作,都很少有使用方言的环境。
同龄人交际是母语习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同龄人交际的环境被限制在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那么他在成长过程中,用自己的方言来进行交际的能力和习惯都会降低。因此他慢慢形成非常自发地优先用普通话交际,方言的使用动机不强,最后的结果就是方言越来越萎缩,这是这些年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陕西方言版话剧《白鹿原》吸引观众。图/视觉中国
方言需要传承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国家关于方言保护的政策是怎样的?
刘丹青:十多年前开始,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就提出了语言资源的保护。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过去,方言被很多人视为是阻碍国家发展、阻碍普通话推广的因素,负面视角多一些,提出语言资源概念以后,就意味着所有的语言方言一定程度上都是资源,都有它的文化积淀、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当时就设立了一些项目,开展了语言资源的调查,我承担了语法调查项目标准的设计。
2015年开展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把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结合起来。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些省份比如湖南还得到了民间力量的支持。
真正把方言列为保护的对象,应该是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这份文件里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这里面最重要的词就是传承,保护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有些人就把它记录下来,也就算一种保护,但记录下来如果没有传承,它最终就只是成为一个档案里的东西,那么作为一种语言来说,它可能就消亡了。
所以现在提出来的传承,就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把方言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提法,表明国家看到了很多方言所处的弱势。

2013年6月12日,海南儋州市,村民们在海边展示“儋州调声”,庆贺节日。儋州调声是海南儋州市民间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方言保护和传承的收效如何?
刘丹青:我觉得收效重要的一点是在观念上面,大家不再只看到方言的负面因素,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要珍惜的对象。这个影响不仅局限在从业人员中间,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观念也开始在改变。
各地也开展了一些保护方言的活动,比如电视台里面招募方言发言人,有一些地方举行英语、普通话、方言的三语比赛,这些都把方言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增强人们对于方言的认同意识。不过,这些举措的作用也不能估计得太高。因为方言发展困境里有很多客观因素已无法改变,比如年轻人缺少使用方言的动力,使用方言的机会也少。
方言提供一种看待事物、感受世界的独特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我们要保护方言,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儿?
刘丹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世纪,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就一直非常注重保护各地濒危的语言。它有一个核心观点:每一种语言实际上也包括每一种方言,它都形成了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套独特视角,从表述方式、用词等方面都可以得到体现。当这种语言丢失,这种视角也就会没有。
比如说在一些地区生活的人们,对某些现象观察得特别细,对某些事物也分类特别细,对植物、动物、生态、地貌、气候都有独特的描写,每种语言侧重点都不一样,就像物种一样宝贵,这是语言和方言很重要的价值。
中国新闻周刊:可以以你熟悉的方言举一个例子吗?
刘丹青:比如说稻子,在英语里面,从田里的稻子、到烧在锅里的米、生米做成的饭,都只有rice这个词。因为稻米文化不是他们的重要的东西,但是对江南人来说,稻米非常重要,所以有谷、米、饭、粥等不同的字来指代不同形态的米。
吴语饮食文化中有个字叫粞,指介于完整米粒和米粉中间不同程度的碎米,只有在稻米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才有这个概念,专门来指称这一类的东西。立夏时,江南人会制作一种节令食品,以金花菜和粞为原材料,叫“摊粞”。
还有“粉”和“面”的区别,北方把碾成碎末状的东西都叫面,因为北方是以小麦文化为原型,“面”最初是指麦子的细末,进而引申出胡椒面、辣椒面等词语,而在南方相应地都叫胡椒粉、辣椒粉。
“粉”这个字是米字旁的,它是以米粉作为一个原型来拓展它的抽象的。“粉”就是指将大米碾成粉末以后的状态,从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来讲,粉字就是一个米字右边一个分,把米粉无限分下去就变成了粉。所以方言都代表着一种思维和文化。南北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我们现在“面粉”这个特殊的词,同时也形成了胡椒面、胡椒粉这些并存的一些状况。
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有这么多方言,哪些方言需要保护?该如何保护?
刘丹青:中國的方言非常多。实际上,从客观上来说,可能也做不到让每一种方言都能完全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实际上就是少做一些推动方言更快消失的事情,让它在自然状态下能够生存,以及创造一些条件让它生存得更好一些。但我们不可能为了保护方言而在其他方面做出更大的牺牲,甚至影响到普通话的推广。你要知道,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当地居民普通话水平的低弱,也是他们脱贫致富道路上的一个阻碍。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2018年9月湖南长沙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也提到语言保护工作的差别化政策,这点怎么理解?
刘丹青:我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对普通话普及还不那么好的地方,还应该继续推广普通话,但对于大部分城市地区,尤其是中东部的这些沿海地区,年轻人说普通话已经不存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把方言保护列到更加重要的议程上来。
中国新闻周刊:该如何解决方言代际传承面临的困难?具体该如何传承方言?
刘丹青:一点就是鼓励家庭内说方言,而学校层面可以从幼儿园开始,上课用普通话,下课后老师可以跟孩子之间用方言交流。普通话这种通用语言的地位不能削弱。
另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养成方言文明使用的习惯,我指的是在使用方言时,要有一种对他人关注、照顾的心理意识。比如说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来自吴语区的,另一个北方人听不懂吴语,那么就不能三个人大谈吴语,把另一个人晾在一边。中间可以穿插一些吴语,并且给不懂吴语的人解释说明,这样也会使得对方对于方言的认同感会增强,不会出现对方言过分排斥的情况,形成一种宽松的方言使用氛围。

2016年6月14日,海南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89岁的老船长卢业发介绍《更路簿》和罗盘的使用方法。《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开发和经营西、南、中沙群岛的过程中,用海南方言写成,利用文字和地图的方式描绘出的航海手册。摄影/本刊记者 骆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