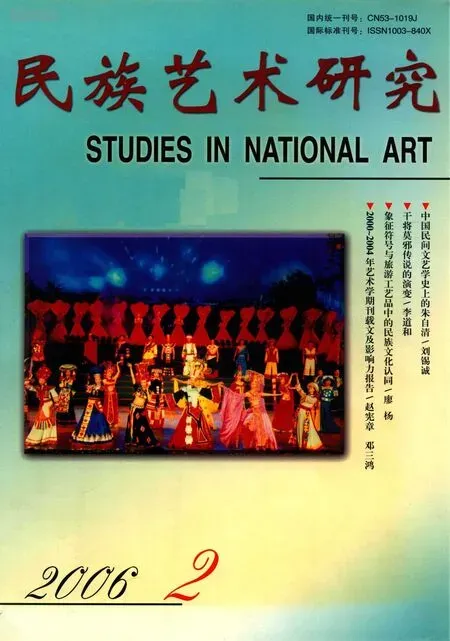2019年中国艺术学理论热点现象述评
2020-07-13郭必恒
郭必恒
经过近10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另辟蹊径设立的艺术学理论,在争议与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的境况下,初步站稳了脚跟。主要表现在:学科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学术争鸣日趋频繁热烈,研究渐趋深入细化,而且学科边界的扩展也有效地纳入了新的“地盘”,学科基础更加扎实了。回顾2019年的中国艺术学理论热点现象,可以看到其在平稳向前的总态势下,涌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趋于艺术学理论开放性发展共识中的求同存异
“艺术学理论”之所以被命名,从而区别于“艺术理论”,其实是与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特殊考虑有关的。在我国现代人文学科建立的过程中,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先后经历了几次繁荣,进而衍生出较为成熟的学术体系,艺术理论与之相比则滞后得多。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传统社会中的“术艺”认知,更重视艺术实践的技巧方面。历史上由于艺术理论的长期不发达,故而多向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借鉴甚或直接搬用和套用,一直处于从属之位,奋力紧追下仍难望其项背。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实践的蓬勃之势带动艺术理论直趋向前、快速进步,于是独立发展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艺术理论在文艺理论的统摄下浸淫日久,难免总是被尴尬地归类于文艺理论。以 “艺术学理论”命名一级学科(而非“艺术理论”),显然有助于彰显学科之新意和独立之决心。只是,艺术学理论从诞生之时起,在短短不到10年里,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云集于此,各种不同观点汇集一堂,喧哗骚动,造成共识难觅的局面。
在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边界上,2019年有别于此前的显著变化是:呼吁学科开放的声音突然增强,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仍有少数学者坚持所谓有别于门类艺术学的 “纯粹性”,但这种观点到了今日已经日渐式微。当然,在主张学科开放性发展的主流意见之中,仍然夹杂着反对声音,我们将这一现象概括为“趋于艺术学理论开放性发展共识中的求同存异”。我们既应欣慰于争执良久的开放发展与闭环发展终于有了趋同共识,但是也该看到在学科内部仍存在着不同意见。未来的取向和路径,仍值得观察和思考。
主张艺术学理论开放发展的学理依据在于关于艺术自身认识的漫长曲折的转变。王一川教授在《构建中国式艺术理论的若干思考》中提出,关于艺术的定义从古至今有巨大差异,“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艺术即模仿、美的艺术定义、艺术即无意识升华、艺术即直觉、艺术无法定义等观点……当前仍然存在以艺术为尊、开放性和分类性等艺术定义路径。”①王一川:《构建中国式艺术理论的若干思考》,《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8期,第4页。在此文中,作者还详细地阐述了艺术理论自身的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就中国艺术理论史而言,深受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影响,显然是多样化的存在形态,而非定于一尊。就西方艺术理论史而言,至少经历了达七次的学科转向,即古希腊人学转向、中世纪神学转向、启蒙运动时期美学转向、心理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社会学转向、经济学转向。在不同的时期,艺术的认识与主流的思潮息息相关,而非在纯艺术的真空中运行,这也恰恰决定了艺术理论复杂的学科背景和纷繁的学术体系,因此也不能独尊其中的一极而断然否定其他。例如,从美学角度来看,艺术理论应为纯精神或偏精神的;然而,从社会学角度看来,艺术无疑是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而已。“今天的艺术理论假如只要求仅仅依托某一背景学科去发展,无疑不现实。今天的艺术理论所需要的,或许是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视角,例如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视角。”②王一川:《构建中国式艺术理论的若干思考》,《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8期,第9页。
历史上关于艺术定义的变迁实质上也拓开了艺术理论的路向,向着人文的、精神的多个领域延伸了自己的触角。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前,艺术概念的演变仍然是遵循一定的确定性思路的,无论是模仿论、美艺论,还是直觉论等,都确认了艺术的中心位和基石点,然后围绕中心打通四围的通道,进而组织起一套具有逻辑性的要素,形成了理论的体系。不幸的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艺术的中心位和基石点不再被承认,失去了中心之后,冀望建筑在虚空中的艺术理论大厦显得与艺术总体实践层面格格不入。艺术变成了不可精确定义的对象,任何给艺术下精确定义的努力,都有违于艺术的实存景象,有悖于当代艺术实践的开放性局面。艺术的定义不再是框定艺术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核心,而是认识和阐明艺术性质及其他相关因素的一个步骤而已。当代的观念艺术、实验艺术、录像艺术等新艺术试验,都昭彰着一个艺术多样化生态的时代业已来临。在艺术家自身还处于懵懂之际,其实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学者都介入新艺术实践的理论概括之中,于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艺术场域理论”、美国哲学家丹托(Arthur C.Danto)的“艺术界理论”等,成为解读当代艺术的金钥匙。再加上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冲击,艺术理论已然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森林形态。在这样的时代,寻找大一统式的艺术理论明显是不太可能的。艺术理论当然仍有重大的价值和显性意义,正在于通过对艺术现象和艺术品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和阐释,从而开掘出艺术生态的新天地、新境界。
如此,则总是囿于门派之间,强行框范艺术理论的路径,总归是弊大于利。而艺术学理论可能也必然要面对新艺术形式的拷问,并努力回应挑战。周星教授认为,面对和回应深刻而剧烈变化着的新艺术形式,是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重大的、核心的问题。他提出,当下学科内部应该反思一个问题,即“艺术学理论如何面对艺术急剧变化的形式,对于不断出现的新的艺术形式判定衡量的问题。”③周星:《中国视角与当代价值——关于艺术学理论认知相关问题的思考》,《艺术工作》2019年第6期,第7页。为了能够切入当代艺术的实际,而不是拘泥于古典艺术理论的范式,处处以“经典”自居而动辄否定新的理论思路和理论阐释,便需要跳出既往的体系,积极拥抱新的经验以及由新的经验而唤醒的新思想。这就要求有开放的心胸和允许试验的态度,而不是急于否定对方和封闭大门。周星教授认为:“对于新的艺术形态构成艺术表现的业态,需要观念跟进,也需要艺术理论与时俱进的认识。”①周星:《中国视角与当代价值——关于艺术学理论认知相关问题的思考》,《艺术工作》2019年第6期,第7页。
其实,之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界力主艺术学理论开放性发展的呼声,也是有直接原因的,那便是颇高的研究生论文外审否定频率,几乎每个高校对此都有怨言。而否定研究生论文的很大原因,便是有学者认为其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论文,而应该归类于门类艺术学。很多学者呼吁艺术学理论的宽容或开放,暗中也是为了缓解这种每逢论文外审便提心吊胆的紧绷态势。只不过是点到未说破而已。彭锋教授直言:“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有人会认为,有些研究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有些研究是针对一般规律的;有些研究是针对单个门类艺术的,有些研究是针对多个门类艺术的。研究具体问题的不能归入研究一般规律之列;研究单个门类的,不能归入研究多个门类之列。这种划分过于武断,尤其是在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都未能出台的情况下,任何对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的划分都是临时的,需要特别慎重对待。在我看来,既然目前只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我们还是不做进一步的划分为好。只要是理论研究、撰写论文,就都可以归入艺术学理论之列。”②彭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问题与出路:从身份认同到开放包容》,《艺术百家》2019年第2期,第23页。他的提法够直接,够明确,说出了众多学界同仁的心里话。
二、艺术学理论内部的“显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
就在艺术学理论内部关于艺术理论的普适性与门类性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些借由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而确定身份的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却在一片混沌中获得了发展良机,并大有斩获。若论现阶段艺术学理论内部的各二级学科的火热程度,首推艺术教育学,接着是艺术管理学,还有艺术人类学等。这直观地从每年的论文发表的数量上反映出来。在“中国知网”,2019年 “艺术教育”的论文发表量是2820篇(不含音乐专业教育2662篇、美术专业教育2856篇),涉及学前、小学、中学、高校各个学段,也涉及成人和社区等广泛领域,真可谓蔚为大观。而与之相比, “艺术学理论”的论文量不及“艺术教育”的13%,为348篇(不含音乐理论791篇、美术理论133篇)。同样, “艺术管理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年均论文数量也多于“艺术学理论”。
艺术人类学、艺术管理学、艺术教育学都有专门的、组织力很强的协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于2006年,是民政部批准成立、国务院备案、原文化部直管的国家一级学会,该学会每年都举办大型年会。艺术管理学依托的学会有“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筹)”,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演艺工作委员会也参与其中。而艺术教育所涉的组织机构则更为庞大,不仅有政府层级的艺术教育司、处等,也有不少社会组织,还有多种多样的学会等学术组织、教学组织,等等。由于有强烈的社会需求,以及多层级、多样态的组织机构的推动,因此,这些二级学科的快速崛起并不令人意外。除以上三个特别显性和活跃的二级学科之外,诸如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传播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民俗学、环境艺术学,等等,也都纷纷涌现,并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些交叉学科或应用学科的显现、扩展和壮大,正与艺术学理论设置的初衷一致,也恰恰说明了当初学界同仁冀望积聚各方力量的选择是明智的。回看21世纪一〇年代初,在艺术学理论设立之始,学界起草并获得教育部正式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艺术学理论》,更深觉其洞见之眼光。在文中提出了五个学科方向,即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跨学科研究。在“艺术跨学科研究”学科方向上,特意强调了所谓“跨学科”的含义,就直接指明交叉型和应用型的。文中提道:“艺术跨学科是指在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交叉思考,体现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并借助其他学科思考艺术自身的规律性问题,或者体现艺术的应用属性。艺术跨学科研究可根据各培界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本学科的基本特点进行设置。”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页。近年来在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构成中,增添的新生血液往往也都是来自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艺术学作为一个门类,与其他的周边学科进行交流和互动时,艺术学理论无疑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和恰当落脚点。这一方面是由于艺术学理论所涵盖的外延是总体艺术学,而非局限于特定的具体艺术类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艺术学理论的规律性和一般性契合了其他学科的理性思维特征,故而导致了当下汇集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二级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风起云涌现象的出现。
艺术教育因进入21世纪以来艺术领域的繁荣而广受重视,所以形成了趋之若鹜的百舸争流之局。在艺术教育行业里,更多的是注重艺术技能的教学,而与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探究与商业性极强的艺术教学技法总结相比,要黯淡不少。但是,即便是艺术教育理论在其所处的领域中不受重视,仍能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讨,远多于艺术学理论的其他二级学科。艺术教育学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吸引了一些学者投身其中,他们往往都是来自教育学领域,其擅长某一个类型的艺术,因此将教育与艺术结合起来,产生了初步的成果。近20年来,艺术教育学的从业人员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业者来自艺术行业,他们在艺术教学中深感教育思想的缺乏带来的浮泛,于是主动向教育学靠拢,将教育学成果结合到艺术行业中来,形成了实践经验浓厚的艺术教育学新风貌。例如,首都师范大学在2018年底召开的“当代美育、艺术教育的观念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从主题上分析,便是将艺术教育理论与具体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在2019年第2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当代美育、艺术教育的观念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综述》中,记述了不少来自艺术教育一线工作者的见解。文章认为,当代艺术教育存在着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结合不够好的问题,为此,一方面应认真研究中华美育精神,将之作为深化当代艺术教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须直面当代艺术教育的现实,包括当代艺术本身的转换实践及其艺术教育功能的迁移。
2019年艺术教育领域的会议层出不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类型:一是政府艺术教育工作会,不时会有国家层面和地方省市层面的艺术教育会议举办;二是学校艺术教育研讨会,由于我国在校学生数量庞大,而且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教师人数也多,因此这一类型的会议最多;三是社会机构艺术教育推广会,近年我国社会机构对于艺术教育的商业投资越发加码,他们举办艺术教育大会,目标更多是推广宣传自身的品牌。
艺术在信息化时代的宽领域渗透和强应用定位,促使艺术行业之内海量的职业蓬勃兴起,不仅是艺术实操,而且与之紧密关联的联络、经纪、运作等艺术管理层面的职业也数不胜数。在这种形势下,艺术管理专业迅猛发展。2019年的艺术管理业界的活动比之于前一年更活跃,这种增长态势在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在学界,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每年都会举办研讨活动,2019年的会议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该大会设置的主题为:“艺术管理教育的全球视域与本地经验”,在分论坛上共设有9个议题,涉及范围广,包括艺术管理学科建设、艺术管理人力资源、艺术管理专业实践、表演艺术课程教育、表演艺术市场融合、大数据与观众拓展、开放博物馆革命、城市发展与新社群、中外文化艺术碰撞等。这些议题可大致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艺术管理学科发展;二是艺术管理实务研讨;三是全球化时代下艺术管理经验探讨。从议题设置上看,艺术管理的兴起不仅是中国特有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热门。故而,中央美术学院更具雄心,要在2020年举办世界性的艺术管理交流大会,其筹备会议于2019年11月先期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球31所大学和国际学术组织的60余位嘉宾出席,并得到了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CAAEA)、美国国际艺术管理教育学会(AAAE)、欧洲文化管理与文化政策教育联盟(ENCATC)、加拿大艺术管理与教育工作者协会(CAAAE)的支持。与此同时,关于艺术管理的理论研讨也较为活络,例如,清华大学举办了 “2019清华美院艺术管理论坛”,聚焦于艺术管理学科建设,“关注国内外学界业界前沿动态,致力促进行业交流,推进艺术管理学科建设。”①章锐:《2019清华美院艺术管理论坛综述》,《艺术管理》2019年第3期,第174页。
艺术人类学是艺术学与人类学交叉而产生的学科。中国的民族文化艺术、民间文化艺术历史悠久和底蕴深厚,吸引着多方人士参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2019年10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在云南艺术学院召开年度学术研讨会,共200多位学者参加。研讨会的主题是“艺术人类学与文化复兴”,设置了5个分论坛,议题分别为: “艺术人类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研究”“艺术人类学与少数民族艺术发展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与个案研究”“艺术人类学与乡村振兴研究”“艺术人类学与手工艺复兴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涉及4个方面: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少数民族艺术民族志撰写、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保护、乡村文化建设等。艺术人类学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支撑之一,也是民族民间艺术的推动力量,故而在我国取得了不俗的进步。当然,也正因为认识到中国在民族民间文化上与国外差别巨大,所以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呼吁加强“本土化”,这也是2019年艺术人类学年会的重要诉求。
三、艺术史的研探仍是热点而实质性突破却未到来
艺术史的研究是艺术学理论的基础。2011年艺术学升门之后,艺术学理论擢升为一级学科,拟定的学科方向中,艺术史是第一个,接下来才是艺术理论,可见艺术史的重要性。在随后的教育部指导性文件中,艺术史被赋予“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的任务,并明确了其地位—— “艺术史是艺术学理论及其他各个学科研究的历史基础和参照依据”。这份文件凝聚着众多业界学者初步共识,在艺术学理论仍处于摸索前进的当下,应该进一步明确其指导意义。
但是当前关于艺术史如何撰写仍然是一个充满不同意见的话题。在2019年12月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范式与外延——2019·第二届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上,关于艺术史的跨门类、跨媒介写作的问题,就形成了两派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艺术首要因素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从媒介形态上是分开的,因此跨媒介本身是困难的,而建立在跨媒介之上的一般艺术史,则无异于空中楼阁。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跨门类、跨媒介的一般艺术史的撰写是可行的,一般艺术史的写作首先要从观念触发,而不是首先从技巧出发,技巧的问题可以在各个门类艺术史中体现,但是艺术学理论视角下的艺术史则要超越艺术的媒体和载体。徐子方教授提出:“学科的跨界正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专业本质,自然也是在艺术学理论视野下的艺术史思考的创新出发点。不解决观念问题,不建立真正意义上打通和综合的艺术史观,艺术学理论学科中便没有也不可能有艺术史的合法地位。”②徐子方:《艺术史理论再思考》,《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5期,第5页。他是赞同跨界研究艺术史的,他在这里提出的 “综合的艺术史观”,很有意义。我们认为: “一般艺术史”是美学范式下的概念,艺术发展至今日,已经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承载体和主要社会生产力之一,囿于过去的学术范式的提法未免不合时宜。在艺术学理论获得新生的时期,应确立 “综合艺术史”的观念。笔者2019年发表在《民族艺术研究》的《2018年中国艺术学理论热点现象述评》中提到过,所谓的 “综合艺术史”,既有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说明,也有艺术史一般进程和规律的展现,还有专门的主流艺术类型的描述。因此,综合型而不是观念型的艺术史的撰写,才是艺术学理论视角下艺术史写作的应有样态。除此之外,再设置一门艺术思想史和一门艺术史学史,则可将艺术学理论的根基更牢固地扎下。
艺术史研究也是2019年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的重要议题之一。该年会于2019年10月在东北大学艺术学院举行,主题是“百年中国艺术理论的现代性建构”。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在会上的发言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学史的走向,认为艺术学理论正是在思想交锋中得到了成长。
艺术评论是当下艺术学理论的一个充满变化的领域,中国文联领导下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每年召开工作会和年会,推动着艺术评论快速发展。艺术评论与创作的第一线紧密连接着,处于眼花缭乱的变动之中,早已超越了纯文字表述的阶段。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联合北京大学文艺评论基地、中国传媒大学文艺评论基地、中国戏曲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西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业委员会等7家单位,于2019年12月举办了“辞旧迎新,迎接2020——文艺评论助力新时代艺术丰盛拓展”,吸引了200余人参加。会议上,学者们评述了近年来艺术评论领域新现象,提出了新的分析思路,也批评了部分恶俗的艺术评论景观,呼吁应关注艺术评论的新样态、新形式,认为艺术评论应该因时而新,趁时而变,随时代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