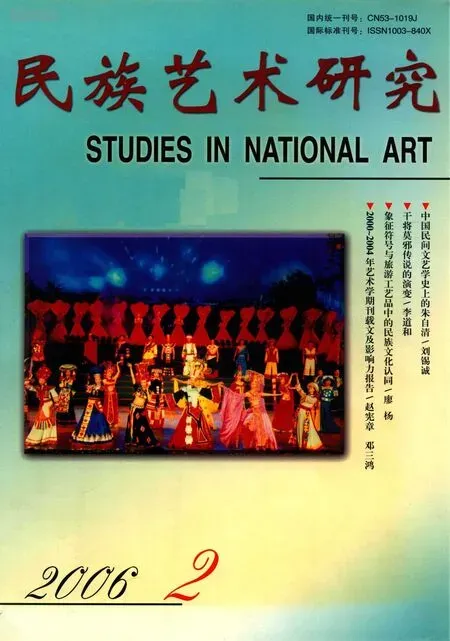2019年中国音乐学热点现象述评
2020-07-13黄宗权
黄宗权
2019年具有双重的“历史节点”意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的音乐学研究领域出现不少以历史的眼光来评析、论述中国音乐研究现状的文论。这些文论的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中国音乐研究的本土意识,体现了中国学者寻求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思考。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2019年出现的某些热点和趋向并非偶然,而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学术整体呈现寻求自我文化意识、音乐学者们以文化自觉的理念和行动推动中国音乐思潮变迁的一个缩影。比如,对音乐学界关于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讨论以及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新路向的呼吁,这些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学界的热点议题。
一、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乐派”建构的主张和观点
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重要学术议题。2019年“第三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办,本次年会的中心议题围绕创作理论来展开。显然,建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们,已经将这一议题从原本的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领域拓展至了作曲理论领域,可谓是该议题的一次纵深推进。
与“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中国乐派”的提法,也在内涵方面有了一定延伸。自中国音乐学院首推“中国乐派”这一概念以来,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反响,批评和赞同的声音都不绝如缕。2019年,适逢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年会的重要议题就是关于“乐派”。其中的一个子议题是“西方音乐的风格流派”。不过,其核心显然不仅仅是指向西方音乐的风格演变和西方音乐经典作品的探究,而是将西方音乐风格流派与“中国乐派”联系在一起,是透过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来探讨对“中国乐派”具有何种可供当代参照的价值和意义。也即,通过西方音乐视野来探究“中国乐派”建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说,该议题的设置预示了国内的西方音乐研究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作为西方音乐研究领域最大、最重要的学术会议,本次西方音乐学会年会呈现了高水平和多元化的特点,尤其在研究视角上有许多新颖的切入点。本届西方音乐年会,让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审视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也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当下中国本土音乐文化发展的需求。
对于何为“中国乐派”?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始终存在争论的。秦序认为, “中国乐派”的概念 “可大可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在中国产生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乐派,这是较小的“中国乐派”;而广义是指诸多较小乐派汇集而成。作为一个“统称”,广义的 “中国乐派”是多元一体的,具有不同于他国、他文化中产生的乐派,“中国乐派”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秦序认为,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乐派”既要继承中国音乐文化的悠久传统,又要创新性地推进当代中国音乐艺术的全面繁荣。他认为,“这是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从自在向自为的提升”。同时,秦序主张,建构“中国乐派”,要坚持多元一体、多样一体、多元共生的发展理念。①秦序:《“中国乐派”的释义与历史定位》,《中国音乐》2019年5期。
“中国乐派”的提法不光在音乐学领域引起讨论,在音乐表演领域也有类似的呼声。比如,王士魁、李先灵在《关于中国声乐学派建设的理论思考》②王士魁、李先灵:《关于中国声乐学派建设的理论思考》,《中国音乐》201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要建设“中国声乐学派”,应按照“立足中国、传承历史、把握当代、面向世界的思路,研究好中国声乐的发展之路,更大程度地发挥中国声乐的社会价值和美学功能”。类似地,黄华丽认为,需要在现有声乐学科建设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和定位民族声乐表演与民族歌剧表演二者之间的关系,主张以民族声乐的方式来演出民族歌剧,建构民族歌剧的话语体系。③黄华丽:《从民族声乐表演到民族歌剧表演话语体系建构散议》,《人民音乐》2019第2期。而郁钧剑则认为,不存在“真正的民族唱法”,现有的民族唱法可以说是“第二美声唱法”。他认为,不能用美声的标准来评判民族唱法,提出要用“语言决定唱法”,创立中国的声乐学派,形成真正的民族唱法体系。④郁钧剑:《中国民族声乐的现状与振兴之我见》,《人民音乐》2019年第1期。
以西方参照中国,或者在中西的互动交流中寻找不同文化的特性,似乎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共识。2019年9月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音乐当代研究暨第22届‘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主题“中国音乐的对比”(Contrasts in Chinese Music)无疑凸显了中外学者对中国音乐中碰撞与对比的关注,包括中国音乐在传统与现代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碰撞,也涉及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百年来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国音乐在未来发展的新趋势等。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传统民间音乐的保护和发展、当代新作品的创作与传播等研究论题成为研讨的焦点。
二、音乐学方法论、价值取向和各学科领域的当下反思
著名的术语“音腔论”的提出者沈洽在《面对失语的囧境——当我们言说某种音乐声时》⑤沈洽:《面对失语的囧境——当我们言说某种音乐声时》,《中国音乐》2019年第6期。一文中,针对音乐界长期以来照搬照套,用西方有关音乐形态学的术语来描述中国音乐传统中的音乐形态所产生的一系列“误读”“曲解”和“失语”等问题,提出批判性反思。沈洽认为,术语(语言)的异化是观念和认知结构异化的表征,而用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异化观念和认知结构解读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中国音乐,必定会带来各种误读。非西方术语所不能描述的那些音乐的特征对持有该音乐的人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他以朝鲜族民谣 《阿里郎》中的“音团” (sound-dough)和潮州筝乐《寒鸦戏水》中的“重三六调”为例,来说明我们现有的很多音乐术语,都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使得这些术语在描述中国音乐(或音乐的现象)时,显得很困难(或者不准确)。由此,沈洽提出建立“音乐形态术语学(The Terminology of Musical Morphology)研究小组”,来建构针对中国音乐传统的术语系统。
王次炤则再次追问音乐学的学科本质和属性。他认为,音乐学是“探索音乐艺术创造性思维的学问”。当下中国的音乐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长足发展和进步,已经在国际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然而,中国音乐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音乐认知的原创性研究”和“建立中国音乐学自身的理论体系”之上。王次炤认为,中国音乐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 “中国视野”“国际视野”“中国视野下的国际视野”三个阶段,视野的转变体现出我国音乐学术研究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不断增强自信的心路历程。王次炤进一步追问:“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音乐理论界如何建立文化自信?”为此,他提出三点呼吁:“(1)深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依然是中国音乐学者的首要任务;(2)音乐学研究的原创性追求;(3)建立中国音乐学自身的理论体系是中国音乐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①王次炤:《音乐学的历史地位和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音乐研究》2019年第4期。
李诗原则强调音乐学研究应具有人文学术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的基本要义是强调人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也即,“将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优化作为分析、研究、判断一切文化现象的基点,并在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相统一的视野中保持着人文学术精神及其价值取向”。李诗原认为,国内现有研究离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主要存在三大缺憾:“(1)音乐学在一定程度上已被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所遗弃;(2)我们的音乐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落后,在学术视野上显得狭隘;(3)我们的音乐研究只关注形态、器具和实用层次的东西,缺乏那种深层的、形而上的和非实用但更具‘实用理性’精神的人文价值支撑。”②李诗原:《音乐研究的人文学术价值取向》,《人民音乐》2019年第1期。
杨民康 《音乐研究怎样 “把目光投向人”》是为《音乐研究》杂志主办的“音乐与文化认同”专栏而写的导语。在文章中,杨民康重提郭乃安先生1991年的那句名言,“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杨民康赞同郭乃安的主张“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人们面对音乐时具备的主体性地位,亦即以人的主体性及文化本位为中心的意识。”杨民康提出的问题是,经由何种途径或研究方法能实现这一目标?杨民康提出,有关“音乐文化认同”的研究,是这一研究方向的尝试。他认为,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近年来转向了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论话语体系问题;二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族性认同和文化建构。杨民康认为,以文化认同为主旨的音乐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代表了长期以来的、传统的、以分析音乐为主体的研究,转向了以文化持有者为中心的人的研究。也即,将“目光投向了人”。③杨民康:《音乐研究怎样“把目光投向人”》,《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
同样受郭乃安的启发,秦序则提出“音乐学,请把目光也投向表演”。强调音乐表演的重要性,认为“无表演,即无音乐”。音乐是“兴于谱(作曲家创作)” “立于演(表演)”的艺术。在中西音乐中,有着不同的音乐表演观点,中国传统音乐有着表演灵活多变,有较大的创造空间。“活板”是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的重要特点。在我国当前的音乐表演艺术起得蓬勃发展的同时,音乐学对音乐表演的理论和探索却显得很薄弱。他认为,应该关注音乐表演实践,从而提升音乐学各方面的全面发展。④秦序:《音乐学,请把目光也投向表演》,《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2期。
音乐表演受到重视确是近年的一个趋向。2019年,有两场大型的音乐表演学术会议。6月14日—18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 “第二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和11月9日—13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首届音乐表演理论学科国际高峰论坛”。前者的会议主题之一是音乐表演的研究,应该形成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归到理论;后者的主题则提出“音乐表演是否需要研究?”
除了对音乐学学科的整体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的讨论以外,音乐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思性文论。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近几年关于断代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2期开设的“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纵横谈”专栏,推出了秦序、项阳、马良怀等人对这几个朝代音乐的研究成果;《音乐文化研究》2019年连续3期开辟了“音乐丝绸之路研究”专栏,刊发的王小盾、孙可臻等人针对中亚丝路音乐的研究引起关注。11月2日—3日,在“第三届宋代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展现了不少宋代的成果,对宋代音乐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陈旸<乐书>点校》的出版让宋代音乐古籍文献的整理成为一个新的话题。
不过,刘勇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四十年之检讨》一文中认为,近40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总体而言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通史写作虽然数量众多,但趋同现象较为普遍;对各类议题的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不平衡的现象。此外,对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与汉人政权并存的地域关注得不够。①刘勇:《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四十年之检讨》,《音乐研究》2019年第4期。
范晓峰从比 “音乐作品”更为广泛的“音乐现象”出发,提出音乐美学研究结论的可信性 (creditability)问题,即,追问音乐美学的研究结论是否经得住“音乐实践”的检验,又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的具有可信度;同时,追问音乐美学命题的“合理范围”问题。范晓峰认为,因为音乐现象本身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以及音乐学的发展拓展了学科领域,使得音乐美学在当下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美学不能仅仅是在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的领域来研究音乐现象,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欧洲古典音乐范围。因此,要让音乐美学跳出 “作品思维”而采用 “现象思维”。让音乐美学在综合各感性听觉的基础上,走向更深刻的理性自觉。②范晓峰:《面对音乐现象——音乐美学如何是?》,《人民音乐》2019年11月。
有关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的研究,项筱刚在《中国现当代音乐研究领域的热度和趋势》③项筱刚:《中国现当代音乐研究领域的热度和趋势》,《音乐研究》2019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方面有一定突破。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该领域取得了深化和拓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他特别论及戴嘉枋于2017年提出的: “重视被‘历史想象’隐匿的历史真实”和“关注‘启蒙’与‘救亡’双主题之外的‘娱乐主题’”。在该文中,项筱刚对近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的方法论和观念转向及原因做了较为详尽地整理和剖析。
三、音乐创作领域的回顾性与历史性展望
2019年1月13日至14日,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座谈会”是近年来音乐创作领域规格最高的一次座谈会,主要聚焦的是交响曲的创作问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以及来自全国的交响乐团团长和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新闻媒体记者近70人出席会议。
在会上,叶小纲再次提出了一个持续了多年的问题:“怎么样让交响乐作品更深入人心,让我们的交响乐真正打动人?”而韩新安则说道:“作为东方文明古国,能够借鉴外来音乐形式,表述本民族与本土的主题与情感,能够融入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中华民族的交响乐文化,这是历史性的音乐文化的进步。”秉持守正创新理念,创作更多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国际视野的精品力作是与会作曲家们的一个重要共识。
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1)委约制度存在盲点,自主创作不可忽视;(2)交响乐团发展:乐季安排需双轮驱动,激励机制要更加完善; (3)中国作品推广:中国作品应定期演出,国际巡演需融入主流观众群;(4)作品诠释、学术研究:二度创作亟待推进,评论分析相对滞后。①裴诺:《全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研讨会在京举办》,《人民音乐》2019年2月。
此外,还有关峡提出的:“老一代作品里面所蕴含的所有创作当中最本质的东西都有。而现在我们一些作曲,最本质东西都没有。”以及徐孟东提出的:“交响音乐作品创作确实是要考虑到的技巧性与可听性、民族性与艺术性,古典与前卫这‘三性’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是创作领域被反复追问多年的问题。
除交响音乐作品创作之外,对音乐创作的思考主要聚焦于民族器乐作品和钢琴作品的创作。这些文论以大跨度的历史时间为背景,思考音乐创作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而对中国当代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
张伯瑜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切入。他认为,许多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中除了强调自己的“艺术个性”以外,还聚焦于 “民族性”问题。这是由中国传统音乐具有“集体性认知模式”所决定的。这种模式又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作曲家接受了西方专业音乐创作中以“个体性”为主的“认知模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音乐创作理念与方法。但是,传统的集体性认知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还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中国当代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形成“个人、民族与世界”三重概念的交融认知,共同形成了中国当下创作的集体性观念。②张伯瑜:《论隐含在中国作曲家创作“个体性”背后的‘集体性’认知》,《音乐研究》2019年第4期。
叶松荣则提出“本土形式的大型民族器乐”的创作观点。所谓“本土形式的大型民族器乐”,是指蕴含“中国精神”的大型民族器乐。他认为,这一形式的创作是展现多样化的中国民族器乐创作,以适应新时代的现实要求。他主张这一形式的创作,应该打上民族气质、民族精神的印记,并将此作为音乐的内容存在于音乐的形式之中。③叶松荣:《关于本土形式的大型民族器乐创作的学理构想》,《音乐研究》2019年第5期。
基于文化的个性化表达是作曲家始终关注的问题。贾达群借评述梁雷的音乐,提出音乐创作的“表达”问题。他通过列举梁雷的《潇湘的记忆》 《千山万水》等作品,评述梁雷代表性作品中具有 “声音的选择”“音色技巧”“节奏安排”和“织体造型”等几个方面的艺术创作特征。他认为,梁雷的创作在这四个方面又分别具有 “有内涵”“有文化” “有逻辑”和“有智性”四个特征。在这个基础上,贾达群谈及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艺术创造中是“没有禁忌”的,音乐创作的根本问题是艺术家的文化选择及其表达的能力问题。他呼吁“让中华文化和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尽快脱离浮躁、肤浅、空洞和低速,而迈步走上文艺复兴的康庄大道。”④贾达群:《梁雷的“表达”及引发的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让钢琴说中国话”是杨燕迪近年来的一个“口号”。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⑤杨燕迪:《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音乐研究》2019年第4期。,他从宏观的视角对近四十年来,中国重要作曲家和钢琴作品进行了梳理和评介。他认为,过去四十年中国作曲界大量吸收和借鉴西方当代音乐思想观念和技术手段,以新的视角审视中国本土音乐文化资源,导致在音乐创作的艺术观和音乐观上的多元和分化。其结果是作曲家对“中国性”问题有着更加复杂和多面的看法。带来的一大问题是,许多钢琴音乐作品为了追求表面效果而缺乏内涵,观众接受度不高,同时,在推广和教学中也缺乏良性机制。在文中,他对汪立三和王建中二人的钢琴作品做了高度评价;此外,杨燕迪对如何以钢琴为载体表现 “民族性”和“中国性”,以及近年来中国钢琴音乐对传统音乐素材的使用方式等问题提出了其看法。
如何在当代创作中使用传统资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许多理论家指出应该使用中国传统独有的方式来创作。比如,杜亚雄认为,将“传统音乐基本理论”用于指导中国当代的作曲实践,是建设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必经之路。①杜亚雄:《促进传统乐理向作曲实践的转化》,《音乐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姚亚平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中国古代音乐没有西方意义上的 “作曲”,其原因在于,中西音乐观念上的差异。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创制实践中,由于音“声”观念复杂多义,故难以生发出类似“音程”的抽象概念,进而无法像西方音乐那样通过音程思维派生出复调、和声以及整个音乐的结构体系。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没有分离出“作曲”这样一个独立的行当,音乐创制和表演是一体的,正是这种一体化,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往往呈现集体性尊重传统,而非突出个人、追求标新立异的文化特征。②姚亚平:《中国古代音乐的创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而明言则借助评论于润洋先生的《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一文,陈述其对音乐创作的观点。再次提出以往现实中“过分着意于自然景色的描绘忽视深刻情感表达的做法,是违反器乐创作艺术规律的。我们的音乐批评不提倡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作曲家还是应该把巨大的创造想象贯注到深刻揭示内心情感上去。音乐是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③明言:《让器乐创作回归常识的呼吁——于润洋<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历史评价》,《人民音乐》2019年第5期。
和器乐作品相比,歌剧创作显得格外“火热”。然而在繁荣的背后,引发的却是各方不同角度的反思。比如,刘锡津认为,旋律写作是中国当代歌剧创作的突出软肋。掌握了专业作曲技术的作曲家,不够关注旋律写作的学习与研究,使得歌剧音乐的旋律不够“成熟老练”。刘锡津从旋律与“文化基因”、旋律与情感、旋律与歌词、旋律与综合表达等角度分析,认为旋律是歌剧赢得观众、能“接地气”的重要途径。④刘锡津:《也谈旋律写作在歌剧创作中的重要性》,《人民音乐》2019年第3期。
当然,赞扬的声音并非没有。2018年年底,郝维亚的歌剧《画皮》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演,赢得业界一片好评。前后有三篇评论与此有关。
杨和平认为,《画皮》是当年最富有创意的一部歌剧。他从和声、织体、配器、民乐的利用和音响的开发、脚本的戏剧化等方面来评点该歌剧的音乐创作,认为《画皮》用民乐队渲染戏剧性场景,在多方面有别于郝维亚此前的歌剧作品,也使其从当代同类歌剧作品中脱颖而出。⑤杨和平:《凛冽的音响叙事与无奈的辩证想象——评郝维亚歌剧<画皮>的音乐创作及其他》,《人民音乐》2019年第4期。
杨燕迪也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认为《画皮》的剧本改编“极富现代意识”。在音乐创作方面,京剧旦角的唱腔和美声形成的重唱,形成奇特而鲜明的、具有冲击性的效果。同时他认为,剧中对京剧韵白的运用是对“宣叙调”创作的一种独特开拓,也是针对中国歌剧宣叙调创作难题的一次成功突破。杨燕迪进一步引申认为,当代音乐环境下以崭新眼光重新开掘传统资源是一种新的可能的道路,因而这种实践的有效性就不仅只是针对个别作曲家和个别作品,而具有了更深广的启发和意义。⑥杨燕迪:《以现代思维开掘传统——评歌剧<画皮>兼谈当前中国歌剧创作中的若干问题》,《人民音乐》2019年第4期。
李吉提则对 《画皮》和郭文景的 《夜宴》这两部室内歌剧进行了从结构到音乐技法的比较,寻找二者的共性。她认为,这两部中国当代室内歌剧对中国戏曲都有多方面的继承,它们都采用了“西体中用”的方式,派生出音乐会形式的“中国新歌剧”体裁。两部歌剧都多方位跨越、用现代审美视角汲取了现代技术,使它们以诗意的方式进行了呈现。李吉提认为,应该以多元的方式来发展中国歌剧,而对中国文脉的继承是中国歌剧发展的一种新思路。①李吉提:《中国室内歌剧的诗意呈现——从<夜宴>和 <画皮>谈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歌剧的评论问题确实越来越引起了业界的重视。由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和山东艺术学院合办的“全国歌剧理论与创作研讨会暨首届全国优秀歌剧评论征集比赛”就是一个例子。该会议(比赛)于2019年12月13日举办,除了对获奖评论文章进行表彰以外,还对歌剧创作进行研讨。焦点依然集中于如何创作民族歌剧,如何体现歌剧思维,如何掌握中国歌剧的话语权以及如何建立中国歌剧学派等方面。另一个例子是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歌剧理论评论人才培养”项目于2019年7月8日至8月11日开班。该项目是首次针对歌剧评论人才的培训。
四、周文中与中西音乐文化的融通交流
2018年“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在星海音乐学院成立并召开了盛大的研讨会,这是音乐界对特定人物的研讨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在这次会议上宣读的文章,于2019年陆续刊发,形成一股聚光灯效应,引发多方关注。2019年10月,周文中先生不幸逝世,使得这些文章成了对这位杰出华人作曲家的永久纪念。
梁雷认为,周文中得到世界的公认,作为文化的使者,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份精神和灵魂的礼物。②梁雷:《精神的赠礼—— “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成立致辞》,《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洛秦以“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分析了周文中先生作为一位文人作曲家,其音乐具有的 “文人”特点。③洛秦:《论文人作曲家周文中——以“音乐文本田野工作”的方式思考》,《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班丽霞从周文中先生的音乐世界观角度来分析周文中的音乐创作观念。④班丽霞:《从音乐文化“汇流”看周文中先生的音乐世界观》,《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
沈云芳通过《霞光》分析了周文中具有的中国山水画情怀和其中国音乐美学观。⑤沈云芳:《一抹霞光入管弦——周文中音乐中的中国山水画情怀》,《黄钟》2019年第2期。李萌则认为《霞光》是作曲家受17世纪早期中国文人画的影响。⑥李萌:《一曲清漪濯晚霞——周文中<霞光>中色彩微变化的音乐表达》,《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美籍华人饶韵华认为,《苍松》表达出了与亚洲内部的成功对话,但这成功的对话却又是因中西文化的对话而促成的。她认为周文中之于西洋现代音乐的深厚涵养及底蕴,对其美学的灵敏,使得西洋现代语法“不露锋芒地融入亚洲当代音乐”。⑦饶韵华:《亚洲内部联结与对话:周文中和伽倻琴》,《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郑艳对周文中的弦乐四重奏《流泉》进行了研究,探究其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融入当代音乐创作当中。⑧郑艳:《流动的风景:周文中弦乐四重奏<流泉>研究》,《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陈鸿铎认为,周文中的突出之处在于,他能够把中西两种音乐文化的精神和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新路。⑨陈鸿铎:《中西汇流再融合 气韵生动创新篇——略论周文中先生音乐的成功之道》,《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梁晴则聚集《易经》和八卦如何影响周文中可变调式的创作。⑩梁晴:《周文中自创性可变调式之八卦》,《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潘世姬认为,周文中的对位观点是在书法艺术基础上融合西方对位的新观点。⑪潘世姬:《周文中:音乐书法家——从“苍松”系列作品试论他的对位观点》,《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
尽管学者们对周文中及其作品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是,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关注周文中作品中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或者说,关注周文中如何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实现了现代性转换,关注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
另一方面,与创作中的中国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问题相关的是中国音乐文化走向国际的实践和策略问题。
那些游走于中西之间的作曲家就此成了被讨论的对象。比如,姚亚平认为,谭盾的成功提供了某种启示。谭盾从象牙塔中突围争取听众,“主动拥抱年轻人”的策略得到了回报。在“玩音乐”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找到了一种将前卫音乐“通俗化”的可能。同时,与美国直接、简明的“快餐”文化相适应也促成了谭盾的成功。谭盾背靠中国文化的大树,其创作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关,不过,在处理 “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上,谭盾的经历是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不是让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进行“融合”,而是让中国文化 “引领”西方文化。①姚亚平:《谭盾:“把搞中国音乐当饭吃”——中国第五代作曲家音乐创作特写之一》,《人民音乐》2019年第6期。
陶诚对此则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他借用舞剧《孔子》在海外的演出案例,认为中国表演艺术作品在海外成功的答案,在于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艺术性”和 “生命力”,并通过适合于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以更加贴近海外主流市场的方式进入西方。②陶诚:《舞剧<孔子>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实践与思考》,《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4期。
让中国音乐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其内在隐含文化强国的倾向,这是近年来产生的群体心理。种种迹象表明,在进入21世纪20年代之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音乐界努力建构中国人自己的音乐话语,面向中国音乐的现实,寻求中国方案的动力越发强劲了。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寻求独特文化认同以及在强大的民族复兴的内在精神感召下,中国音乐界的这一目标能实现吗?
也许不用再等10年,我们就能看到结果。
(附言:感谢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9级研究生舒张静芝为本文提供的相关文献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