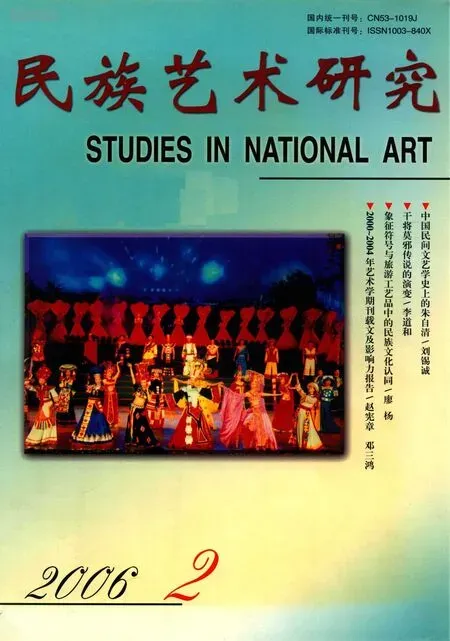形式演变视野中的文艺高峰
2020-07-13刘涵之
刘涵之
艺术形式是艺术品的符号呈现方式,任何艺术品首先都是通过形式触动人们的感官,令其“兴起”,从而引发人们借助它去探讨艺术的奇妙世界。“艺术作品要存在,必须是有形的。”①[法]福西永:《形式的生命》,陈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我们无法想象离开形式表达的艺术终究会怎样。事实上,艺术的主题、内容只有转化为形式,成为具体可感的艺术样式,人们对艺术的领悟与接受才有可能。一幅画作之所以为一幅画作,一尊雕塑之所以为一尊雕塑,一首诗歌之所以为一首诗歌,它们的价值何在?人们在开展艺术活动时首先便面临着对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区分,对艺术品的具体种类、样式的区分,对精妙的艺术与粗俗的艺术的区分。而做出这一甄别、判断的基础乃在于形式标准,正是通过形式的确认,人们不仅表现出对艺术的认知能力,而且表现出对艺术的欣赏和理解能力,从而利于艺术活动的常态开展。
作为文艺发展史的特殊现象的文艺高峰显然也存在着这样的形式标准。中外文艺发展史上若干时段的文艺高峰无不证明形式标准和尺度的辩证关系。即是说,文艺高峰的标准和尺度需要恢复到历史总体性和具体性的关系面得到理解。没有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便没有艺术发展,更没有文艺高峰的筑就。比如,在中国文学史上,韵文文体形式的发展就先后呈现过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的格局,造成了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体形式盛出的景观,又比如艺术形式的革新还通过由俗到雅的文体转换这一环节为文艺发展输入新鲜的血液:《诗经》“国风”采自民间,后在汉代被尊为儒家经典,格调逐渐雅致化;南朝民歌被引进梁陈宫廷,促成宫体诗的产生;词在唐代本是民间通俗曲子词,宋代文人加以改进从而登上大雅之堂;戏曲本起源于市井勾栏,有元一代蔚为大观,至明清形成高峰……
一、形式变迁与文艺高峰
在论述“美的定义”的历史渊源和具有标志性的文艺现象时,美学家鲍桑葵指出:“在古代人中间,美的基本理论是和节奏、对称、各部分的和谐等观念分不开的,一句话,是和多样性的统一这一总公式分不开的。至于近代人,我们觉得他们比较注重意蕴、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表露。一般来说,这就是说,他们比较注重特征(the characteristic)。”①[美]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页。自艺术的诞生期开始,艺术品的实用目的决定了艺术的存在价值,形式因素显然不完全构成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区分标准,但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深化、对艺术创作认识的加深,基于对理性力量确证的形式之美常常成为艺术创作和美学理论的关切点,这从古代希腊人建筑、雕塑、悲剧等文艺杰作崇尚比例、和谐、秩序感、规律性和宁静之美可以看出,同时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 “宇宙谐音”说、苏格拉底的“合式”说、柏拉图的 “理式”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可以看出。至古罗马时期,有关建筑物外貌布置、比例等形式的思考已经非常成熟,如神庙、剧场一类经典性公共建筑柱廊的设计等等,如当时罗马宫廷的御用建筑师和工程师维特鲁威所著的《建筑十书》就因从形式方面立论并总结建筑艺术成就而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在中世纪,神学美学也宣称美的要素取决于完整、和谐,取决于光和色彩的鲜明等等,其时占主流的哥特式建筑对比例和几何结构的突出,宗教题材绘画对整体之美和因静观而致生的超感官的美的突出就是明证。文艺复兴繁盛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将人体解剖学和透视学用于绘画,更注重艺术创作物体空间布局、运动、形态和内部构造关系等方面,更注重知觉对形式的把握和形式在知觉中的反映,他在讨论诗画之别时就指出绘画的美妙在于和谐、整体地“模仿”自然:“绘画替最高贵的感官——眼睛服务。从绘画中产生了协调的比例,犹如各个声部都齐唱,可以产生和谐的比例,使听觉大为愉快,使听众如醉如痴;但绘画中天使般脸庞的协调之美,效果却更为巨大,因为这样的匀称产生了一种和谐,同时射进眼帘,如同音乐入耳一般迅速。”②[意]列奥纳多·达·芬奇:《芬奇论绘画》,戴勉编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4页。17世纪在荷兰兴起了以伦勃朗为代表的风景画画派,这个画派将普通人的生活置入画面,农民、牲口、工场、客店、街道无不成为绘画的表现对象,逼真地还原出荷兰的社会风俗和精神风貌,而其艺术形式则在挖掘和谐之美,以至于著名的艺术哲学家丹纳如此评论道,“这些作品中透露出一片宁静安乐的和谐,令人心旷神怡;艺术家像他的人物一样精神平衡;你觉得他的图画中的生活非常舒服,自在。”③[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3页。18世纪的英国著名画家荷加斯在其享有盛誉的《美的分析》一书中则论证了艺术形式的六大原则:适应、多样、统一、单纯、复杂、尺寸。荷加斯认为这几大原则“都参与美的创造,互相补充,有时互相制约。”荷加斯以绘画领域的线条、色彩、构图、面部、姿态、动作等方面的处理为例详细分析了美术创作形式因素的本质和各种不同组合方式,在他看来形式因素的组合与艺术品的总体意图相适应。如果不合意图不合目的,也就失去了美;反之,如果没有美的形式的呈现也就谈不上艺术品的总体意图。整体而言,荷加斯结合自身创作经验总结艺术形式创作原则并没有超出“多样性的统一”这一核心观念,用荷加斯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兴趣在于“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认为某些东西的形式是美的,另一些形式是丑的,某些东西的形式是有吸引力的,另一些东西的形式是没有吸引力的。”④[美]威廉·荷加斯:《美的分析》,杨成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不仅在美术领域,古典时期的表演艺术领域也有对艺术形式“多样性的统一”的思考和实践,法国宫廷戏剧家、理论家布瓦洛和戏剧大师高乃依、莫里哀就是代表。对于布瓦洛来说,诗歌的创作需要借鉴古代希腊人的法则,既要合理又要合适,“处处能把善和真与趣味融成一片”⑤[法]布瓦洛:《诗的艺术》(增补本),范希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从而实现美、真和艺术快感的三者同一。对于高乃依、莫里哀来说,戏剧创作合乎“三一律”规则是不二选择,时间的一致、地点的一致和情节的一致能保证戏剧在形式上紧凑严密、完整统一和平稳妥当。据说1624—1642年间曾任法国首相的黎塞留还亲自操刀悲剧 《米拉姆》的写作和演出。《米拉姆》一剧仅用一堂布景,五幕戏分别选择不同的灯光来标明时间,第一幕戏发生在日落时分,第二幕为月夜时分,第三幕是太阳初升之时,第四幕则在正午,第五幕则为傍晚, “在一昼夜里发生在一个地方的一件事,规整的内容产生了规整的布景”,①余秋雨:《世界戏剧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完全吻合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时间、地点、情节一致性的规定。西方艺术发展史表明,无论在“古代人中间”美的定义内涵体现对“多样性的统一”原则的倾斜,还是中世纪到新古典主义艺术体现出对这一原则的偏至,因而“比较注重特征” “多样性的统一”这一形式美学观念实际扎根于艺术实践中和文艺杰作的创作,重和谐、重秩序感的审美意识贯穿了自古典时期至18世纪的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发展过程,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
与西方重和谐、重秩序感的形式美学类似,中国艺术形式美学的智慧主要集中在对“文”的作用、功能的突出上。文与纹相通,意指文身,源于对身体的修饰,它带有很强的原始宗教色彩,后又用于战争图腾、宴会以及成年礼仪中。文的主要特点在两个方面。一为修饰性。饰,单一不行,错彩成画,寓成于和。二为规定性。规定性意味饰最终服务于礼制的规定性,结果伦理承担为其本义。②此处借鉴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一书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的观点。 (见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4页。)孔子在《论语》“雍也”篇里将古代关于文的思想表述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人的学“文”而言,孔子把礼乐修养视为文的主要内容,质则当作人的固有品质,孔子因之强调君子之学对两者关系的制衡;就艺术创作而言,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标准大体反映了政教礼乐之文(包括制诗、制乐之类的艺术创作)需要考虑到形式因素的本来面目,是对文的创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还以文为标准来肯定尧舜和西周,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称西周“郁郁乎文哉”。③于民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从先秦对包括礼乐之制的文的实践来看,如 《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臧僖伯谏观鱼等典型事例,无不注重文艺风格的表现形式和文物昭德的伦理功能,所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总结孔子的这一做法时,会认为“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④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在孔子的启发和影响下,中国艺术对文的考究和对文所蕴含的质的考究便成为中国形式美学的主要特色,文、质关系的平衡可谓一以贯之,其中尤以作为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韵文、格律诗为甚。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提出过“文附质”“质待文”的观点,并以此为标准检讨历代诗文创作实绩。李白则在《古风五十九其一》中高呼: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的艺术理想,并身体力行。朱熹从他的理学视角出发,认为道和文有着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申明“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李渔基于自己的戏剧创作经验,以为戏剧传奇有三美: “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情事不奇不传。文词不警拔不传。情文俱备不轨乎正道……亦终不传……三美俱擅,词家之能事毕矣。”而思想家王夫之在《尚书引义》中则通过文与质之间关系的辩证,文与象之间关系的比照,将这一形式美学阐发得更为系统,带有总结的意义:
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无有无象。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所以质以视章,而文由察著。
……
辞之善者,集文以成质。辞之失也,吝于质而萎于文。集文以成质,则天下以达质,而礼、乐、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质不昭,则天下莫劝于其文,而礼、乐、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败鼓,而莫为之兴。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惟质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惟质则要足以持,惟文则要足以该。故文质彬彬,而体要立矣。①于民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217、302、426—427、459—460页。
在中国艺术史上,“文质彬彬”作为艺术的形式标准一提出便得到连续持久的贯彻,这和儒家主张情感内敛、含蓄的中庸美学取得了一致,决定了艺术史中和之美形式表达的总体风貌和形式、意蕴并重的艺术主潮,当然也决定了中国文艺高峰的“儒雅风流”的整体姿态和标准。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和尺度》一文认为:“我们说‘标准’,有两个意思。一是不自觉的,一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是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自觉的是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并且称“不自觉的种种标准为‘标准’” “种种自觉的标准为‘尺度’。”朱自清考察中国文学史的传统,得出结论:即便整体上, “儒雅风流”是标准,但这个标准在不同时代因为文学发展有着许多变化就有了新的尺度,因为尺度伸缩的长短不同、疏密不同,因而不同时代的文学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文艺发展史表明,文艺史一方面内蕴某种一致性的审美特质,一方面这样的特质又具体化为分殊的审美崇尚。如果说前者意味着有关民族性的某些总体性的文艺实践,那么后者则说明文艺实践是贯彻到具体的、差异明显的包括时代精神、艺术创作、艺术表达在内的文艺现象之中的——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便是连续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中国文艺高峰的形式离不开“文质彬彬”的标准,但也因为具体实践的差异而赋予“文质彬彬”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形式意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艺)”,其实也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艺)形式。
二、文艺高峰的形式理论举隅
近现代艺术形式相对古典时期来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与其说古典时期艺术创作集中“多样性的统一”之于艺术形式表达的重要性,促进了艺术形式或模仿或反映世界自身的和谐性,不如说近现代艺术标举对这一和谐性的反动,进而引发艺术创作更注重提升形式的内蕴,从而解放了形式,说这个时期艺术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不为过。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以他独有的方式清晰地勾勒出形式之于审美判断的意义:“在绘画中,雕刻中,乃至在一切造型艺术中,在建筑艺术、园林艺术中,就它们作为美的艺术而言,素描都是根本性的东西,在素描中,并不是那通过感觉而使人快乐的东西,而只是通过其形式而使人喜欢的东西,才构成了鉴赏的一切素质的基础。使轮廓生辉的颜色是属于魅力的;它们虽然能够使对象本身对于感觉生动起来,但却不能使之值得观赏和美;毋宁说,它们大部分是完全受到美的形式所要求的东西的限制的,并且甚至在魅力被容许的地方,它们也只有通过美的形式才变得高贵起来。”②[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在康德看来,人们对美的事物的欣赏取决于其形式,在绘画领域主要集中于线条、轮廓等抽象外形。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突出审美判断的客观性,突出这种客观性的普遍适应性,突出审美判断通过诉诸理性而不是直接经由感性给出,因而他会将“魅力” “感觉”和美对立起来,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肯定经过理性过滤的形式表达与美的表达。康德形式主义美学给予德国、英国浪漫主义文艺极大的影响,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文艺巨子纷纷重视想象力、重视文艺形式的新奇性和异国情调的表达都与康德美学注重形式有关。
19世纪中后期,艺术对新标准的寻找又促发了现代主义运动的产生。现代主义艺术对艺术形式、艺术手段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独立性的关注无与伦比。这里我们试结合抽象主义的开创人俄国著名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绘画及其理论加以描述。康定斯基将绘画分为两类,一类是重物质的艺术,另一类是重精神的艺术。前者通过视觉的刺激来影响欣赏者,它是外在的;后者则诉诸欣赏者的心灵共鸣,它是内在的。康定斯基又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源于艺术家的内在心灵,对于艺术家来说“所有的手法都是神圣的,假如它们是内在必需的话。所有的手段都是荒谬的,如果它们不是出自内在必需的话。”所谓“内在必需”是指艺术的表达手段充分尊重心灵法则,结果艺术形式只能以艺术精神的内在需要为依据:“最精确的比例、最精确的计算和砝码都不会用头脑计算和演绎衡测的方法得出正确的结果。这种比例不可能计算出来,也找不到那样的衡秤。比例和砝码不在画家身外,而在他的心里。它们可以称之为尺度的感情、艺术的节拍——这是画家天赋的物质;激情可以使他们升华到天才发明的高度。”康定斯基的画作极为注重点、线、面艺术元素在构图中的作用,以为三者作为艺术的基本要素可以得到“纯”科学式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动力在于“无目的的或超目的的知识渴望。”①[俄]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李政文等编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123页。康定斯基的画作通常有色彩和构图的并置,但几何构图在画面中的地位更为突出,点、线、面的连缀使得画面充满动态,这一动态又颇能折射精神的自由,其作品《几个圆形,323号》《黄·红·蓝》就是这方面的佳例。前者选择以几何圆点为构图的支配力量,后者非规则几何图聚、散结合,突出的都是颜色对比中的点、线、面动态呈现,从而充分表现了画家内心的灵动之感。
20世纪上半期,对艺术的形式从理论的高度做出全面总结的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艺思潮流派。在被标举为形式主义宣言书的《艺术作为手法》(1917)一文当中,形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反对从形象思维、形象因素着手研究艺术时便顺手指出了艺术研究的真正对象:
各种诗歌流的全部活动不过是积累和发现新的手法,以便安排和设计语言材料,而且安排形象远远超过创造形象。形象都是现成的东西,而且人们在诗歌里回忆起的形象,比用来进行思维的形象要多得多。
形象思维无论如何也不是联系所有艺术科学的纽带,甚至也不是联系文学艺术各个学科的纽带,形象的变化并不是诗歌发展的本质。
既然不承认形象是诗 (艺术)的本质,那么只有从诗歌 (艺术)创作的本质属性“积累和发现新的手法”“安排和设计语言材料”着手了。为了清晰地阐明这一新手法并检验其效果,什克洛夫斯基将艺术对形象的“回忆”表述为 “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艺术创作类似于“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这表明“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无关重要的。”“奇特化”(亦翻译为“陌生化”)造成的陌生、间离效果显然目的在于“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延长审美感受,这显示了形式主义从鉴赏心理的满足方面考虑艺术审美属性的独特视野。什克罗夫斯基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为例,认为其小说的“奇特化”手法主要表现在“他不直接呼事物的名称,而是描绘事物,仿佛他第一次见到这种事物一样;他对待每一事件都仿佛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件。”②[俄]维·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载[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6页。在1921年写就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结构》一文当中,他仍以托尔斯泰为例,指出“奇特化”手法“另有一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就是在一个图景的细节上耽搁许久,并加以强调,这样便产生常见的比例的变形。”③[俄]维·什克洛夫斯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结构》,载[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托尔斯泰小说的奇特化表现效果证实了“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在形象塑造方面的创举,它不但有助于展现小说细节刻画的逼真性,而且有助于推动情节布局的创新,从而确证形式新变之于艺术效果的意义,而托尔斯泰作为俄国文学的高峰也能在这里得到理解。
三、文艺高峰的形式意蕴与文艺范例
英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过:“欣赏艺术品,我们不需要带有什么别的,只需要带有形式感、色彩感和三度空间感的知识。”①[英]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7页。贝尔虽然着重探讨人们对绘画作品的欣赏条件,但他指出“形式感”之于艺术欣赏(当然也包括艺术创作)的基础地位,的确是肯定了形式因素在艺术活动中的首要性。艺术形式总是指向艺术品本身,创作新的艺术便是创作新的艺术形式,反之亦然。形式因素的确立意味着艺术的确立,艺术形式原本就是艺术品的存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它对艺术起到规范、整饬的作用,艺术并非一个随便是什么和随便做什么的自由王国。换句话来说,无节制的形式和不完美的形式意味着艺术创作的非完美,因此,对形式的考究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关键环节。比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就以艺术形式的合目的性标准划分艺术类型的等级序列为:诗的艺术→音的艺术→造型艺术;再比如,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在康德的基础上以意志的客观化为标准将艺术类型进一步等级化:建筑艺术→花园艺术→雕塑→绘画→诗歌→悲剧。
就具体的艺术品来说,它内在的组合、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构成艺术的样式,即艺术形式。艺术形式是艺术品的形式,离开形式也就没有艺术特征可言、没有感性整体可言,因而艺术的特征在于形式,形式是艺术品的存在方式,“由于形式使对象成形并赋予对象以一种存在,因而完全可以说形式既是意义又是本质。它是体现在外观中的理念,并赋予外观以某些永久性。”②[法]米·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上册),韩树站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艺术品不同于一般自然物质在于它是艺术家创作的产物,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在于它是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呈现出来的美,因而艺术品是人工之物,艺术美是人工之物的美。艺术家作用于自然物质也就是为一般物质赋予形式、赋予形式之美。艺术天才为艺术立法,往往是为艺术形式立法。艺术家的创作始于形式又终于形式,他必须围绕着素材、对象运用有力的手段去突出某种形式、建构某种形式,以便让欣赏者通过对形式的体验来理解形式的功能。
形式永远是活着的。托尔斯泰就把形式传达看作情感体验效果的标志,他这样认为:“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把自己所体验的情感传达给别人,就重新唤起自己心中这份情感,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托尔斯泰以受狼惊吓的男孩讲述自己经历为例来论述这种“外在的标志”的内在构成, “一个遇见狼而受过惊吓的小男孩,在讲述这件事情时,为了使别人也感受着他所体验的情感,于是在描写他自己遭遇到狼之前的情况、所处的环境、森林、自己的无忧无虑,随后描述狼的样子、狼的举动以及他与狼之间的距离,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男孩子在讲述时再次感受他所体验过的情感,感染着听众,让他们也体验到讲述者所体验过的一切——这就是艺术。”③[俄]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张昕畅、刘岩、赵雪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显然,小男孩讲述自己遇狼经历的故事感染效果取决于他所描述的故事的布局,在故事内核中,小男孩遇狼的即时状况被安排进受狼惊吓的环节,这涉及故事如何叙述、以何种方式及结构层次叙述等形式要素,小男孩不仅仅是在向他的听众讲述自己遇狼的经历,他需要考虑到自己如何唤起听众体验到他所体验过的一切,他的描述意图决定他的故事的感染力度。
对于形式的讲究,在一些执着于新方法、新手段的实践的天才艺术家那里可能走得更远,以至于不难想象:愈是艺术杰作愈是讲究艺术形式的突破,愈是艺术形式取得伟大突破愈是艺术杰作。试以印象主义绘画宗师凡·高的《夕阳和播种者》为例。就像凡·高许多具有标志性特征的风景画一样,“播种者”的画面内容很简单:已经翻耕的土地呈现蓝褐色,一直蔓延到地平线;播种者迈开士兵式矫健的步伐,昂首前行,他的身后是一片火红的麦地,上空一轮夕阳低悬天空,光芒耀眼。正如有的论者指出, “凡·高的画,看很多细部,会发现颜色与笔触纠缠成一片如火焰的颤动,这种形式,不再是客观的形式思考,已经是凡·高内在主观形式的再现了。”①蒋勋:《艺术概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0—101页。在画面的右上方,播种者迈开士兵式的雄阔步伐,从田野的这一端撒播开种子直到田野的尽头,他有可能只是一个尽义务的劳动者,有可能是一个负债者,有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承担者,他的当下状况模糊不清,人们只能从他矫健的身姿去辨明他是一个熟练的体力劳动者。人们从翻耕的土地,从落山的太阳还可以体会到播种者紧张繁忙的一天即将结束,尽管这个劳动场面不很壮观。而他身后的成片麦地约略构成这么一种景致:等待收割的麦子,翻耕的土地。这是一个播种到收获的过程的浓缩,播种承继着收获,收获承继着播种。这个今日的播种者在昨日可能是一个收割者、一个翻耕土地的人,若干日过后,他又可能是一个翻耕土地的人,一个收割者、播种者。他所有的劳动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继续,他可能为土地歉收伤神,可能为病床上的妻子担忧,也可能为偿付不了债务犯愁,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曾阻碍他劳动的步伐。他是一个劳动者,在开始劳动的时候就被选择了劳动者的身份,仿佛亲近土地是天赋予他的权利,他不会去寻思这种身份确立得合不合理,他也不会去反抗什么,更不会去计较重复劳动带来的单调乏味。他仅仅为填饱肚皮而劳动,为治好妻子的病而劳动,为付清沉重的债务而劳动。他稳健的步伐表明他有信心解决好这一项项的困难,用劳动的双手创造一个休养生息的家园。只要他的劳动有所收获,他的汗水随着撒播的种子飘落在干涸的土地上,希望的种子就一定能生根、发芽,长成茂盛的庄稼。他如果看到一线生机尚在,他的步伐就会加快,而欢畅的歌声也就会从空旷的田野上空升腾。这种田园风光和劳作场面因为凡·高印象主义的浓墨重彩而层次分明,它虽不恬淡但很质朴,它静幽却充满着刚健的力度,尤其是地平线上方太阳光芒的橘黄色与土地的蓝褐色对照强烈、交相辉映,几乎让人产生眩晕的感觉,给欣赏者心理极大的刺激。而刚翻耕过的土地是新鲜的,日落西山意味着新的一天即将来临,这两者相互承接,在主题蕴涵和形式表达方面又融合为一。土地上的播种者就是这个主题和形式的阐释者:他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氤氲了自然和人工的生长点。土地因孕育生命而伟大,他因点播生命而伟大。作为早期印象派的奠基者,凡·高的画作,如《向日葵》 《鸢尾兰》《夕阳下的柳树》《星月夜》等,对颜色的强调和构型显示了他一贯的美学趣味,凡·高的星空、大地、静物无不着染上他个性化的风格, “在大地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美中,凡·高只选择了一种:颜色。大自然那种总能使色彩对比得无懈可击的特性,色彩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中间色,以及土地那种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又不论在什么季节,不论在什么纬度都同样美丽的色彩,总是使凡·高惊喜不已。”②[俄]康·帕乌斯托夫基:《金玫瑰》,戴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可以说,凡·高画作给人造成的感染力正是取决于因颜色调配而生发的形式美,它让画家惊喜不已,也让每一个观赏者惊喜不已,正如贝尔推崇画家塞尚,称他为 “发现 ‘形式’这块新大陆的哥伦布”,塞尚“创造了形式,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能获得他生存的目的——即对形式意味感的表现”,③[英]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41、143页。凡·高也是形式新大陆的发现者,他的画作同样是“对形式意味感的表现”。
当然,形式是相对艺术品的主题和内容而言的,说到艺术品的形式,很难不与内容相联系。艺术品因为内容的意义呈现而富有价值,因为形式的表达而定型。当我们说艺术形式是就艺术品的形式而言的,它意在突出艺术形式的独立性,而艺术品乃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辩证地内蕴于艺术品之中,故谈论艺术形式又需回到两者的关系方面。在艺术品中,内容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对整体效果来说至关重要,它涉及形式表达的作用和目的,因而不存为形式而形式的艺术创作,同时,形式的美学效果最终助益于内容和主题的呈现,因而不存在为主题(思想)而主题(思想)的艺术创作。“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中,谈到内容与形式问题,通常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的含义:其一就任何一部具体艺术作品而言,其内容与形式都具有与别的作品不同的个性;其二就一类作品而言,即通常所说的艺术的种类和体裁,是指某些艺术作品就其在反映的对象、表现方式和传达手段等方面具有共同点,因而在这些艺术品之间不论内容与形式都存在着共性,而与其他类型相比,又具有特殊性;其三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艺术作品而言,或者在一种艺术类型内部,或者在几种艺术类型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风格的类似性或一致性。”①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200页。有人将艺术形式与非艺术形式的区别认定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见的一致性”②[美]F.大卫·马丁李·A.雅各布斯:《艺术导论》,包慧怡、黄少婷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其实亦可从“个性”的形成、类型的特殊性、风格的一致性三个方面来理解,艺术品形式的“可见的一致性”并非什么神秘之物,需要就其服务对象而言,而这个对象自然也能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区别开来。艺术形式“可见的一致性”说明,艺术形式服务于艺术品的整体效果,不可将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谈论。至于具体的艺术创作领域,如诗歌、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等,因为素材、质料的差异可能形成不同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但即使同样的主题在不同的艺术种类中也存在不同的形式表达,比如,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指出的“拉奥孔”雕塑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史诗对祭师拉奥孔的恐惧情形的不同刻画方式;比如,我国唐代敦煌“变文”和“俗讲”在处理佛经故事上的形式差别,它们的艺术史地位与其说来自神话传说、佛经教义,不如说来自形式的独创性和艺术表达的变革。艺术形式通过致力于整体效果的实现而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这样相对独立于主题和内容的形式要素获得自身的审美特质,艺术成就愈伟大审美特质因此愈突出。这是我们选择从形式演变及其历程的角度探讨文艺高峰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