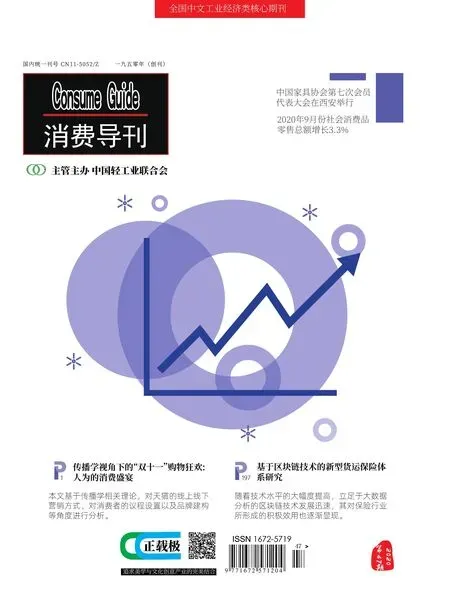“强监管 严监管”政策背景下地方中小银行应对策略探析
2020-07-12崔亮青岛农商银行
崔亮 青岛农商银行
一般认为,监管政策是影响银行经营发展的外生变量,并将监管政策视为银行影响视为短期、突发性影响因素,并在分析方法中将其作为虚拟变量进行考虑。然而,2008年以来监管政策的出台与实体经济基本面密不可分,强监管、严监管背景下,监管政策成为影响银行市场定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监管政策研究需要梳理其背后逻辑的基础上,分析监管政策对银行业基本面的宏观影响,进而分析其对银行个体的微观影响。
一、“强监管、严监管”的政策逻辑
此轮“强监管、严监管”政策的出台从2016年底开始,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回归本源、加强监管协调、补足短板”。《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首次提到“灰犀牛”概念:“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将防风险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强监管、严监管”政策背景经历一个由弱及强,由点及面强化过程,监管政策的出台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实质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初金融监管部门密集出台重磅政策,拉开金融乱象整治的大幕,银行业已经历了两轮监管政策落地。第一阶段,2017年上半年,以银监会“三三四十”检查为代表是监管政策落地的第一波高峰;第二阶段,2017年底至今我们再次迎来了监管政策的落地潮,包括一行三会发布的《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及其配套文件、银监会《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银监会《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等。梳理监管政策演变逻辑发现,监管政策变化源于实体经济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基于以下考量:一是随着国内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大量的信贷资源被城投、房地产、僵尸企业等低效率主体所消耗,恶化经济结构,没能有效支持供给侧改革。二是金融体系的虚胖对实体经济增长贡献减弱。尤其是从15年开始,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事倍功半,单位社融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并导致宏观杠杆率急剧攀升。三是金融体系日益膨胀、同业链条拉长,系统性风险显著增加。13年钱荒、15年股市调整及诸多隐患敲响警钟,国内银行业极易在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过程中产生冲击和共振,引发宏观系统性风险。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国“一行三会”累计共出台重要监管文件超过20个,具体到银行业,监管罚单数量、处罚金额、处罚人数较以往大幅提升,2017年处罚金额高达26.98亿元,2018年19.45亿元,2019年14.49亿元,由此判断近年来银行业监管力度持续处于高压态势,监管部门特别强调通过提高违法成本促进银行政策落实。梳理2020年已公布的监管罚单,处罚问题集中反映在信贷业务、同业理财业务、票据业务等领域,其中信贷领域中的违规发放贷款、信贷资金被挪用、贷款三查不尽职等问题处罚居高不下。
二、监管政策对当前银行业的影响
近期监管治理金融乱象的总体思路是:坚决去杠杆,去通道业务,引导银行业务回归本源,进一步规范市场投资和交易行为。从监管的重点来看,主要是针对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重在遏制层层嵌套和资金脱实向虚。从监管内容看,包括表外理财、同业存单纳入MPA,银监会“三三四”专项治理,严查消费贷入楼市,发布资管新规等一系列监管方案密集出台,对银行业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去杠杆、去通道,资产端服务实体的要求明显增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在过去十年,城投、房地产和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而在金融系统重塑的过程中,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将重新调整,减少对城投、房地产等的支持,需要推动金融资源向供给侧改革中的补短板方向倾斜。监管要求银行资产端溯本还源,重新回归支持实体的主业。
二是表内资产负债管理难度增大,资本金补充压力显著增加。MPA考核直接约束广义信贷扩张,并提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机构信贷增长主要靠压缩票据和同业资产,腾挪信贷规模,而随着非标和委托贷款等表外资产逐步回表,导致银行资本金补充压力大增,但问题是地方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途径单一且不通畅,股权融资的难度较大,经营不佳的中小银行二级资本债、可转债、永续债等债券融资难度也越来越难。
三是集中度不断提升,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空间明显收窄。在强监管背景下,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和收缩无法避免,之前中小银行之所以能与国有大行、股份制行竞争,主要就在于依靠非标等高收益资产来支撑高负债成本,并得益于资金池模式来扩张规模,随着金融乱象整治,地方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相较于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影响将更加剧烈。
三、地方中小银行的市场定位与应对策略
08年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业务发展重点先后经历了公司、同业、零售三阶段轮换,而这又与我国企业(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居民部门先后承担加杠杆主力军紧密相连。相较于其他银行,地方中小银行在市场定位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地方中小银行局限于本地区域市场,发展战略上主要采取跟随性策略,在以上三大业务板块,地方中小银行只能作为跟随者。因此,地方中小银行的市场定位比其他商业银行更容易受到监管限制。然而,反过来考虑,监管从严给地方中小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同等政策空间、同等市场选择机会,如果能充分发挥自身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服务实体经济的比较优势,反而具有更大后发优势。因此,地方中小银行在业务发展中应当探索采取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借助“地方银行、市民银行、小微银行”的发展平台,争取利用本地资源多、决策流程短、法人地位灵活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一是回归本源,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从银行业发展趋势来看,零售业务发展战略成为各家银行战略重点,零售银行作为地方中小银行“一体两翼”战略的核心,是立行的基础。当前形势下,地方中小银行充分研究国家和地方相关普惠金融、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相关政策,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完善激励机制、创新产品服务,引导分支机构,聚焦主业、聚焦实体、聚焦小微、聚焦三农,争取在零售银行战略落实方面实现新突破。
二是政策力度加码,监管合规成为业务发展的重要规范。在强监管背景下,银行业务发展过程中更加突出合规经营发展理念,注重业务流程再造,从产品创新、细节控制、风险评估入手,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将合规管理贯穿于业务流程始终,真正做到不碰监管红线、不踩监管底线。
三是寻找新的增长点,需要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强监管形势下,并不能一刀切,让银行放弃业务创新,完全回归传统存贷汇业务,而赢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开展特色化、差异化业务创新,特别注重从资产负债配置、风险管理中降低成本,提升收益,要特别注重流动性管理、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定价管理、经济资本管理等核心管理工具开发运行,真正提升地方中小银行长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