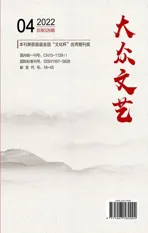郭象《庄子注》中“志”范畴研究
2020-07-12扬州大学225002
(扬州大学 225002)
《庄子》继承老子空无、虚静的理论,创造性讨论了至“道”的途径:只有通过直接诉诸本心的内省直观之法,保持内心的虚洁清明,才能体悟“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庄子·天地》)的“道”。这种审美活动过程,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心斋坐忘”,即用心去斋戒 。至于如何“心斋”,《达生》中说道:“用志不分”,即要求心志专一。那么,《庄子》所论的“心斋”与“志”之间是怎样的一种联系,使得二者可以在价值层面上达到统一呢?笔者从对《庄子注》中“志”的范畴研究出发,进而考察“心斋”与“志”间的关联,以究郭象“内圣外王”的内涵及旨趣。
一、“志”之释
在解释郭象所言“志”之前, 先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它的用法和含义做整体上的考察, 以便更清楚地把握《庄子注》中“志”的范畴含义。
(一)“志”字义考察
《周礼·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识。葢古文有志无识,小篆乃有识字” 。因古时“识”字的志韵与职韵音韵不分,意义又相通,因此古文作“识”为“志”。则志者,“记也,知也”。如左传曰:“以志吾过”。《说文解字》谓“志”曰:“志,意也”。《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之所之不能无言,故识从言”。由此可以看出,汉时“志”与“识”已经有明确的区分。现代汉语一般将其理解为志愿、志气、志趣等,表示心之所向,内于心中的远而大的打算。总而言之,“志”的普遍意义为人仍未实现的志向、意念或抱负,体现出一种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
从结构来看,“志”分为上“士”下“心”。《大戴礼》说“士”的关键词为“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不可易”者即是士人的“志”。儒家重志,“志于人”、“志于道”(《论语·述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都不能降其志,说的都是主体个人的志向和抱负的重要性。至于这种内在的感性理念如何得以显现,儒家提出了以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能达到的社会理想状态为证明。在此意义上,儒家将个人追名逐利的志向自然而然地合理化。
(二)《庄子注》之“志”
据《老庄词典》统计,“志”字在《庄子》中一共出现22次(不含得志、养志等合成词)。总的来看, “志”在《庄子注》中的用法和含义包含以下几种情形:第一,虚指。笼统的志性、心志。例如:“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天地》)、“无拘而志”(《秋水》)、“志乎期费者”(《庚桑楚》)。第二,实指。明确的志向、情志。如:“贤人尚志”《刻意》 、“寥已吾志”(《知北游》)、“彻志之勃”(《庚桑楚》)。第三,通假字,通“誌”。记载,记下。如:“齐谐者志怪者也”(《逍遥游》)、“弟子志之”(《山木》)等。 可以发现,除通假字外,《庄子注》中“志”都是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与取向。
(三)“得志”:功利的取舍之间
《庄子·缮性》云:“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庄子注》解“轩冕”为高官厚禄,郭象认为这些不过是临时寄托的东西,既是身之外物,便不必为其得失而恣意放纵。与儒家相比,《庄子注》也承认“志”的意向性,但认为“得志”的本质在于出自本然,保持真性,而不是对于外物的疯狂追逐。这体现出其对主体的价值取向有了更高层面的内在性和专一性的要求。《庄子注》否定“志”的功利价值,指向得是生命的圆满与生存的自由,代表着个体独立自由的意志。
二、“心斋”:用志不分,听之以气
阐释“心斋”的意蕴及其在《庄子》中的具体意义指向,需从“心”与“斋”两字说起。
(一)“心”之释
《老庄词典》中有“心”的三类解释:一是心脏,如“比干剖心”(《庄子·盗跖》),这与《说文解字》解“心”为“在身之中”意义相同;二是心胸,如“中身当心”(《庄子·达生》);三是作为一种思维器官。古人认为心是思想、情感、意志的发出者,但《庄子》中却要“无听之以心”(《庄子·人间世》),成玄英疏“心有知觉,犹起攀援”,只有使得心寂,方能淡泊忘怀,进入道的境界。
(二)“斋”之释
《说文解字》解“斋”为:“斋,戒洁也”。《庄子》则由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引出:“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
郭象认为,“一志”即是“去异端而任独也”。成玄英表示,“异端”的根由在于心只能感受事物的表象,易为外物所迷惑。因此,“斋”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吃斋念佛,而是要去除由心而生的知觉,泯除由心而起的疑虑与欲念,使得内心洁净。
(三)“气凝”而“志一”
在中国古代哲学理念中,气是空明且能化生万物的,《庄子》所讲的“听之以气”的“气”,可谓“某种心理状态的比拟说法”。“听之以气”仅是修养过程,能够通过养“气”来保持空灵明觉的心,才能应待宇宙万物,与大道相应和。因此,“一志”,是“心斋”的前提,通过“气”的培养与凝聚,又反过来使得心志虚静专一,从而达到“心斋”的目的。
三、“心斋一志”以成圣
《庄子注》中“心斋”所要感悟的“道”,是对老子“道”的自然化,是将“道”突破了时空的界限,作为“精神生命之极诣”。而《庄子·缮性》中却写道:“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丧言隐,方督是非。儒家认为“志”能够统领主体的身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心志的展开本质来说是目的为了济世。但当主体所存在的时空都无道法可言时,个人的理想与志愿也就无法得以实现。庄子借孔子之口来释“心斋”,想要倡导的是主体面临“不显志”之时应对之法——或曰乱世存活保全之法。天下有“道”只是庄子设想中的一种社会理想状态,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无道可循。“世与道交相丧也”,对于庄子而言,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面前,剩下的也只有无可奈何的追怀与感叹了。
《庄子》外篇有一章名为《刻意》,陆德明释文中解“刻”为“削也”;“意”为“志也”。按《庄子注》之解,刻励意志只是“人道也”,仍未达到如“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庄子·天地》)一般“圣王之道”的境界。通过对《庄子注》中“志”范畴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精神领域凝气专一,虚静待物,自然无为,恰是“心斋”活动的审美过程;处于“玄冥之境”的“道”自然是郭象笔下的审美对象;能够“去离尘埃而返冥极”的圣人之德则是至高审美标准;不囿于名利,不刻意追寻目的,专心一志的“纯白者”才是郭象理想中的审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