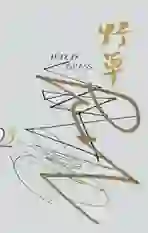我弄扁舟去了
2020-06-30张黎华
张黎华
栗河上有几条船,远远望去,像几片菜叶子。杨捉鱼从办公室出来,走到河边,看到其中一条船上站着一个女人,穿红色旗袍,人望夕阳,手机对着自己唱歌:唔喂,风儿呀吹動我的船帆。恍惚间,杨捉鱼以为是妻子,但仔细看女人随风飘拂的刘海,却又不是,想是租船拍抖音的。栗河治污,遍植水草,河水变得清澈,鱼多起来,人也敢吃河里的鱼了,不少人拿着钓竿坐在河边,对着河水聚精会神。正是春天,万物有了生气,走在夕阳下,杨捉鱼觉得人清爽了许多。流动舞台车停在文化馆旁边,边上是大片的空地。整个拆迁区只剩下文化馆和电影院,原来是挺辉煌的建筑,其他房子拆除后,没有粉刷的后墙露出粗砺的沙子,像卸妆后的女人,有些羞愧,还有些认不出自己的惶惑。空地上过去长满野草,现在铺了碎石,那些在荒草里出没的野狗野猫也不见了。几个年轻演员往皮卡上搬道具和服装,装道具和服装的箱子经了年头,橘黄色磨淡,但擦拭得干净,尚存隐隐的光泽,有个演员对着箱子甩了甩头发。杨捉鱼上了师弟的车,在副驾坐好。师弟说,哥哥好。师弟总是称自己弟弟,叫他哥哥,让杨捉鱼时常感觉自己坐在梁山泊聚义厅,山下水泊亮光闪闪,四面山风劲吹。他转头和后座上的演员打招呼。几个演员都画好了妆,小吴双眼圆睁,夕阳透过车窗照进来,他脸上的油彩有些晃眼。小吴用戏曲念白的腔调和杨捉鱼打招呼,下官吴亦凡,给杨主任请安。旁边的小姑娘噘起嘴,用兰花指点着小吴的头说,你又占我便宜,不准你再用我老公的名字。杨捉鱼笑笑,想那姑娘应是吴亦凡的粉丝,自己年轻时喜欢周星驰,他的电影一部没拉下,后来拍的烂片也到电影院捧场,却远没到粉的程度。杨捉鱼拱手叫小吴免礼,安座。车子开动,他们向着一个叫火连坡的村庄进发,师弟的老家就在那里。这次送戏下乡,杨捉鱼作为荆河戏《白衣天使》的主创,跟着剧团去看看效果。师弟导演,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角色,说,哥哥,你也要过过唱戏的瘾。杨捉鱼说行,听他安排。《白衣天使》主要讲发生在疫情期间的事,现在疫情已经散去,但那些隐痛,还留在杨捉鱼的心里。
杨捉鱼靠在椅背上,后座两个姑娘说着话,小吴时不时插两句,笑声在车里回荡。杨捉鱼按下车窗,风吹进来,同时进来的是油菜花浓郁的香味。大片的金黄一掠而过,让人想到梵高向日葵的油画。杨捉鱼想,梵高拿着那只被自己割掉的耳朵跑向原野,大片的向日葵静默不语,整个原野天堂一般,他丢掉耳朵,支起画布,专心作画而忘了疼痛。杨捉鱼有时沉浸在创作中也会忘了周围的世界,妻子在阳台上叫他,捉鱼兄,桂花开了呢!一会儿又惊奇地说,捉鱼兄,滴水观音真的滴水了。儿子在旁边学话,捉鱼兄,桂花开了呢!他听不到儿子和妻子说话,只能听见各种角色在他的剧本里叫喊。妻子也不怨怼,仿佛捉鱼兄只是她习惯性说出的名字,如果反过来说也行,譬如说滴水观音,捉鱼兄开了呢!然后拿了花洒,哼着歌给花浇水。儿子在旁边蹦蹦跳跳,跑到书房,像猫样蹭上他的腿。
不知不觉间,火连坡到了。村庄紧挨一座石山,村民房屋沿山而建,外墙都刷得雪白。一块巨大的岩壁像是人工凿就,高悬于村庄之上,下面是一大片空坪。流动舞台车开到空坪中央,后厢挡板铺展开,六米宽八米长,是个简易舞台,没有后台,没有化妆间,两侧搭了铁梯,供演员上下。月亮在树梢上,整个村子朦朦胧胧。空坪里没有什么观众,几个小孩子正追赶打闹。倒是有个小伙子,袖着手,两挂鼻涕像火车在隧道里进进出出。走过来两个老头,一个头发全白了,佝腰拖着一个音箱。音箱装了滑轮,像一个拉杆箱,可能是平时跳广场舞放音乐的。另一个老头穿着米白色夹克,也许是月光的缘故,脸上皱纹不太显眼,看上去不那么老,拿着话筒喊,王娭毑,李老倌,县里送戏来了,来看戏。师弟过去和他们打招呼,白发老头问,毛头,今天唱什么戏?师弟说唱《白衣天使》。老头说喜欢沉香,想看《劈山救母》。师弟说下次送戏的时候再唱。小伙子走过来,把袖着的手拿出来和师弟相握,说,王毛头,我代表党和人民感谢你。师弟说,首长辛苦了,应该的应该的。两个老头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滑轮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声响,但很快被喊话的声音淹没。疫情泛滥时,杨捉鱼看过一些地方的宣传视频,条件好的开着小车,打开天窗,拿着喇叭喊话,条件差的坐在三轮车里敲锣喊话,火连坡这里可能是拖着音箱喊话吧。杨捉鱼问过师弟,那个显得年轻的老头果然是村书记。师弟说,哥哥,年轻人都出去了,条件好的在兰城买房安家,家境差的继续在外打拼。杨捉鱼问,那年轻人怎么回事?师弟说,小时发烧,没想到是脑膜炎,耽误治疗了。说话间,小伙子的母亲走过来,披了一件衣服在他身上,又用手轻轻拂去他头发上的草屑。
舞台上响起锣鼓,二胡的声音也响起来,小姑娘们咿咿呀呀地试音。一会儿之后,稀稀拉拉来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月光渐渐明亮,演出开始。两个小姑娘扮演护士,白衣,白色燕尾帽,在舞台上如穿梭般急速行走。杨捉鱼反串不太讲情理的婆婆,媳妇被抽调到发热科,婆婆却不想让她去。杨捉鱼亮相,念白:
太阳出来一把火
那恶婆娘就是我
念完白,杨捉鱼突觉心酸,排练时没这感觉,现在忽然有了。一瞬间,杨捉鱼觉得母亲到了他身后,轻手轻脚,如灵魂越过空谷。当初写剧本时,杨捉鱼想过母亲,她有时的确有些不讲情理。父母经常吵架,就像饭后抽烟或者吃一个水果样,不会激烈到动手的程度。但两个人嘴巴上都挂着刀子,刀光往对方的心窝猛扑。在杨捉鱼看来,很多时候是母亲不讲情理。鬼节时,父亲到月台买纸钱回来,母亲说他一坨晦气,看上去是被悖时鬼附体了。父亲回一句,被你附体了。母亲气得不行,刀子连绵不绝,一把把飞向父亲。表弟刘成功消失那年,父母离婚,母亲一个人搬出去。父亲像是习惯了刀子扎心,离婚后桌上总摆着酒,对面凳子上坐着杨捉鱼小时玩过的布猴子,是母亲给他的生日礼物。父亲举起杯子和布猴子说话,有时轻言细语,有时恶语相向。父亲没想到,酒是更厉害的刀子,过肚穿肠,竟把他扎倒在仙眠洲上。母亲后来找了个老头,看上去精神了不少。从办公室望出去,杨捉鱼能看到母亲在兰城公园跳舞,广场舞,鬼步舞,都能来。母亲跳舞特别投入,跳《小背篓》,歪着头,把手贴在脸上,神情天真,像是回到了幼儿园。杨捉鱼有次看到母亲和老头背着几个布娃娃,背影欢天喜地,想是刚从超市里抓的。有次突然接到老头电话,说,你母亲殁了。杨捉鱼回不过神,问老头,母亲怎么了。老头又说,心梗,送到医院就殁了。等杨捉鱼赶到医院太平间,母亲已经睡在水泥台子上,双眼紧闭。她穿着一件底色青黑的寿衣,上面有五只蝙蝠围着一个变形的寿字。母亲爱美,她一定不喜欢这种俗气的衣服。杨捉鱼想到小时候,母亲总是打扮得清清爽爽,有条连衣裙,上面缀着淡蓝色的小碎花,母亲喜欢,杨捉鱼也觉得好看。母亲叫他,幺儿,肚子饿不饿,妈妈给你煎鸡蛋。幺儿,把衣服穿好,不冻着了。长大一点,母亲叫他的名字,杨卓越,作业做好啊。母亲带着芷城那边的口音,听上去像是在叫他杨捉鱼。在殡仪馆,杨捉鱼看到母亲从烟囱里出去,他跑到外面,一道青烟直直地往天上走。青烟中传来母亲喊他的声音,幺儿,捉鱼。声音隐隐约约,似有无限委屈。杨捉鱼还是把母亲的骨灰盒和父亲的放在一起,心想,在僻静的仙眠洲,两个人争争吵吵,总好过那冷火秋烟般的寂寞。得闲时,杨捉鱼骑上单车,然后喊船过澧水,过河后穿过大片的草丛,在父母坟前坐下,看书,看云,看风梳理野草。他想在坟前栽一棵树,再弄一个木质长椅,鸟儿在树上栖息,自己坐靠长椅,在树木摇曳的浓荫里构思剧本,或者什么也不做,就在长椅上睡一觉。
儿此去不是为把名扬
儿此去也不是保边疆
儿此去也似是上战场
儿此去啊,为的是把病毒杀光
两个小姑娘侧身站立,右手曲拐前顶,上臂和小臂形成一个三十度的角。杨捉鱼对媳妇挥手,目光满含眷念,望着她走入木板后面的医院。走下舞台,杨捉鱼闻到更加浓郁的油菜花香。不远处有一排树,高高低低,在月光下影影绰绰,如山岭起伏的轮廓。舞台上,扮演媳妇的护士照顾小吴扮演的病人。在隔离病房里,小吴胡搅蛮缠,一会叫护士给他拿这个,一会叫护士给他拿那个。小吴的家人托人给他送来一盒饭,小吴叫护士给他打开。护士听到有人在喊,看了小吴一眼,匆匆地跑开。小吴的病情突然恶化,呼吸急促,竟然死了。护士过来,看到病床旁边的柜子上搁着那盒没有打开的饭,看着小吴,内疚地哭出声来。
杨捉鱼和妻子开了一瓶红酒,正是黄昏,夕阳的余晖从北窗进来,静静地铺在餐桌上。两杯酒喝下去,杨捉鱼笑话说妻子像个灯笼,里面红烛摇曳。妻子反驳说,你呢,炸弹黑。儿子坐在地上玩拼图,听到妻子说炸弹,问哪里有炸弹。正说笑间,妻子接到电话,假期取消,要回医院上班,并要求她做好十天半个月不回家的准备。妻子收拾换洗的衣物,出门时,抱起儿子亲了又亲,又和杨捉鱼拥抱。妻子拉着箱子等电梯,杨捉鱼望着她。电梯到了,妻子向他挥手,要他在家照顾好自己和儿子。
如果我没回来,那就是弄扁舟去了。
电梯门缓缓关上,杨捉鱼看到妻子的笑里隐藏着一点落寞。
以往,杨捉鱼和妻子讨论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妻子说想开一家奇异服装店,卖各种各样奇异的衣服,譬如益智衣,穿上就是高智商,或者是治愈衣,不管什么病穿上这衣服就好。杨捉鱼说,我想要一件隐身衣,随时躲在里面,谁也看不到。妻子看看杨捉鱼,说可以考虑给他穿一件疯衣,这样周末的时候可以到合口精神病院去探望他。我眼泪汪汪,你一脸迷惘,好玩。妻子被自己的想象逗笑了。杨捉鱼说,说点现实的吧。妻子蹙眉思考,说,想到河里划船。杨捉鱼想想,在河里划船也是挺好的,阳光,一点点风。他说,到河里划船有什么稀奇的?只要得空就可以去。妻子说,划船时会想到小时候唱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杨捉鱼说,划船的时候我唱给你听。妻子说,也不是一定要唱那首歌,只是想到那句歌就会回到童年,无忧无虑,一脸阳光。杨捉鱼知道妻子的压力比自己大,于是对妻子说,李白说过,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妻子唱了李荣浩歌曲中的两句:如果时光能重来,我想学李白。又说,我喜欢这个,弄扁舟,我要弄扁舟。妻子问他最想什么,難道是克罗地亚的白鹳?陈美娣早已回到克罗地亚,两人很少联系。有时看她发朋友圈,不管什么内容,杨捉鱼只是默默地点个赞。自己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去年秋季在石首天鹅洲,他去领一个民间的麋鹿剧本奖。举起奖杯的瞬间,几只天鹅在河边的滩涂起飞,洲上芦苇摇曳,其间似有麋鹿出没。台下响起掌声,就在那一瞬间,他体验到以前从没有过的愉悦和成功感。难道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一次次举起奖杯,想想却又不是。他想起加缪《鼠疫》里的一句话:他们现在知道,要是说在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向往,并且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于是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弄扁舟。这句话过于柔情,妻子仰头,似要把泪水逼回去,一会却又笑了,眼睛看向卧室的方向,说,走啊,捉鱼兄,弄扁舟去。
卧室里没有开灯。杨捉鱼拿出手机,十一点二十三分。月光把窗台栏杆的影子投射到被子上,像是无边原野里的黑色栅栏。他走到窗台边,把手拢起放在嘴上,黑色栅栏边出现了一个无声呐喊的人影。他又望向窗外,街上店门紧闭,只有路灯还亮着。栗河小桥桥拱装了霓虹灯,以往看去像挂在桥上的彩虹,此刻靠近南岸的灯可能接触不良,熄灭了,但北岸的半边彩虹闪烁,像不停向舞伴伸出手的舞者,但舞伴坐在黑暗里,永远不肯伸出应答的手。月光明亮,能看到远处澧水河对岸的大堤,一辆摩托车从东往西走,车灯如同骑车人提着的小小灯笼。车子往高处走,缓慢,从容不迫的味道,车灯变成天上的一颗孤星。街上有人大声唱歌,你和他还在藕断丝连,让我心底的爱火熄灭。可能是从夜市归来的饮者。这样看了一会,还是没有睡意。他有点想儿子,昨天打电话吵着要回来,说外婆家里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一点都不好玩。杨捉鱼正写一个剧本,兰城木器行的少爷早年留学日本仙台学医,隐约见过鲁迅先生。少爷在日本生情,并留下一子。后回国继承祖业,守着一铺子木器过日。抗战爆发,兰城沦陷,成了中年男人的少爷没有逃走,每天还是靠在柜台上看天空。一个春日午后,他点燃一支烟,突然发现几米外,有个日本兵端着枪对他瞄准。闭着左眼,左脸肌肉往上提,嘴角略向右歪。那人眉眼有说不出的熟悉和亲切,他心里咯噔一下,是当初留在日本的孩子。右边脖子里的黑疤,自己也有一块,像跳跃着的黑色火焰。他有些愧疚,只记得儿子两岁的时候,在松岛湖带他划过一次船,当时樱花盛开,白色水鸟绕着朱红色的福浦桥飞来飞去。女人微微仰起脸,去嗅飘来的樱花香,儿子却在桨声花影里睡着了。剧本写到这里卡住了,是让枪声响起,还是就到这里戛然而止,他拿不定主意。从剧本里出来,杨捉鱼想,儿子长大后会不会理解他和妻子,会不会对他举起枪,里面装满冷漠做的子弹,然后对着他一个点射。
杨捉鱼又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给妻子发了一条信息:我弄扁舟去了。
走到小西门,街上车辆稀少,偶尔经过一辆,如同腾起的烟雾倏忽远去。过铁路道口,杨捉鱼想起表弟刘成功。年少时,两人常在这边玩耍,有时沿着铁轨走出很远,铁路边是陌生的村庄,看着昏黄的阳光,杨捉鱼常常以为到了另一个世界,但又有一种曾经来过的感觉,特别是两个白色的烟囱,如在他的梦里吐烟。刘成功把耳朵贴在铁轨上,然后告诉他火车就要来了。两个人站在铁轨上,等火车靠近的时候才跳下来。如果你还在,杨捉鱼嘀咕了一句,还会不会和我一起站在铁轨上?铁轨在月光下闪着冰冷的光,杨捉鱼看到刘成功赤脚在上面走了一个舞蹈里面的跳步,像是走钢丝的人炫技。他给妻子发了一条语音,快到河边了,船老大在催我呢,还说我神经病,深更半夜划什么船。船老大你知道的,发小,上次喝多了,我送他回去,他吐着酒气,说要给我集资二十块给你拉双眼皮。他这是笑话你眼睛小,哈哈。他点开自己的语音,声音听上去有点奇怪。突然来了一阵风,天上的云一会儿把月亮完全笼罩,一会儿又把月亮放出来。光影隐现,杨捉鱼感觉自己走在某部戏剧中。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但光不是总追着我。杨捉鱼又给妻子发微信。儿子出生是一道光,可是我们的狗却走了。你说那只鹦鹉是不是和狗产生了感情,狗走后,它竟然不吃不喝,还在那里模仿狗对着门叫。汪,汪。杨捉鱼又点开自己的语音,汪,汪,声音冲出手机屏幕,在夜里蔓延。
河坡上青草薇蕤,杨捉鱼看到草丛里有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个光头。他心里咯噔一下,仔细看看,是个模特,椅子是可以升降的理发转椅,凳面破烂,黄色海绵包抄了模特的屁股。走到一棵垂柳下,杨捉鱼用荆河戏里白素贞的腔调喊,船家,过河则个。我靠,捉鱼兄,你终于来了。水也要睡觉的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的感受?一条黄色的胡子鲢坐在河边,嘴里的烟头明明灭灭,声音却是船老大的。走近一看,船老大穿了一件美人鱼的衣服,水气弥漫,鳞片闪闪。吓着你了?老子今天临时客串了一把美人鱼,来不及换衣服就被人拖去喝酒了。游客说,没见过这么丑的美人鱼,我靠。要脚踏船还是小划子?杨捉鱼要了小划子,心想,脚踏船是哪咤的,他会唱让我们踩起双轮。
河水和月光浩渺一片。杨捉鱼觉得自己在月亮里行走,但他意识到月亮里只有无尽的荒野,并没有桂花树。妻子如果在月亮上,不会喊他,捉鱼兄,桂花开了呢。那她会说什么呢?妻子不是矫情的人,肯定也不会说,啊,捉鱼兄,你看,无边无际的荒野。妻子会说什么呢?代表月亮消灭你?他使劲想,总找不到一句适合妻子的台词。小船往前走,能听到水草轻舔船底的声音。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反复哼着这句歌词。妻子说唱这首歌能回到过去,他恍然觉得,左边的河水是过去,右边的河水是未来,正对着的河水便是此刻。妻子在左边,委屈地给他打视频电话。网上有篇文章,说妻子作为医护人员,为人冷漠,工作不负责任,连给病人打开饭盒都不愿意。病人有力气还会求你吗?可怜的病人,临死前连吃一口饭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捉鱼兄,我想弄扁舟。
我和儿子都在等你,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弄扁舟。
捉鱼兄,你还记得天主教堂吗?
杨捉鱼当然记得,有段时间,他创作陷入瓶颈,想找个地方使自己安静。朋友给他在兰城西郊的天主教堂安排了一个房间,他晚上有时就住在那里。有次妻子去看他,他们沿着教堂外面的小路往北走,一直走到小山上。火车穿过脚下的隧洞,蜿蜒远去。从山上往下俯瞰,兰城灯火辉煌,两人心里生出无来由的感动。西风穿空而过,杨捉鱼从后面抱紧妻子,下巴抵在她肩上。看向四周,塔吊林立,在建的高楼在夜色里好像端着枪。妻子说,如果那些塔吊开火怎么办?杨捉鱼走到妻子前面,说,我给你挡著。回来时,教堂被夜色掩映,高大的门墙一片模糊,只有屋顶的十字架闪着光。妻子说教堂像他父亲的药箱。捉鱼兄,奇怪的很,到教堂怎么就像到医院上班一样?杨捉鱼说因为医院也有十字。妻子又问,你知道医院为什么以十字架做标志吗?杨捉鱼隐约知道一点,好像是某个传教士把国外的医术引进中国,救了很多人,后来建医院时,把十字架作为标志,这样一路沿用下来。
杨捉鱼对妻子说,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妻子在手机里叹息,说,我也需要救赎。
杨捉鱼正想安慰妻子,她却把电话挂了。
小船到了多安桥,桥的右侧以往是殡仪馆,拆迁后,连同附近的几十亩地都栽了桃树。据说桃木有辟邪功效,这样鬼魂便不会在此作祟。桃花开时,不少人在里面赏花,拍照。杨捉鱼想,赏花的时候,妻子会不会像他剧本里的日本女人一样微微仰起脸?她的眼睛细长,倒是和樱花很配。
河水突然一阵响动,水花翻涌,一条银色的鳡鱼跃出水面。鳡鱼上坐着一个人,穿黑色西装,里面白色衬衫上打着黑色领结,像婚礼上的司仪。再仔细一看,那人手里拿着布猴子,正是父亲。杨捉鱼喊,爸爸,你怎么在这里?父亲脸上表情模糊,声音却很清晰,我和你妈妈抓娃娃去,她现在对这个特别上瘾。杨捉鱼说,你们现在还好吗?父亲说,很好,你妈妈现在对我百依百顺。杨捉鱼说,妈妈说你两句,你就受了吧,不要老是争争吵吵。父亲说,儿子,你的心也要放宽一点。杨捉鱼说知道。过了一会,母亲也来了,她骑在一条细长的针嘴鱼上。那鱼黑背圆颌,像杨捉鱼有次上班时见到的一只鸟。那天,他走到二楼半楼梯时,听到砰地一声。他快走几步,上到三楼,一只鸟躺在地上,长喙无力地搭在地面,身边血迹洇染。过了几天,杨捉鱼又看到同样的一只鸟,个头略小,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像是在寻找什么。鱼是水里飞行的鸟,杨捉鱼不知是从哪里看到过这句话,他想,鸟死后都会变成鱼吧,或者,鱼死了,它的灵魂会化成鸟在天上飞。母亲说,我到太平洋去了。杨捉鱼想起自己大概七八岁时,母亲带他到河边放风筝。看着浩渺的河水,他问母亲河水流到哪里去。母亲说,百川归海,最后到太平洋。杨捉鱼当时想着自己坐着木盆在水里漂荡,最后来到太平洋,海水无边无际,只有无数鸥鸟翻飞。杨捉鱼喊妈妈,母亲看了他一眼,没有和他说话,她捏捏针嘴,鱼像摩托艇一样划开水浪。父亲在后面喊,败家娘们,等等我。杨捉鱼眨眨眼睛,水面平静,阗寂无声。也许,我出现幻觉了。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大声唱了一句,却惊起岸边树上的宿鸟,唱你妹啊,把老子吵醒了。咿呀一声,鸟又向另外一棵树飞去。
杨捉鱼坐下来,头靠在船舱挡板上。任意东西吧,他想。拿出手机,仔细看儿子画的一幅画。河岸线穿过抽象的房屋,岸边的树上飘着一朵云,在洁白的纸上投下一团模糊的黑影。一只白鹤脖子扭成S形,扭头啄自己的羽毛。白鹤旁边立着一条坚硬的裙子,裙子里没有人。河岸线下面是弯弯曲曲的河水,一条针嘴鱼站在河水中,嘴上的针像吸管伸出水面,吮吸河面上的青草气息。河水的最下层,一个女人张开双臂划水,闭着眼睛,脸孔洁净,长发被河水冲刷着,杨捉鱼甚至能感觉到它在飘动。儿子那天画完后给杨捉鱼看,杨捉鱼问水底下是谁。儿子说是妈妈,妈妈在游泳。那爸爸在哪里?儿子指指树上的那朵云。我不是男人,是穿裤子的云,他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抱着儿子,他的鼻子有点酸。
起风了,四面都是飒飒声。他把风声发给妻子,妻子的手机在他口袋里呜呜震动。岸上的桃花一片片飞过来,不一会便铺满了河面。杨捉鱼看到妻子的脸在桃花中隐现,他掉转船头,慢慢往家的方向划。
【责任编辑朱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