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初美国见闻
2020-06-29沙博理任东升
沙博理 任东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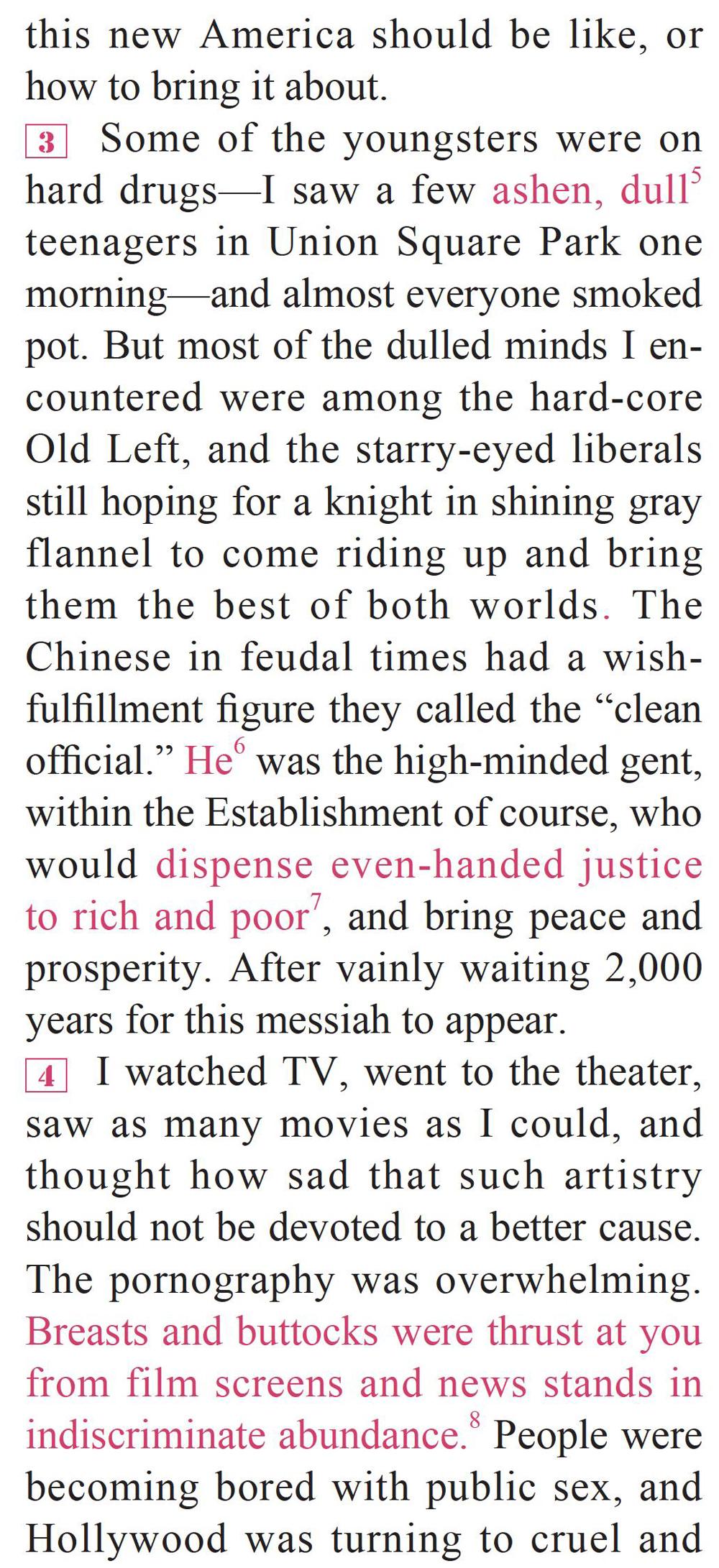

随后的几周,我发现变化真不小。有些变化我是喜欢的,如立体声调频收音机播放的美妙音乐,便宜小巧的电视机,缩短旅行时间的高速路和飞机,便宜实惠的家用小件,合成纤维布料的衣物,样式新颖活泼,富于想象,还有便利的超市和气派的新写字楼。
2我最乐见的还是年轻人。美国人向来有话直说,现在好像还特别振振有词。我遇见的孩子身上没有一点儿“垮掉”的样子,他们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者持批判态度。他们希望有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观,但没几个人清楚这个新美国该是什么样子、又该如何实现。
3有些青少年吸上了容易上瘾的硬毒品,一天早上我在联合广场公园看见几个面如白蜡、精神萎靡的孩子。至于大麻几乎人人在抽。但是,我遇到的精神不振的人多是铁杆“老左派”,还有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依然期盼会有身穿闪亮灰色法兰绒的骑士策马而来,把两个世界里最好的东西带给他们。封建时期的中国人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称之为“清官”的人物身上。他们是不论贫富都施予正义的君子,能够创造和平与繁荣。当然,他们都是达官贵人。然而空等了两千年,这样的救世主也没出现。
4我看电视,去剧院,电影能多看就多看,深感这样的艺术形式没有用在更好的事业上是何其悲哀。色情泛滥,从银幕到报摊,坦胸露臀的照片比比皆是,充斥眼球。人们对银幕上的情色场面已不感兴趣,好莱坞便把镜头转向残忍血腥的暴力,想要撑起日益萧条的票房。
5我和杰里·曼在加州待了两周,多年前,我曾和他扒乘货运火车横穿半个美国。如今他已是一位成功的女士运动装制造商,住在好萊坞山上。他有一所漂亮的宅院,电话线可以拉到肾形游泳池旁,有个菲律宾男仆给他做饭,墙上没挂任何照片。杰里跟杰伊·韦斯顿合住这所房子,杰伊是个电影制片人,当时在制作一部片子。原来有12家电影制片厂,现在只有3家大的留了下来。两个人都离婚了,没有孩子。他们都很聪明,为美国所走的道路苦恼,但是又太“讲求实际”,或者因精神疲惫,就不想改变什么。
6笼统而言,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社会良知、有艺术才华的,普遍厌倦了自己当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老一辈倒是有那么几个奋起抗争,但为数不多。还有些人干脆妥协,及时行乐。有那么一两个勇气可嘉的在谈论逃离。纽约一个拿高薪的电视编剧对我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全家移居巴黎开一家熟食店,尽管他们家在中央公园西路有一套大公寓。
7这些人大多是富裕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相对而言还是少数群体。绝大多数人还是像我印象里那样,一大早就挤地铁,一整天就伺候一台机器,或者做一些不用思考的办公室工作,然后在交通高峰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将就一顿“经济”晚餐,而后看一通电视上虚构的煽情节目,这才上床睡觉。失业和半失业的人住在满是害虫又漏风的贫民窟里,他们对只管收取高房租却拖延甚至不给修缮房屋的房东心怀怨恨,直到贫穷和悲惨的境遇无可避免地把心中怒火逼得爆发。我在布朗斯维尔和贝德福德一史岱文森就看见过烧毁的房屋残骸。
8纽约还是有新生机的,这多亏有大量新鲜血液的注入,主要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我的母校詹姆斯·麦迪逊中学的黑人学生约占三分之一。地铁里挤满了往返于各个学校的孩子,他们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滔滔不绝。每当警察跨进车厢,车厢里便立刻静下来。警察日夜在地铁巡逻,总是两人一组。这时通常有半数孩子很快在下一站下车,经验让他们对警察又恨又怕。白人迁居郊区之际,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进了城。这些人对纽约而言是建设性力量还是破坏性因素,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他们。种族关系高度紧张,这对城市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9我感受到,不光是穷人,就连整个社会都陷入团顿、裹足不前。孩子们在学校学不到多少与他们和他们的问题“有关的”东西。国家领导层在推行一成不变的政策,鲜有成效。工作枯燥乏味而且很难找。老百姓对美国在越南制造的杀戮以及国内大街上的凶杀深感厌恶。
10人们必须给房门安装两三道锁,最好还养条狗。晚上不敢在公园里散步,老太太们在公寓的走廊和电梯里会害怕,女孩子无论何时何地都须留神。即使有一辆轿车,曾在路上飞如魔毯,现在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汽车实在太多了。公路上拥挤不堪,交通阻塞司空见惯。停车场收费昂贵,离上班地又很远。大部分人平日里干脆把汽车留在家里,停在房子前,因为车前车尾有花哨的护板,车身过长塞不进老式车库。
11至于精神食粮,那就几乎谈不上。电影拍得那么糟糕,人们不再去看。朋友们告诉我,他们确实多年没有看过电影了。附近一些剧院过去每天连续演出12小时,现在只在晚上和周末开放几小时。戏剧内容通常毫无意义。我去看过一场外百老汇音乐剧,戏台上竞反反复复地唱一句“越南人也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那就只剩下电视了,确实,播放的球类比赛还挺好的,“搞笑”节目也挺棒的,还有原封不动照搬午后电台节目的煽情肥皂剧。人们有了电视,谁还需要宗教这个“精神鸦片”呢?
12压抑人们快乐的最大因素是通货膨胀、物价居高不下。像样的两居室公寓月租绝不少于150美元;过去理一次发50美分,现在得5美元;原来只要5关分镍币的地铁票现在要35美分;原来10美分一个的汉堡包现在得50美分,连面包圈也不给烤一下。(1971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离谱了,我还是照着1947年离开关国时的物价来考量的。)这不是一个与邻居攀比看齐的问题,而是自己能否活下去的问题。普通美国人不敢丢掉工作,他们不得不循规蹈矩,在“自由”的社会中被迫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
13阔别美国25年,我看到了实用的小玩意和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然而却没有看见多少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