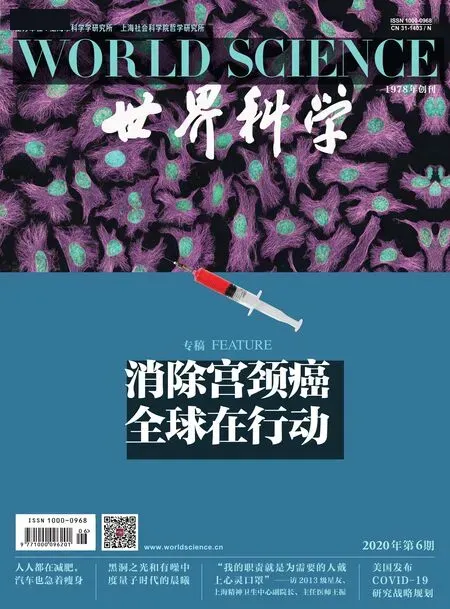心在云上
2020-06-28编译姚人杰
编译 姚人杰

“云”作为一个科技用语,人们对它已经很熟悉了,比如云计算、云服务等等。按照某些业界人士的说法,一切数据都可以放在云上,给人类带来便利。假如有一天,人类自己也被放入云端,那会怎样呢?在科幻文学中,人类将意识上传,以虚拟存在的身份生活下去并不是新鲜的概念。这篇《心在云上》结合热门的“云”概念,给故事增添了一些新意。
我躺在沙地上,不停地哆嗦,同时纳米云蚕食着我的躯体。我没有感到一丝痛楚——我的神经软件确保了这一点,但我的躯体继续因肌肉反射而抽搐,任何一个被“粒子子弹”抹除的人都会这样。纳米机群降落的时候像一朵黑色的金属云团。它们比物质更像液体,慢慢地吞噬我——骨骼、肌肉、筋腱、鲜血、每个原子、每滴汗水。其他士兵的呻吟与叫喊穿过硝烟与沙砾,传了过来,他们也在渐渐被自己的“云”吞噬殆尽。敌方的炮火在远处隆隆响起。
等到纳米机群到达我的腹部时,我想起了妻子莉安娜。等到云吞下我的胸膛,变成黑色闪烁的方块时,我想起了女儿妮娜。我寻思着,我是不是永远再见不到妻子和女儿了,我是否没机会道歉了。
像深太空一样浓深的阒黑吞噬了我的胸膛、喉咙和脸庞,就像柏油一样。我想要尖叫,然而它已经吃掉我的嘴巴。沙滩、尖叫声、陌生的天空,一切都眨眼间消失了。突然,我被关入一家医疗诊所。白色的无菌墙壁旁,机器污迹斑斑。但我什么气味都闻不出,无法感知我的心跳、呼吸和生物节律。
我飘浮在半空中,我没有躯体。
我想要尖叫。我能感受到恐慌在胸膛中扑动,只是我没有胸膛。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某人迈步走进房间。
“利亚姆·芬彻吗?你重启得比我们预计中更快。”她告诉我。
重启?我尝试询问。“从云中重启。”她说道,仿佛我已经成功一般,“我是尤科弗博士,负责这个站点的纳米技术部门。我很抱歉,我认为别人没有正确地向你解释你万一早逝后将会发生的事。”
只是,确实有人解释过了。记忆汹涌归来: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在那间又冷又暗的房间里,被植入神经软件点阵。我们被告知,假如我们的躯体超过可维修状态,我们的生物质会被归入云中。也就是“人类之云”。我们的躯体和意识会保存于远程存储器中。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这个愚蠢的事一笑了之,为纳米蠕虫选择了名字。只是,我现在笑不出来,哭不出来,甚至叫不出声;现在我是一团黑暗的、颤动的质量,就像金属般的黑色卵石。我以前从未留意过我的心跳或呼吸。如今,它们消逝了,我不敢相信它们留下了一个多么大的空缺。
“从实际存在角度来说,你已经死了,但你的意识仍然存在,你的身体也仍然存在。” 尤科弗说道,“你和另外数百个人处在相同的状态。他们都在学习如何取回身体。我会演示给你看。”
她确实那么做了。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学会如何控制每块“云碎片”,它们像突触一样,是我的一部分。两周内,我就能将我的身体组合成肉体形态,比如我的古铜色肌肤、乌黑头发、柔软的手脚,甚至连我左侧面颊上的胎记也没落下。这些全都是存放于远程存储器的数据。我永远不会衰老,永远不会再长出哪怕半寸头发。我相当于停滞了,但起码我还活着。
不出两个月,我就能在数秒内从人类形态分解成旋转无休的“云”,在半空中安逸自在地移动。不出三个月,我就能讲话了。“我的家人知不知道我还活着?”我的嗓音变形失真,就像出故障的无线电信号,但这是我的嗓音。
“他们知道,”尤科弗的面庞抽动,挤出笑容,“他们很快会来见你。”
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来看我。这家机构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允许获知这儿进行的事。假如被伦理委员会获知,他们会大干一场。我永远无法离开这个地方。
我开始让我的“云”体积越来越小,轻巧地探索隐藏的裂罅、缺口和通风口,这些地方本来应当是锁闭的。直到最后在某个晚上,我的整个形态都冲了出去,先是爆裂成一百个不同组件,等出去后再次结合成为黑色的云。等到警报声响起时,我已经在去往我姐姐家的半路上。我想象着他们会说什么,我又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这件事。
我像蜂群一样飞到姐姐的红砖房屋。我从窗户窥探房内时,我的云形态化为人类形态,就像液体凝固成固体一样。壁炉台上摆放着我的照片,我自己的脸庞从照片里回视着我。我的家人绕着彼此走动,身穿黑色衣服,拿着瓷质餐具的手指颜色惨白,莉安娜从来不用这套餐具。
我的妻子莉安娜比我记忆中更老些,接受着对我死亡的吊唁。“他心肠那么好,”一位我报不出名字的亲戚这么告诉她,“只要他愿意,他总是那么敏感又温暖。”
莉安娜强颜欢笑,不顾睫毛膏化开的晕染:“是啊,他在许多方面都很好心。”
她对哀痛的亲戚们说了这句话和十多句其他言语。仿佛我没有在某些晚上醉醺醺地回家过,仿佛我发火时没有扔出玻璃杯砸中她的脑袋似的,仿佛当她找出我吸毒用的针管后,我没有说出那些可怕至极的话,仿佛多年以来我做过的数百件并非故意、但破坏程度没有减少的小事压根不存在。
但她选择不去记起我的那一面。也可能是悲伤盖过了其他所有事,透过玫瑰色的玻璃过滤了我这个人。头脑的潜意识夸大好的一面,对坏的一面就轻描淡写。
我不想为她打破幻象。
我飘浮到女儿的卧室窗口。妮娜从娃娃身上抬起视线,向上瞄时刚好看到窗帘飘动。但她没有看见我顺着天花板一点一点挪动,将我的云形态散布到落地柜上。我不敢相信她长得这么大了,又不敢相信她的模样这么像我。
妮娜拂去沾着脸庞的深色头发,重新蹲到娃娃面前。“他们在说谎,”她告诉毛绒猪玩偶,那是我离开时买给她的礼物,“爸爸仍然在外面。他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
我的胸膛本该存在的地方,有些东西在内部撕扯。有那么半晌,我还以为自己依然拥有心脏。
资料来源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