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路过诗坛
2020-06-21孙凌宇
孙凌宇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林白
生于广西北流,现居北京。曾经插队,当过中学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先后在图书馆、电影制片厂、报社、文联等单位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 《一个人的战争》 《说吧,房间》 《婦女闲聊录》 《万物花开》 《北去来辞》 等多部。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首届女性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提名。有日、韩、意、法、英、西等文字的长篇和中篇单行本出版。
事情发生在2月初,小说家林白开始写诗。北京下着雪,书桌却无法冷静如初。这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谁也没料到,诗,不再是小桥流水般温婉抒情,而是又猛又躁,如飓风降临,并且持续汹涌——用她的话说,这是一次“炸裂式写作”,这样一种激烈状态在她六十多岁时突袭而至。
这次的爆发由新冠病毒引燃,“不得不写”,从立春一直到立夏。林白毕业于武汉大学,后来又在武汉市文联工作了十年,2005年搬到汉口,就住在距华南海鲜市场10分钟的发展大道荷花苑。离开已有四年,但她仍不能感到侥幸。
疫情期间,她的心格外被揪扯。武汉有她的朋友、同学、同事,湖北浠水有她作品《妇女闲聊录》里的主人公木珍,同学的亲人是中南医院消化内科护士,后来去增援雷神山医院。她每天听到种种消息,情绪翻滚,溢到笔尖。
全身发抖,哭完决定继续写
2月7日写下第一首,《二月,所有的墨水不够用来痛哭》。本以为是一次性表达,结果第二天早上六七点起来打坐,双盘四十分钟后,诗句又自然涌出。
她充分体会到了美国诗人W·S·默温总结的“写诗从来就不是一项你能够完全控制的行为”。1976年,默温避开人群与社交,隐居夏威夷毛依岛,潜心写诗。在夏威夷的家中,他经常身着一件长衫,打扮得像个禅师,甚至专门备了间禅房,供每天两次打坐之用。
早期林白也“完全不受控”,似乎只负责提笔和打坐,“句子都是自己出来的”。写完第二首后,她发给《收获》杂志,那段时间他们的公众号刚好也在推送诗歌。推出来后,林白转给一些朋友看,结果一半的人都表示反对。
其中有位老朋友劝她不要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写诗,“这件事超出你的感受与思考方式,超出你的擅长领域和驾驭能力。你本身不是思辨的,不是理性的,不是反省的,不是意识形态的,更不是现实/政治的,所以最好放下这个事,不要去梳理了。已然发生的不用去管了,继续写你原来的东西,在疫情中照看身体和家人。”
“诗歌当然不算我擅长的领域”,林白认同。即便她二十多年前就写出了“一般文艺青年都知道”的《过程》,几年前辽宁人民出版社还为她和汪曾祺、贾平凹出版过“小说家的诗”,但她始终不敢妄称自己为诗人,多次说自己只是票友,从诗坛旁边路过而已。
出于另一些难以解释的原因,这番劝阻令她感到非常难受。第二天打坐的时候,她全身发抖,眼泪哗哗流。哭完决定继续写,朋友巫昂的话很大程度上释怀了她:“任何时候写诗也许都是残忍的。”
第三首诗的诗名体现了这番一意孤行的态度——《记录吧,你》,决绝与义无反顾,口吻如同她1997年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
二月的舌头己生锈
再不开口就来不及
记录吧,你
把诗忘掉
这首写完,“人就比较顺畅了”。《收获》连着推送了三次,每次都是上午写完,中午修改,傍晚发过去,晚上便推出来。林白回忆,是对方把她的状态像“三级火箭”一样推到了轨道上,之后她便继续飞速旋转。
后来她完全不给公众号推了,写诗却未因此间断。每天内心依然激荡出很多句子,朋友们渐渐也就不说什么了,“反对我写诗的,我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就不联系,主要是没有精力。”林白每天上午写诗(必须手写,才写得出来),快的几分钟,慢的半小时,写完一首,直接在本子上修改。改完了做点家务,打打太极,午饭后小睡一会儿。
身处武汉的作家同学寄来Paperblanks(爱尔兰古典笔记本品牌)的本子给她写诗,说:Paperblanks号称自己的本子可以存放两百年,想象2220年人们发现你写的东西,像读历史一样读着诗稿。
林白嫌本子太小,照旧用女儿送的将近A4纸大小的厚本子写。绿色封面的早就写完了,现在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40周年的酱色纪念册,里面印着鲁迅、莎士比亚、雨果文集等图案。三个月来,她写了超过100首,本子只剩几页空白。每天修改完,就用手边够得着的东西压住摊开的笔记本一角拍照,将当日作品发到朋友圈和微博。有时用木质物件,有时用石头,有时干脆用整棵未剥的大蒜。
几年前,她将微博名改成“老林白”。这是格非大概10年前对她的称呼,她觉得受用,因为“老是很有分量的”。随诗发布的常常是自己的旧照片。4月29日,写到第90首时配的是一张13岁的照片,两个小辫儿,发型虽稚嫩,眼神却透出成年人的拘谨。如今,她对外用得最多的照片是去年夏天女儿在家中为她拍的黑白照——大而凹的眼睛瞥向窗外,显出宽阔且清晰的下颌线,像越南女人一样有着突起的颧骨和扁榻的鼻梁,在利落短发衬托下,眼神坚定而强硬。
湖北诗人张执浩2013年的时候就在微博上鼓励林白多写诗,但林白说,“不可能多写的,没有状态,根本不可能多写。”所指的状态更多受制于身体状态,对于这位体重勉强超过40公斤的虚弱女作家而言,写诗是格外消耗力气的。她容易疲惫,写完常常需要在床上躺一会儿。作家陆源认为,真正的诗人必然是怪兽,诗歌创作必然是一种特殊的、剧烈的新陈代谢。
一口气连着写一百多首,这在以往,林白想都不敢想,这回除了情绪助推,她也因打坐获得了足够的体能动力。上一次体力爆发出现在2017年。4月,林白回广西老家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大家四十多年不见,公认她是全班身体最差的一个,“气血很差,消化不行”,一度疲惫不堪到要停下手头的长篇。
等到5月,共享单车出现,她在手机里下载了OFO和摩拜单车,每天骑车,一骑心情就特别好,心情好了以后身体就好很多,写作速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人家老问你的驱动力从哪里来。我发现我的驱动力真的就是来自共享单车,因为写作需要有力,你没有文学荷尔蒙怎么写这个东西?”她乐此不疲、每天三趟地往外骑,两个平台都累积了上千积分。
骑自行车是她们那一代人的青春纪念,插队后,林白常常晚上在没有亮灯的田埂小路上骑行,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拿着手电筒。这段经历也被她写到了近期的诗里。

十九岁的乡间小道
我单手右手扶把,左手电筒
坚硬与烂湴交替
稍一迟疑就会跌倒
在全然的黑暗中
四月的蔷薇一路炸裂
浩荡向前
回翻笔记本,她发现前面四十几首诗都跟疫情密切相关,到了后面,书写的题材五花八门,外婆、略萨、解封、领骨灰盒,回忆2014年和小引去额济纳、模仿鲁迅写打油诗,甚至书桌上摆放多日后腐烂的苹果,都可以成为触动她的开关。
稀薄的芬芳安抚了我
某种缩塌我也完全明白
在时远时近的距离中
你斑斓的拳头张开
我就会看见诗——
那棕色的核。
“我的语言肯定会更明亮更流畅”
张执浩记得林白说过要在晚年重新开始写诗的宣言,称赞她的诗里有一种强大的自省能力,同时也有对个人生活细微审慎的刻画,看似絮语,实则惊心动魄。
写完《苹果》后,林白非常畅快,有一种自知是好诗的、以往写小说时从未感受过的狂喜与晕眩,觉得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生写诗的巅峰状态。早年写得慢,是因为“很在意语言”,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反复斟酌,特别较劲,觉得那样才是文学。
就连口语化的《妇女闲聊录》,她也是反复打磨。书中内容由湖北保姆木珍的218段谈话整理而来,用林白的话说,“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虽然这些原生素材已足够精彩,但林白认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做,“整理、加工出来的文字,跟以前的叙述是不一样的。一句话、一个词肯定是用她的,然后这个句式怎样,前后节奏怎样,什么时候短句,什么时候长句,怎么才有现场感?因为我写了几十年的文字,也写过诗,对语言的节奏和语感肯定有感觉。然后我把它变成文字,变成现在这个东西,换一个人把她的对话记下来,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2019年夏天女儿在家为林白拍的照片
有人评论,就口语写作而言,在目前的汉语作品里,《妇女闲聊录》前面只有《马桥词典》,后面只有《繁花》。作家孔亚雷也提过,“文字提炼后的《繁花》和《妇女闲聊录》都很美”,他甚至清楚记得《妇女闲聊录》的开头,“木珍在火车上笔直坐了八九个小时,‘笔直用得太棒了!”
至于质量,林白自认以前写的“都是很差的”,哪怕是詩集,也没送人,“实在拿不出手。”“为什么现在写得顺了?因为我好像慢慢找到了一种新的叙述方法,每一段要讲究节奏和色彩,叙述语言有很多种,色彩是不一样的,我想现在我的语言肯定会有改变,会更明亮、更流畅。”
她希望自己的诗来路不明,不喜欢自己的诗写得太像诗人的诗。到了后期,一些懂行、苛刻、视野开阔且特别信任的朋友的肯定更加支撑了她的判断,“我觉得近期的诗已经很不错了,能拿得出手嘚瑟的相当不少,所以兴奋得很,所以才写了104首。要是觉得自己的诗很烂,肯定不会写104首。”
这是我们5月上旬交谈时的最新数字,她每天写,写得不亦乐乎,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潜意识里,多少有对小说的逃避”。那之后不久,她在接受一位意大利学者的访谈时更加详细地阐释:“写诗和写小说非常不一样。写诗比写小说更具神秘性,需要更强烈的情感激荡来启动,需要速度,需要神灵的眷顾。另外我觉得写诗能提高人的精神层次,可以极大地激发人的精神能量。”
即便如此,也许是已经过足了瘾,又或是手边已写好的、待修改的40万字长篇小说的无声催促,现在她开始有意识地慢慢减少诗歌写作,“估计下周我就开始进入小说了,希望诗歌的节奏能够跟长篇小说共振起来。”
“女性要生产,要哺乳,还要兼顾工作和家庭,真的太难了”
2020年1月,《说吧,房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纪念修订版,过了23年,腰封上的“先锋女作家”依旧不变。林白率性坦荡,“语言上看不顺眼的越来越多,凡是不顺眼的通通删了。”修订版的线上分享会上,她在微信群里发来一条条文字,“不敢说语音,觉得好像是跟幽灵说话。”她坦言,“本来以为线上线下都一样,你让我回答问题我就大脑空白,不过现在发现还是线上更爽。8点开始,我7点半还可以在床上躺会儿,差5分钟起来,不用梳妆,披头散发就可以聊天,如果是线下,还得先打车到现场,路上就够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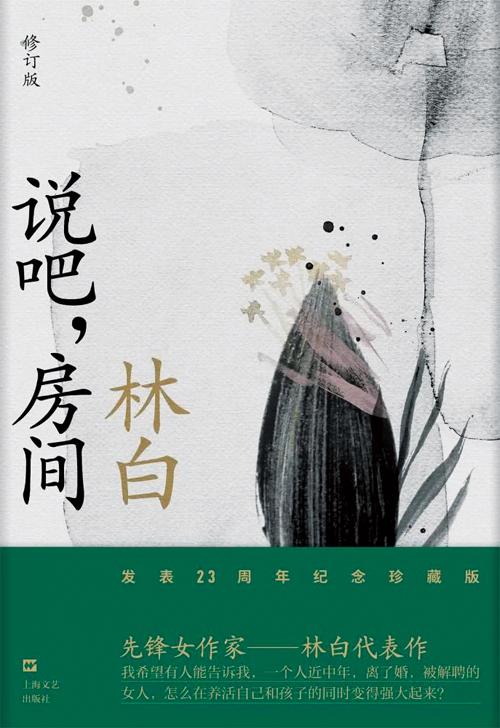
写这本描述职业女性生存、“90年代我的作品里女性意识最强”的长篇小说时,林白下岗,接连碰壁,“求职的过程是一个人变成老鼠的过程”。23年以来,她感觉女性的生存境况并没有更好,似乎还更难了。“以前是国家分配,现在找工作多难啊,很多工作不愿意招女性。现在还开放二胎,女性要怀孕,要生产,要哺乳,还要兼顾工作和家庭,真的太难了。”
林白在后记中写道:“女性之生活终究无大变,哺乳的奶汁仍然是血变成的,挤公交车的疲惫仍然会使乳汁分泌下降,奶水仍会变成汗水悬挂在额头,人工流产仍需面对锐利凛冽的器具,面对那些弯刃、钢尖、锯齿,那些刀刃之上的刀刃,寒光之中的寒光,这些仿佛变成刑具的手术器械,它使女性如惊弓之鸟。”
她在2018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首次谈到自己80年代被一位“殿堂级”杂志的诗歌编辑叫到家里强吻的事情,尖叫着逃跑后,编辑在她背后警告:以后不要在他所在的杂志发表作品了。接下来的一年内,在杂志社开会时她的名字也被避免提及。
据报道所说,林白和那个编辑再无联系,后来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诗集,书上标明某某糖厂赞助。“他要出一本诗多么困难,糖厂给钱,他才能把这本书买来寄给人,要不然出版社就不会印你的书。我的书谁都能出,对吧?就这个结构来说,我在他的上面,以这种方式:权力的变化,在文学上我变得更有权。”
多年不懈的书写,林白希望让读者在社会认知上承认女性的弱势地位,并为此努力改变,“这作用肯定也是微小的,但我的文学能做的也只能如此。”80后编剧、作家柏邦妮曾说:“如果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那应该是林白的《玻璃虫》。那里面的林蛛蛛,敢冲敢闯,天真而又无赖,呼一下把自己擦亮,又呼一下把自己点燃,词和短句噌噌往外冒,在头顶像焰火一样开放,在黑暗中蔚为壮观。她简直是我的榜样。”
在这个层面上,不论是诗还是小说,都无异于一场文学疗愈。如同林白在《说吧,房间》修订版后记中所写:“无论女性生活的变与不变,那些生命中的焦虑、惶恐、疼痛、碎裂等等,都还是需要文学的,而文学也是需要它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