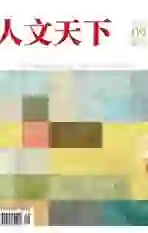共听潮声兼话声
2020-06-12孙宜山
1935年7月14日,青岛《民报》文艺副刊《避暑录话》创刊。《避暑录话》问世于“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偶而有若干相识的人,聚集在青岛”,这些“相识的人”有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十二人。十二人相聚青岛的原因各异,对文艺的态度却在短时期内趋于一致——避暑。至1935年9月15日停刊,《避暑录话》连续出版10期,刊发76篇文章。但在意料之外似乎又在情理之中的是,避暑的闲适滋生了遒劲的文骨。短短两个半月,《避暑录话》就从青岛走向全国,给当时的文坛吹去了“一阵清爽的海风”。这“清爽”的产生,原因众多,后人曾经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做过解读。于今对此再次审视,所获又有不同。《避暑录话》带给全国文坛“清爽”的原因,或许可以从老舍在终刊时发表的《诗三律》中“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旧学和新声
《诗三律》为旧体诗。创作旧体诗,对于因话剧和新文学而蜚声文坛的老舍而言实属少见,所以更应重视。老舍在诗中写道:
远近渔帆无限情,
与君携手踏沙行。
于今君去余秋暑,
昨夜香残梦故城。
漠漠云波移往事,
斑斑蛤壳照新晴。
何年再举兰陵酒,
共听潮声兼话声。
晚风吹雾湿胶州,
群岛微茫孤客愁。
一夏繁华成海市,
几重消息隔渔舟。
不关宠辱诗心苦,
每忆清高文骨遒。
灯影摇摇潮上急,
归来无计遣三秋。
故人南北东西去,
独领江山一片哀。
从此桃源萦客梦,
共谁桑海赏天才?
二更明月潮先后,
万事浮云雁往回。
莫把卖文钱浪掷,
青州瓜熟待君来。
上述三首律诗的内容和情感暂且不论,时代环境需要先行描述。1935年距离1919年时隔16个春秋。1919年的五四运动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而救亡图存作为历史的选择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显著增强了文学的致用功能。1935年6月,《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相继签订,国民政府又火上浇油,发布《邦交敦睦令》。日本对中国的飞扬跋扈与国民政府“严禁排日”的委曲求全让大部分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倍感屈辱。青岛虽地处一隅,但民众对日本的侵略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1914年至1922年曾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经历使青岛民众积蓄了仇日抗日的情绪和力量。明道救世,抵御外侮,是《避暑录话》一干编辑言而未明的意图,也是所刊发文章编辑成册后走向全國的一大因由。
以“避暑录话”命名《民报》文艺副刊就颇有“弦外之音”。事实上,“避暑录话”并非新创,而是持之有故,源自宋人叶梦得撰写的一部史料笔记《避暑录话》。老舍曾对以“避暑录话”作为刊名做过个人的解释:“宋朝,有个叶梦得,博古通今,藏书三万余卷,论著很多,颇见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其实,采用宋人笔记《避暑录话》命名现代报纸的文艺副刊,看似随意为之,实则意味深长,可称之为推陈出新。
宋人叶梦得在有宋一代,绝非寻常之辈,《宋史》专列其个人传记。他曾官至尚书左丞,为宋高宗谋划抵抗金兵入侵以及守备建康城。1129年,宋高宗曾亲临建康府,表示要在此领导抗金,恢复北宋的河山。《避暑录话》撰成于1135年夏。该年年初,叶梦得上《应诏咨询状》,提出抗金策略:对内安抚、对外强硬,其主战立场十分明确。但叶梦得的意见并未被采纳,同时因党争而辞官归隐。外患频仍,忧患意识极强的士大夫如何有闲心“避暑”?虽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自序中谈及,“泛话古今杂事”,实际上泛而不空,杂事不杂。全书240条纪事,除去四分之一篇幅的个人经历和家世外,其余皆为史事、政事。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真是进亦忧退亦忧,忧在大好河山逐渐沦丧,收复失地遥不可及。
800年后的1935年,与800年前的1135年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日本相类于金国,蒋氏相类于赵氏,不同的是侵略对象变成了南京。虽然时序百番轮转,但面对的问题却一致,面对外敌入侵,到底该不该抵抗?这个问题,800年前宋朝的百姓问过,叶梦得的回答是抵抗,所以他被赋闲避暑了。800年后的中国民众再问,国民政府的回答是邦交敦睦,所以洪深、老舍等遗传了叶梦得这类“士子”基因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只能以“避暑”的形式纾解压抑的心声。
由此再回到老舍的《诗三律》,诗的形式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旧体诗这一形式所承载的“新声”。诗中,“昨夜香残梦故城”“群岛微茫孤客愁”“独领江山一片哀”等句,清晰地表达出老舍寄居青岛,心怀故城的愁、哀之情,愁哀转为忧愤,忧愤诉诸文字,成歌成诗成文章。
老舍的“新声”也是“心声”。从老舍的“心声”到《避暑录话》其他编辑和作者的“心声”,再到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者们的“心声”,顾炎武的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足以当之。《避暑录话》穿越800年的时空至此焕然一新。
二、文学和民声
1930年代的时代主题是革命和救亡。革命对内,救亡对外。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革命而艺术,成为当时摆在作家面前的一道选择题。文章合为时而著。左翼文学作家选择了后者,重于以文学促变革,追求“文学的大众化”。民族的屈辱落在民众头上,就是人间疾苦。风声雨声读书声,更遑论民间疾苦声,毕竟“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避暑录话》的十二位创刊发起人中,左翼作家身份明确的有王余杞、刘西蒙、王亚平、杜宇、孟超和洪深六位,他们听到了当时民间的哀怨和疾苦之声,呼吁作家切勿“妄自菲薄”,要立于时代的前沿,发出民众的呼声,也就是“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在发刊词中,洪深有感而发:“他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然而他们都对人说着:‘在避暑胜地的青岛,我们必须避暑!避暑!避暑!”既然有正事要做,又不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那为何又要“避暑”?这样的避暑意图何在?洪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
原来“避暑”并非为了躲避天气的炎热,而是为了躲避国民政府的“炎威”。“炎威”相较于“严威”,那种烈日当空的灼肤灼心更让人恐怖窒息。自1930年3月“左联”对外正式宣布成立以后,国民政府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以各种手段予以“文化围剿”,如枪杀、抓捕左翼文人,多次查封、捣毁“左联”组织,实行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等。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事件发生,左翼文艺运动遭到重创。进入1935年后,状况更加恶化,田汉、阳翰笙等“左联”的重要人物先后被捕入狱,“白色阴霾”迅速向全国弥漫。在此背景下,“左联”发起人之一的孟超、左翼美术家联盟成员刘西蒙、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洪深从上海来到青岛,《新诗歌》杂志负责人王亚平从北平到青岛“避难”,左联刊物《当代文学》编辑王余杞从天津到青岛“躲避风头”,时任青岛《民报》总编辑的杜宇作为“左联”成员则以东道主的身份力促“弄个小刊物出来”。因此,《避暑录话》甫一诞生,左翼立场即露锋芒,“文艺是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的旗帜就树了起来。既然文艺可以增进人类幸福,那么无益于人类幸福的事物都是他们抨击的对象,尤其是对于独断专制、辱国欺民的行径,“在青岛这样一个外国军舰横陈的地方,这样‘书生救国惭无力但又心怀义愤的一群人,你写篇散文,他来篇杂文,凑成一个小品文刊物”,以此作为标枪、长矛,去刺穿遮盖着丑陋行径的“皮袍”。
洪深首先投出了标枪。他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动炎威,署名发表了《友人狱中诗》《友人狱中词》,并且加了录注。这位“友人”就是田汉,二人作为我国现代戏剧的开拓人,交情深厚。1935年,上海戏剧界上演了田汉创作的话剧《回春之曲》,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鼓舞了民众的战斗热情,因而惹怒蒋氏政府,田汉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田汉依然保持乐观的革命精神,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安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娇儿且喜通书字,巨盗何妨共枕头。极目风云天际恶,手扶铁栏不胜愁。”后来,这些狱中创作的诗词辗转到了洪深手中。洪深在为田汉的高风亮节所折服的同时也为挚友鸣不平,便在田汉遭到关押的时候,将这些诗词加上录注,在《避暑录话》中刊登出来。在蒋氏威权统治下的青岛,洪深敢于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被当局关押的共产党人的诗作,既表明了洪深的胆魄和立场,也说明了《避暑录话》的左翼倾向。
由此观之,在老舍《诗三律》中,“不关宠辱诗心苦”“每忆清高文骨遒”两句就更显含义隽永,耐人寻味。他本人撰写的《暑避》《等暑》两文,即以谈暑为名揭露社会现实的无奈。应该说这一时期的老舍,创作心态正悄然发生变化,开始向“笔尖上滴出血和泪”迈进。这和大气候有关,也和小环境有关。与洪深、孟超等左翼文人联合编辑《避暑录话》应该对老舍影响颇深。避暑的闲适随意背后实际上担负了对社会苦难的抒写,“诗心苦”带来“文骨遒”。《避暑录话》将民众的呕血苦吟之声转换成斑斑墨迹,以文学的清高,见证并记录了时代的荣辱和民众的呐喊。
三、大学和书声
在《避暑录话》的十二位创刊发起人中,老舍、洪深、赵少侯执教于当时的国立山东大学,吴伯箫也曾在国立山东大学办公室短暂工作,臧克家为国立山东大学毕业生,而王统照于1946年8月出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如果再加上私立青岛大学毕业生刘西蒙(国立山东大学校址为原私立青岛大学校址,二者有传承关系),国立山东大学师生占了《避暑录话》创刊发起人的半壁江山以上。因此,可以这样说,彼时校址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以自身的文化滋养了《避暑录话》,提升了《避暑录话》的文化格调和品位,并带动了青岛整个城市的文化繁兴。
上述创刊发起人中,老舍在《避暑录话》上发表的文章多达9篇,洪深8篇,其他人员数量不等,但均未超过洪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舍对《避暑录话》的重视,他是将《避暑录话》作为个人文学理念的试验田对待的。作为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知名的作家教授,老舍身上充分体现出“传道授业解惑”的学者情操和价值理念。他把在大学“授业”与在社会“传道”结合起来,既育人又正风,试图以自身的学养和理想去沟通大学与社会,达成雅与俗、体与用的和谐,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老舍在《避暑錄话》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丁》,生动描绘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大都市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丁”是公务员,他认为青岛的美“是一片空虚”,呈现出一幅糜烂的社会景象。小说借用主人公“丁”的所见、所闻、所感,一方面表现了他颓废、矛盾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以及导致这些现象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日益深入。在小说中,通过经济文化的表面繁荣与实质上社会更加堕落与危机四伏的反复对比,老舍表达了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憎恨和对贫穷者的同情。作品中还可以读出忧国忧民的老舍对祖国和国民并没有绝望,而是充满着希望。他深刻认识到,批判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还得依靠中国人自醒自觉去解决。因此在揭露讽刺背后,寄托的是老舍对民族和国人的殷切希望。因为老舍希望像“丁”这样的国民能够抑制住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以养成健全的人格,并能够最终引领中国走向光明与希望的未来。
这不是偶然的触发,而是持久的驱动。当老舍从齐鲁大学来到国立山东大学时,其学术思想和文学理念就已悄然发生转变。在国立山东大学,老舍主要讲授《小说作法》《高级作文》《文艺批评》《欧洲文学概论》《文艺思潮》等课程,《小说作法》《高级作文》属于“术”,乃制器;《文艺批评》《欧洲文学概论》《文艺思潮》等属于“学”,乃传道;学与术、道与器兼顾,说明老舍既重视思想启迪,又重视技巧应用。启迪思想不仅局限于课堂,公开的学术报告或者演讲更像是面向社会的“布道”。而这个“道”就是救国救民的情怀和民族自强的信心。1934年10月,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面向师生和青岛民众做了题为《中国民族的力量》的演讲,“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的确是伟大。我们可上可下,只要努力使劲,我们只会上,不会退下”,给大学师生和正处于国难中的青岛民众以巨大鼓舞。
一面是批判,一面是激励;一边破,一边立。老舍打破了大学的藩篱,对接社会现实,输出思想和精神,给予民众以教育和引导。大学的琅琅书声宁静了世俗的喧嚣,振奋萎靡的民风,鼓舞消沉的士气。以造就“新民”,促使整个民族踌躇满志而又精神抖擞地面对世界与未来。《诗三律》中一句“共谁桑海赏天才”尽述老舍的希冀与理想。
旧学、文学、大学,学为根本;新声、民声、书声,皆为潮声。先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皆以“民”为根本。一册《避暑录话》,无论家长里短还是阳春白雪,讲的都是民话,而不是官话,是民族和时代的宏大语境中,虽然琐屑却又事关宏旨的“闾阎短长”,值得当时听,也值得现在听,更希望未来依然有人听。
共听潮声兼话声,真是声声入耳。
[责任编辑:祝莉莉]
[作者简介] 孙宜山,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