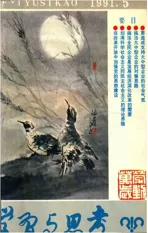中国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凡例体系及其形成与特点*
2020-06-11陈长安
陈 长 安
提 要:中国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凡例体系(简称“中凡”)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总《编辑说明》和每卷《凡例》,分散内容则包括第一版、第二版散见于每卷注释等的相关编辑内容。“中凡”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从第一版翻译俄文《第二版说明》、前15卷《说明》及其准凡例到不译到自撰第40-50卷《说明》及其准凡例,再到第二版专门撰写总《编辑说明》、每卷《凡例》的过程,是模仿、反思、突破、超越苏联模式的反映。“中凡”的特点包括统分结合、各部分通用一个《凡例》、内容酌情调整、篇幅较短、个性化不足、具中国特色等。“中凡”应通过经典著作编译专业的联合设立、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相关文献的整理和每卷《凡例》篇幅、个性化的增强等而得到坚持和完善。
“凡例”源于杜预《春秋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①《春秋左传注疏》,[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四·左传》(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00、3761页。此即成语“发凡起例”的出处。及《隐公七年》中的杜预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②《春秋左传注疏》,[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四·左传》(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00、3761页。此即成语“发凡起例”的出处。等。后世凡例(图书凡例)“多指图书编撰者编纂图书之时所遵循的各种编辑原则、规范或方法,包括作者的意图、选录标准、编排体例、资料来源、遣词用字、符号使用等等。唐代以后,图书编撰者常将本书凡例列专文进行说明,凡例由此成为专篇的说明文字。”“图书凡例至于宋代已发展成熟,到明清时期更加完备,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图书编撰的方方面面”。③马刘凤著、曹之指导:《中国古书凡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第16页。到明清,图书凡例“大多作为专篇刊于卷首”①曹之:《古书凡例考略》,《编辑之友》,1997年第4期。。归纳“历代图书正文之前的成文凡例”,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图书撰写经过、编撰内容与编撰形式等三个方面的说明”。②马刘凤著、曹之指导:《中国古书凡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第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简称“中一”)只有处于萌芽和分散状态的凡例,而没有专篇凡例,从中国古典文献学传统来看,是非常罕见且发人深思的,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俄文第二版(简称“俄二”)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当然,“中一”对“俄二”凡例相关内容的处理,亦可见其逐步突破“俄二”和苏联模式的努力,此点下文中会详细论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汉字文化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第一版(简称“日一”)第1卷虽然没有专篇凡例,但第二年就在第2卷增设专篇《凡例》③『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全集』(第二卷),東京:改造社,1929年,461-465ページ。其“凡例解説”为专门部分,下设单独的“凡例”和“解説”,位置不在卷首,而在卷末。“日二”则单独设专门的“凡例”,位置也改为卷首。,可见中国古典文献学传统对日本及“日一”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第二版(简称“日二”),尽管也以“俄二”为底本之一,但仍继续坚持《凡例》。在中国,直到苏东剧变后,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之际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重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简称“中二”)时,才设立专篇《凡例》,真正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译事业中突破“俄二”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凡例体系(简称“中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其伟大成就,也会体现在“中二”的编译成果之中。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凡例传统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研究“中凡”应注意的背景。今天,加强“中凡”研究并有所坚持、加以完善,对反思、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不无裨益。
一、基本内容
“中二”作为中国人第一次独立编译的全集,第一次在全集编译史上采用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唐代以来专文凡例传统及明清大多作为专篇刊于卷首的传统,形成“中凡”。遗憾的是,这一“中凡”并未得到国内读者、学界的应有重视,相关的专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凡”萌芽于“中一”相关内容,直到“中二”才包括单独成篇的总《编辑说明》和每卷《凡例》(具体形成过程及相关情况将专门分析)。就这一“中凡”专门、系统体现于的“中二”而言,其基本内容首先包括独立成篇、位于第1卷的全版《编辑说明》(共五段)以及独立成篇的每卷《凡例》(每一部分大致相同、总共七条)。独立成篇的全版《编辑说明》和每卷《凡例》是“中凡”的基本内容,也是主体内容,是全集编译史上的崭新一页。除了这些基本内容外,还有一些凡例内容散见于每卷《前言》的首尾段(有时一段,有时多段)、编辑问题相关注释(题注、题下注、编者注、译者注等)、《凡例》前编译页、卷末④具体位置“中二”在版权页前一页。“文一”(陈长安 张子骞 连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文第二版、日文〈《资本论》手稿集〉版〈大纲〉编辑比较研究初探——以〈编辑说明〉和〈凡例〉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年第5期)、“文二”(陈长安:《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凡例体系的特点及形成过程》,《理论视野》,2018年第7期)误为封底,特此更正并致歉。分工署名页(可简称“分工页”)等,以及“中一”的相关内容,可称为分散内容。这些基本内容与分散内容,共同构成“中凡”⑤与中文全集相关的选集、文集、专题文集或单行本等,本文暂不作探讨。。
以下,根据“中二”对“中凡”分而述之。①“文一”对“中国特色编辑凡例体系”及“中二”《编辑说明》和《大纲》《凡例》逐段、逐条进行了初步分析。“文二”补充了《前言》相关、译者注、注释、其他等凡例相关内容,但未展开。本文对上述内容有所深化,包括明确提出“中凡”的概念、为《编辑说明》每段及《凡例》每条明确命名、分析内容有所增补等。
(一)基本内容之“中二”全版《编辑说明》
“中一”在第1卷(1956年12月)卷首全文翻译了“俄二”第1卷的《第二版说明》(简称“二说”),这表明“中一”是从一开始就计划以“俄二”为底本编译。“中二”则在第1卷(1995年6月)自撰了全版《编辑说明》。虽然类似“二说”且篇幅、内容较前者少得多,但集中、精炼地交代相关编辑问题,篇幅约半页,以下逐段分析说明之。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编辑说明。中文第二版对全卷《编辑说明》和每卷《凡例》均未注明页码,也未收入每卷《目录》中。
第一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编辑说明。可称为编译段。编译工作的决定者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承担者为中央编译局,这表明第二版编译工作是执政党中央之行为。这一工作从国际背景来看处于苏东剧变后不久,具有明显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建设意义。该段内容亦单独成页位于每一卷《凡例》前两页,成为编译页。
第二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述的汇集,第一版于1956年至1985年出版,共50卷。由于条件限制,第一版在翻译和编辑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为了适应我国读者当前及长远需要,经中央批准,我们着手编译一套内容全、编译质量高、可供长期使用的新版本。”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编辑说明。可称为新版段。主要谈“中一”概况及出版“中二”的必要性。既介绍了“中一”的收文情况、出版卷数及持续时间等概况,也交代“中一”限于条件存在的缺点,以及“中二”的版本目标、定位。
第三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以第一版为基础,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文版重新进行编辑和译校。全集收入了第一版未收入的一些著作,删除了第一版误收的、不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笔的材料。全部著作除个别语种外,均按原文译校。”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编辑说明。可称为底本段。其关于“中二”的底本表述表明“中二”的间接底本似是“俄二”,但大多数文献是根据MEGA2“编辑和校译”。“中二”的封面设计、书脊内容、内置书签等装帧明显模仿MEGA2,则直观表明MEGA2的底本地位。此外,“中二”对文献有所删补,“除个别语种外,均按原文译校”。新版段中提及的“条件限制”,包括“中二”的版本定位(学习版而非研究版)、编译工作的实际情况(“中一”的翻译质量上乘、完全根据MEGA2从头再来准备不足)等。考虑到这些“条件限制”,读者不应苛求“中二”没有直接、严格根据MEGA2编译。从本文探讨的“中凡”等可知,“中二”在编辑上有明显超越“俄二”的创新。2010年以来,原中央编译局与国际马恩基金会合作的工作方式更进一步表明“MEGA2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主要版本依据。”⑥柴方国:《MEGA的编辑出版及在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理论视野》,2018年第7期。这一国际合作的学术效应正在溢出。2018年出版的MEGA2I/16《编辑说明》⑦MEGA2 I/16, S.615.明确致谢编译局及其人员的编辑工作,是MEGA2正文首次致谢中国研究机构及其人员。
第四段,“全集分为四个部分:第1—29卷为著作卷,第30—45卷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46—59卷为书信卷,第60卷以后为笔记卷。同第一版相比,文献篇数和收文字数有较大的增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编辑说明。可称为结构段。该段根据MEGA2将全集分为四部分,并规划好每部分的卷次。与此新结构相适应,文献篇数、字数比“中一”有较大增加。其中的笔记卷,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译史上,MEGA2第一次将之作为一个专门的部分。就版本结构而言,“中二”的底本是MEGA2而非“俄二”。
第五段,“全集各卷设有《前言》,简介所收文献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卷末附有正文的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等参考性资料。”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编辑说明。可称为体例段。该段介绍了“中二”的编辑体例及具体内容,较多涉及编辑凡例。
总之,“中二”《编辑说明》通过编译段、新版段、底本段、结构段、体例段等专门、专业内容,介绍了编译工作的缘起、目标、底本、全集的构成和体例,是“中凡”的第一项重要内容。
(二)基本内容之“中二”各卷《凡例》
“中二”各卷《凡例》最早出现在第1卷,共六条。“中二”各卷《凡例》总共七条最早成形、定格于第32卷(1998年1月)。下面以第32卷《凡例》为基准讨论。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凡例》。可称为时序条。此条交代每卷文献的编排顺序依据是写作或发表时间,并说明个别变通及其理由。
“2.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凡例》。可称为星花标题条,简称“星标条”。此条交代目录和正文中的一种特殊符号的标题的含义和施加者。
“3.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凡例》。可称为尖括号圈点条,简称“尖圈条”。此条交代引文中的尖括号和圈点两种符号的含义和施加者。
“4.在正文和目录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凡例》。可称为方括号条,简称“方括条”。此条交代正文和目录中方括号的含义和施加者。
“5.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凡例》。可称为原注条。此条交代脚注中编者注之外、马克思或恩格斯所加的原注。
“6.《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凡例》。可称为索引条。⑨关于全集索引汇编,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篇名版本目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篇名版本目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篇名字顺索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不详年版;福建省图书馆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篇名字顺索引》,福州:福建省图书馆,1974年版;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专题分类索引》,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1978年版;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名索引》(第一至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第一至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说明、索引(第40至5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近年专门的论文可见闫月梅:《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名目索引的历史及现状》,《中国索引》,2011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书后索引简介——兼谈年会主题“内容索引与出版事业”》,《中国索引》,2012年第4期;《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索引工作也要与时俱进——马恩经典著作各种索引的保存、更新与完善》,《中国索引》,2014年第1期,等等。此条交代各种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排序,体现“中二”语言特征。
“7.引文的出处中标有[P.]、[B.]、[M.]、[L.]、[Zh.]者,分别为马克思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伦敦笔记》(1850—1853年)和《引文笔记》(1859年)的外文缩写符号,符号后面的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分别指笔记本的编号和页码。”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凡例。可称为笔记本缩写、编号、页码条,简称“笔缩条”。此条交代数部《资本论》笔记的外文缩写及其笔记本编号(罗马数字)、页码(阿拉伯数字)之表现。
《凡例》总七条在各部分各卷中略有变化,大致情况如下所述。
第1部分第11卷(1995年6月)的《凡例》与第1卷完全相同。第10卷(1998年3月)、12卷(1998年3月)进而增加了“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并固定在其后的第13卷(1998年10月)、3卷(2002年10月)、25卷(2001年4月)、21卷(2003年5月)、2卷(2005年10月)、19卷(2006年6月)、16卷(2007年8月)、14卷(2013年12月)、28卷(2018年12月)《凡例》之中。
第2部分最早出版的第30卷(1995年6月)《凡例》前六条与第一部分第1、11卷完全相同,另增“笔缩条”,但“ 《引文笔记》(1859年)”的缩写“[Zh.]”的内容到第32卷才加上并定格在第33卷(2004年6月)、第34卷(2008年7月)、第35卷(2013年4月)、第36卷(2015年12月)、第42卷(2016年12月)、第43卷(2016年12月)之中。而第31卷(1998年12月)、第44卷(2001年6月)、第45卷(2003年4月)、第46卷(2003年5月)、37卷(2019年12月)、38卷(2019年12月)《凡例》第7条则未见“《引文笔记》(1859年)”的缩写“[Zh.]”。②“文一”“文二”关于第32卷七条凡例的定格描述有误,忽略了32卷第7条首先增加了“ 《引文笔记》(1859年) ”,特此更正并致歉。
第3部分第47卷(2004年7月)共5条,其中第1条为“1.正文和附录中的书信分别按写作或发表顺序编排,所有书信均加有序号。”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凡例。第2、3、4、5条则与第32卷完全相同。这五条也定格在此后的第48卷(2007年10月)、第49卷(2016年3月)《凡例》之中。
第4部分尚未出版,其《凡例》非常值得期待。
总之,各卷《凡例》以时序条、“星标条”、“尖圈条”、“方括条”、原注条、索引条、“笔缩条”从七个主要方面,系统交代全文、正文、目录、引文、脚注、索引中的相关编辑问题并单独成一个部分,是“中二”编译的一大创新,是“中凡”基本内容的主体之一。
(三)分散内容
1.《前言》相关。“中二”每卷《前言》一般会在首段(一段或多段)介绍收文范围、尾段(一段或多段)介绍底本、编辑处理等涉及编辑凡例的内容。
如“中二”第1卷《前言》首段如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部分为著作卷(《资本论》及其手稿除外),包括第1卷到第29卷。第1卷收入马克思从1833年到1843年3月所写的著作。全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博士论文和政论文章,第二部分为中学毕业作文和早年的文学习作。它们反映了马克思从中学时期直至《莱茵报》停刊为止的思想发展,他从唯心主义逐渐向唯物主义转变以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形成和发展的过程。”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这也是各部分第1卷卷首兼介绍本部分文献和本卷文献的情况。第30卷首段介绍第2部分的内容(《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卷次(第30—345卷),第二段介绍本卷内容(和31卷一起构成一个单元)。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第47卷首段介绍第3部分的内容(书信)和卷次(第47—360卷),第2段介绍书信的意义,第3段介绍该卷的内容。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中二”第32卷《前言》首段如下:“本卷收入马克思的1861—1863年手稿第I-V笔记本和第XVI笔记本以及第XVII笔记本前七页的内容。这部手稿共23个笔记本,马克思亲自编了页码,共1272页。全部手稿收入本版第32—327卷。”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33—37卷首段也如此。这是以一组文献分多卷时共用一个《前言》首段的情况。
第49卷《前言》首段如下:“本卷是书信部分的第三卷,收入1852年1月至1855年12月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和他们给其他人的书信,共计291封;附录部分收入燕妮·马克思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委托给其他人的书信,共计19封,还收入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5封书信的片段,其中转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5封现已遗失的书信的部分内容。”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介绍了具体文献及数量。
尾段的内容,现以第1部分第1卷为例说明。该段内容是:“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8篇……原第1版中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经考证不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本卷不再收入。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由此卷可见,《前言》尾段主要是将《编辑说明》底本段具体到每一卷。
此外,《前言》尾段还会根据每卷情况酌情介绍相关编辑调整情况。如第30卷《前言》尾段谈到在“必要的地方加了少量标题”、把“过长的段落分短了”、对引文“用相应的符号作了注明”等问题。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第42卷(《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前言》尾段第一段谈到本卷与通行版(《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同部分第44卷)译文保持一致及译出不一致、500余条反映第1卷四版“意思明显不同、表述差异较大或名词术语作了修改的地方”的编者脚注以及对后来的版本“单纯的文字和数字修改以及印刷错误”不一一说明。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2.注释相关。“中二”注释部分中,一般在某一文本(主要是著作)的第一个注释会介绍该文本的相关情况,也包括一些编辑问题包括文本内容、简介、文本物理状况、引文、标题、发表流传、手稿括号等。这个注释可称为题注,会参考MEGA2资料卷(Apparat)中的《形成和传播》(Entstehung und Ueberlieferung)、《见证人描述》(Zeugenbeschreibung)的内容,但不是作为单独的部分。注释中的脚注经常会参考MEGA2资料卷中的异文表(Variantenverzeichnis)、校正表(Korreckturverzeichnis)、文献索引(Literatureregister)和人名索引(Namenregister)等⑧曹浩瀚:《MEGA2注释的特点及问题》,《理论视野》,2018年第7期。。此外,编者注、译者注等形式的注释,也采用脚注的方式,没有专门设在注释主体卷末注中。个别注释会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修改、笔误等,但是数量很少,也没有专门标出,在脚注和卷末注中均有体现。有些文本的标题下,也会有类似注释的内容,说明该文本的写作时间、首次发表、原文、翻译底本等,可以称为题下注。题注、编者注、译者注、题下注、卷末注等延续自“中一”。类似《前言》尾段的底本内容,题注、题下注一定程度是将《编辑说明》底本段具体到每个文本及其标题。
3.其他。除前述编译页,还有“分工页”等。如“中二”第1卷“分工页”列出了“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参加编辑资料工作”及“译文”“审定”者名单。“分工页”吸收了“中一”相关内容。
综上,每卷《前言》首段对文本内容、尾段对底本及相关编辑问题、注释中对文本内容及流传、编辑等、编译页将编译段成页、“分工页”对编译分工的交代,以及“中一”相关内容,分散体现了相关编辑问题,也是“中凡”的分散内容,与“中二”全版《编辑说明》及每卷《凡例》共同构成“中凡”。
二、历史形成
“中一”及每卷并无“中凡”的基本内容,仅有分散内容。这些分散内容本身有所变化,大多为“中二”“中凡”分散内容所继承,其集中涉及编译的内容则独立成专门的全版《编辑说明》和各部分、每卷《凡例》,形成“中凡”的基本内容。“中凡”之形成,时间上略晚于从模仿苏联模式到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体现。
(一)从“中一”“二说”到“中二”《编辑说明》及《凡例》时序条等
“中一”在第1卷全文翻译了“俄二”“二说”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二版说明第V-X页。。“二说”主要介绍了“俄二”的编译情况,包括“俄二”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出版;“俄一”概况和缺点;包括的基本文献;著作卷次和卷内次序以时序原则排列;结构上附有说明和参考资料(注释、生平事业年表、索引);版本定位为学习版而非研究版;预计30(实际50)卷,等等。介绍完基本编译情况后,用三个星花隔开,用更大篇幅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突出列宁主义和苏联实践的意义。
“二说”在“中二”发展为全版《编辑说明》,其中,编译段改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新版段说明“中一”的缺点和“中二”的版本定位;结构段和底本段则借鉴MEGA,明显超越“俄二”;体例段吸收了“二说”的说明和参考资料等内容。“二说”中的文献排列的时序原则发展为《凡例》时序条;原注条和索引条都有涉及“二说”谈到的注释、索引等问题。
(二)“中一”从翻译《说明》及其准凡例到不译到自撰《说明》及其准凡例
“俄二”每卷均有《说明》,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主体,可称为解说部分,主要介绍的是对每卷文献的解说,与凡例体系有关的主要内容是每卷收集的文献内容等,位于首段。解说部分在“中二”中发展为每卷《前言》,内容也主要是对每卷文献的解说,与凡例体系有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首尾段,但没有像“俄二”那样专门隔开。剩余部分与解说部分一般用三个星花隔开,专门交代跟编译有关的内容,可称为准凡例,从凡例研究的角度而言,这部分是关注重点。事实上,“中二”的凡例主要就是从这个准凡例逐渐发展并独立出来的。以下探讨各卷《说明》的变迁时,着重准凡例,一般不谈及解说部分。
“中一”对“俄二”每卷《说明》,大致经历了从翻译刊印到不再收入到独立撰写三个阶段。内部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出版说明”对前两个阶段有所说明:“第一卷至第十五卷印有各卷《说明》,第十六卷以后《说明》就没有收进去。”其原因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有些卷,在中文和附录的编排、技术规格等方面与俄文版不完全相同”;二是“俄二”第1-39卷“《说明》大部分有严重问题,如宣扬修正主义观点,为老沙皇辩护,直接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影射攻击我党等等。”但本书中,“这些错误观点,未加删节”①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7年版,出版说明。此外,第40-50卷《说明》见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说明、索引(第40至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二”专篇《凡例》的形成过程,以下先概述三个阶段,然后择卷简要考察“中一”“中凡”分散内容概况。考察着重点放在每卷《说明》的准凡例②中山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2015级本科生马文学帮助录入、整理了“中一”50卷《说明》《译后记》等凡例相关内容,特此致谢!,重复的内容一般只在首次出现时介绍,有关卷、册以括号的形式注明出版日期和相关文献的页码。
第一阶段,第1卷(1956年12月)—315卷(1963年12月)翻译刊印每卷《说明》,第2卷(1957年12月)—38卷(1961年10月)、第12卷(1962年8月)—315卷独立撰写《译后记》。此阶段每卷在《目录》前有编译页,内容如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译页。第2-15卷与之相同。编译页说明了编译的决定者、承担者及底本的决定者、承担者、出版者及原文本。“中二”的编译页仅谈及编译的决定者和承担者。自第16卷(1964年2月)起,“中一”各卷不再有编译页。“中一”《说明》第1—39卷署名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40-50卷署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第14卷版权页列出了底本的原文(俄文)信息,还有交待底本的话:“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版权页。,这句话可称为底本段。
此阶段每卷《说明》准凡例一般涉及收文信息、底本问题、流传发表情况、编辑问题处理等,篇幅从一段到五段不等。其中,第1卷翻译“二说”(第V—X页)。第2卷无准凡例,其《译后记》(第732页)主要涉及参考的相关译本情况;底本是“俄二”并参照有关原文、英译文;相关参与、分工等。这是中文全集的第一个《译后记》。第3卷(1960年12月)《译后记》(第741—742页)主体内容类似《说明》解说部分,尾段内容涉及较多编辑符号问题:“本卷中几种括号的用法是:方括号[ ]内的话是俄文版编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所作的增补,六角括号〔 〕内的中文和外文是译者加的,尖括号< >内的话和符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引用别人著作时所加的。”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2页。。此为“中凡”最早介绍这些符号,“中二”《凡例》的“尖圈条”、“方括条”由其发展而来。这篇《译后记》也是中文全集首次出现致谢,原文是:“本卷在译校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一之同志帮助我们从德文校阅了‘费尔巴哈’部分,北京大学郑昕、熊伟、芮沐、宗白华和洪谦等同志从德文校阅了‘圣麦克斯’部分,给译文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2页。这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协同参与编译事业的宝贵传统。第6卷(1961年8月)《说明》(第XIII—3XXXI页)准凡例三段,首次涉及标题星花:“当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时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说明第XXXI页。,第9卷(1961年12月)—313卷(1962年11月)、15卷亦有类似内容。“中二”《凡例》的“星标条”源于此。第12卷(1962年8月)《说明》(第IX—3XXX页)准凡例五段,是“中凡”首次提到异文:“如果马克思同时发表于两种不同报刊上的文章中有重大差别,或者刊印出来的原文与保存下来的手稿有不一致的地方,凡是重要的异文都放在脚注中。”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说明第XXX页。这种异文脚注为“中二”所延续。
第二阶段,第 16卷(1964年2月)—339卷(1974年11月)不译《说明》,第17—22卷以《译后记》为主过渡、探索底本、分工等问题,第23—29卷固定使用底本段交代底本及参考译本。其中,第17卷(1963年11月)将原《说明》内容概要写入《译后记》(第908—909页)主体内容,原《译后记》内容写入最后两段并加三个星花隔开,涉及底本、分工参与等。第19卷(1963年12月)《译后记》(第744—745页)处理类似第17卷。其他卷次,如第16卷、第18卷(1964年10月)、第21卷(1965年9月)、第22卷(1965年5月)的《译后记》内容类似此两卷星花隔开的尾段内容。第18、21、22卷版权页兼有底本原文信息和底本段。第20卷(1971年3月)的底本段“本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二十卷并参考俄文版译出”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版权页。格式在第23卷(1972年9月)—39卷继续使用。其中,第23卷、第24卷(1972年12月)、第25卷(1974年11月)特别提到参考了《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第26卷I(1972年6月)底本段为:“本册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册并参考德文版译出”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版权页。,此后各卷、册底本段与之相同,仅改变相应卷、册数字。此阶段探索的结果主要是以底本段的形式保留《说明》准凡例及《译后记》,显然需要较大改革。
第三阶段,第40卷(1982年2月)—50卷(1985年12月)独立撰写每卷《说明》。准凡例第一句或第一段类似第26—39卷的底本段,延续上阶段探索成果。准凡例其他内容专门说明尖括号< >、方括号[ ]、箭头竖号、着重号、左竖线、*号、花括号{ }、手稿和页码编号、注释、索引等诸多编辑凡例内容。原版权页底本段改为介绍分工及参考译本等。以第三阶段准凡例内容为主要基础,综合《译后记》等涉及的相关问题,“中二”设立专篇《凡例》,置于《目录》之前,但未列入《目录》之中,也没有编页码。
此阶段第40卷(1982年2月)《说明》(第I-V页)开始独立撰写,准凡例两段。第二段如下:“在本卷中,马克思在引文中加的语句或标点,用尖括号< >标出,编者加的标题、插入的文字、页码等,均用方括号[ ]表示。”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说明第V页。,接近“中二”《凡例》的“尖圈条”和“方括条”。原底本段被以下内容代替:“本卷是由福建师范大学翻译、中央编译局定稿的。参加本卷工作的有:福建师大的许崇信、谢翰如、汪庆安、周复、范一、陈正元、赖耀先、黄松柏、戴树英、魏天翔;编译局的王治平、李俊聪、詹汝琮、刘漠云、孙家衡、胡尧之、冯如馥。《博士论文》是根据贺麟译文校订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版权页。这是“中一”独立撰写每卷《说明》阶段,在版权页第一次专列分工署名内容并提到高校及其人员。这种把分工参与(有时兼及参考译本)置于版权页的做法,可称为版权页分工署名段,简称“分工段”。“分工段”在“中二”发展为位于版权页前专门的“分工页”②个别卷次,如第34卷,“分工页”位于版权页之后,疑为误印。。第41—50卷均有“分工段”,其中,第41卷(1982年12月)、42卷(1979年7月)、46卷(上册1979年7月,下册1980年8月)、49卷(1982年12月)兼及参考译本信息。第44卷(1982年5月)《说明》(第I—VI页)另加相对“俄二”的新增文献及“编写了有关的注释和人地名索引”等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说明第VI页。。
第45卷(1985年12月)《说明》(第I-IX页)准凡例两段。第一段涉及底本,包括参考“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出版的原文版”。第二段涉及诸多编辑符号:“本卷中凡属笔记性质的著作(他人著作的摘要、摘录和爱尔兰问题札记)在版面上作了与其他文章不同的处理。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和他人著作中的话是用同样大小的字体排印的,为了表示区别,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开始时都用特殊符号┃│标出,最后都以反方向的同样符号│┃表示终止;此外,上下都用宽行距与他人著作中的话隔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划了着重线的文字一律排成黑体字,划了两条着重线的文字排成黑体字加重点。这些笔记中的方括号、圆括号和文字左侧的竖线、*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记中原有的,少数花括号中的话是俄文版编者或中文版译者加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说明第IX页。其中,着重号被吸收到“中二”《凡例》的“尖圈条”,但表现方式不同。
第46卷《说明》(第I-IV页,位于上册)准凡例两段,涉及编辑凡例的主要问题有底本及编辑符号、注释、索引等。索引说明即第二段:“本卷每册附有人名索引、马克思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下册附有全卷的名目索引。”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说明第IV页。第一段中的“马克思在引文中所加的词句或标点符号,放入尖括号< >内”、“编者加的标题和插入的文字用方括号[ ]标出”、“马克思手稿的原稿本编号和页码用方括号标出,括号中的罗马数字或拉丁字母表示稿本编号,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说明第IV页。等非常接近“中二”《凡例》的“尖圈条”、“方括条”、“笔缩条”。
第47卷首次在底本说明中明确提到MEGA及中文全称:“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七卷为依据,其中第I—V本笔记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第二部分第三卷第一册原文并参照俄译文翻译的。”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说明第V页。第48卷则参照MEGA。
(三)从“中一”自撰《说明》及其准凡例到“中二”专设《编辑说明》《凡例》
上述各卷《说明》《译后记》、底本段、“分工段”的变迁,可见“中一”对“俄二”从模仿到反思的过程。“中二”总结“中一”独立撰写每卷《说明》的经验,将尾段准凡例相关内容独立成文、形成了由与“二说”类似的总《编辑说明》和“俄二”所没有的每卷《凡例》等内容构成的“中凡”,则体现了这一反思的创新成果。具体而言,“中二”“中凡”对“中一”的吸收或超越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中二”总《编辑说明》模仿“中一”翻译的“俄二”“二说”,编译段、新版段与“二说”基本一致,底本段比“二说”相关内容更清楚,结构段、体例段有一定相似性但更清楚、更专门,且吸收了MEGA2的新成果。另外,“中二”总《编辑说明》没有采取“二说”花大篇幅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其次,“中二”将“中一”翻译刊印的《说明》、独立撰写的《说明》《译后记》等内容的吸收、发展,独立成每卷《凡例》,以下分条说明。一是时序条吸取了“二说”中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卷次和卷内的次序,是根据各篇写作时间或发表的日期排列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二版说明第VI页。这一时序原则。二是“星标条”吸取了第6卷《说明》准凡例(以下略去,只说卷次)及第9—13、15卷等的做法。三是“尖圈条”中的尖括号在第3卷首先提出,在第40、46—50卷加强,圈点则以不同于黑体字的方式吸取了第45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划了着重线的文字一律排成黑体字,划了两条着重线的文字排成黑体字加重点”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说明第IX页。的做法。四是“方括条”中的方括号在第3卷首先提出,在第40、45—50卷加强。五是原注没有直接涉及,但“二说”及“中一”第9—14、44、46卷等谈到的注释间接涉及。六是索引在“二说”即提到,第44卷提到“人地名索引”、第46卷提到“人名索引、马克思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全卷的名目索引”。此外,从体例上看,“中一”第1卷《目录》即有“人名索引”“期刊索引”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目录第II-III页。,内容位于卷末。以后各卷《目录》均有相关索引。七是“笔缩条”中的外文缩写在“中一”相关内容中不见提及,是“中二”的一个创新。笔记本编号及页码则在第46卷开始提起,并在第47—50卷加强。
再次,各种注释、“分工页”、《前言》首尾段等“中凡”分散内容亦延续、吸收 “中一”。总《编辑说明》、每卷《凡例》及“中凡”分散内容的形成,可梳理总结为以下《“中凡”内容、形成简表》。“俄二”等全集有待研究,在此不展开。

“中凡”内容、形成简表

《前言》相关首段 延续“中一”《说明》首段 借鉴“中一”《说明》并有所发展尾段 借鉴“中一”《说明》准凡例题注 “中二”延续“中一”题注类似 MEGA2的 Entstehung und Ueberlieferung题下注 “中二”延续“中一”题下注 类似MEGA2的Zeugenbeschreibung编者注 “中二”延续“中一”编者注异文、校正等有所表现注释相关分散内容译者注 “中二”延续“中一”译者注卷末注 “中二”延续“中一”卷末注编译页 “中二”借鉴“中一”“二说”相关内容及编译页 “中二”编译段单独成页、篇幅不及“中一”“分工页”借鉴“中一”《译后记》、底本段,将其“分工段”单独成页 “中二”创新致谢 “中二”无 “中一”有可能遗漏的内容相关
三、主要特点
根据上述对“中凡”基本内容和分散内容的分析,结合相关内容,可以总结出“中凡”的若干主要特点。
第一,独特的统分结合体系。“中二”《凡例》之体例,基本内容集中体现于全版《编辑说明》和每卷《凡例》,而其他相关编辑问题则体现在分散内容中。这也是笔者概括并提出“中凡”的主要根据之一。
第二,独特的各部分《凡例》。不同于“俄二”及MEGA2等,“中二”有一个独特的各部分《凡例》,即各部分诸卷逐渐形成或径直通用一个大致相同的《凡例》。大致内容,以第32卷七条为基准,第一部分《凡例》为其前六条、第二部分为全七条、第三部分为前五条(第一条根据部分特点有修改)。具体而言,第一部分从第10、12卷开始,各卷《凡例》完全相同。第二部分自第32卷以后各卷《凡例》基本相同。第三部分各卷《凡例》从一开始就完全相同。第四部分,观此发展,可以预料其部分《凡例》会从第一卷就开始通用。总《编辑说明》、各部分《凡例》、每卷《凡例》形成“中凡”基本内容从总体到部分到各卷的层次性,这在各主要全集版本中是罕见的。
第三,与时偕行,酌情调整。如前所述,根据编译实践,“中一”的《说明》、编译页等有较大调整,“中二”《凡例》也有所调整。“中二”调整既有部分内的,也有跨部分的,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增加。第一部分从第10、12卷增加“《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后就固定下来。第二部分第32卷增加了“《引文笔记》(1859年)”后《凡例》就基本固定下来。二是根据各部分特点的修改。例如,时序条在第一、二部分内容相同,但在第三部分则有调整。这是因为,书信卷的“文献”具体是“书信”,为编辑及读者方便起见均需加序号,而“变通处理”则不再需要。三是根据各部分特点的删除。例如,对第三部分书信而言,第一、二部分的“星标条”并不需要,所以删除。根据这样的编辑精神和先例,第四部分《凡例》增加、修改、删除等,皆有可能。
第四,篇幅较短。从第32卷《凡例》七条及有关变化来看,《凡例》篇幅较短,约400字、半页,约为MEGA每卷《编辑说明》①中译实例可见“文一”附录一。的十分之一,仍有增补之空间。
第五,基本内容没有、分散内容则有个性化到每一卷。MEGA2的《编辑说明》是个性化到每卷的,当一卷包含多个分卷时,每卷的《编辑说明》则列在第一分卷。“中凡”的基本内容个性化不足,未很好地个性化到每卷。这从各部分、每卷《凡例》总共七条、大致相同就可以明显看出。其中“尖圈条”和原注条提到的“马克思或恩格斯”有的卷次应酌情具体指明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凡例》“尖圈条”和原注条中的“马克思或恩格斯”以及“中二”每部分都存在的多卷《凡例》完全一样等情况,应该在以后编译工作中尽量酌情避免、做到个性化每一卷。
需要纠正“文一”“文二”的是,如前所述,每卷《前言》首尾段、相关注释、“分工页”等“中凡”的分散内容,则个性化到每一卷。
第六,中国特色。“中凡”的中国特色,除了前述独特之处外,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看,“中一”分散内容中的《说明》首段及准凡例、“中二”《前言》首尾段类似汉魏南北朝“附在序文中的凡例”,“中一”“中二”题注、题下注等相关注释则类似唐李善注《文选》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采取的“注文中发起的凡例”,而“中二”每卷《凡例》,则类似隋唐以来作为“作为辅文的凡例”①申非:《凡例源流初探》,《中国出版》,1994年第5期。,尤其是明清“大多作为专篇刊于卷首”②曹之:《古书凡例考略》,《编辑之友》,1997年第4期。的凡例。二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看,“中凡”体现了模仿、反思、突破、超越苏联模式的历史过程。“中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中的体现,其经验、教训都弥足珍贵。
苏东虽然剧变,但历史并未终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编译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二”的同时,也应追求编译水平的更上一层楼以及对MEGA编辑的更多研究、参与和贡献。对“中凡”的坚持、完善和研究,无疑是这一努力的诸多步伐之一。为此,在“文一”“文二”建议的基础上,谨再补充若干建议供参考。第一,发扬传统,在编译局内外协同创新的基础上,联合高校、机构相关学科推动设立经典著作编译专业、培养编译人才。第二,“中国的MEGA2研究者也应当组织起来, 成立相应的MEGA2研究机构或协会”③赵玉兰:《MEGA2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理论视野》,2018年第7期。。第三,加强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除非涉密,相关编译工作条例等文献应予公布④如国际马恩基金会在1993年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准则》[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而中文全集似没有公开发表这样专门而系统的编译文献。笔者于2017年底获基金会胡普曼秘书长授权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计划把该书翻译与中文全集学研究等结合起来。并接受公众反馈。与凡例直接相关的建议主要有:一是编纂《中国经典著作编译史》,系统描述中国经典著作编译的历史并反思经验、教训。二是批判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凡例传统,整理《中国古典编译概览》。三是推出《中国经典著作编译家列传》,既铭记他们的贡献,也增进各界沟通。四是推出《中国经典著作编译文献汇编》丛书⑤前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说明、索引(第40-50卷) 》等都属于此类丛书。,将所有编译工作规范文件加以整理、发表。五是推出《国外经典著作编译概览》⑥最近陆续出版的、由杨金海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等含有较多此类内容。,系统收集、整理、研究国外同行的基本情况,以资借鉴、参考、超越。这些工作,应充分考虑电子化、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广泛吸引社会、民间参与并及时听取公众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