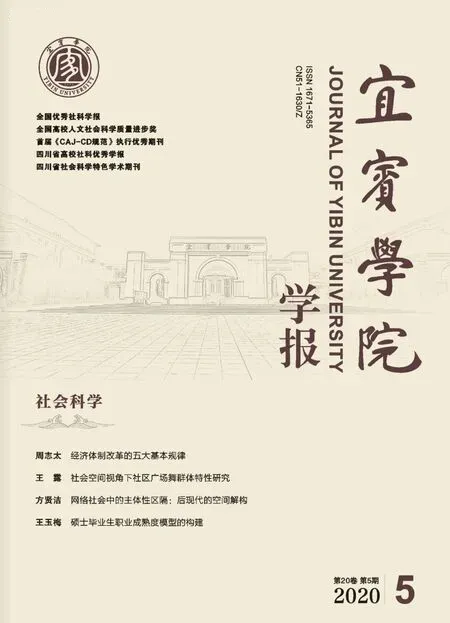社会空间视角下社区广场舞群体特性研究
2020-06-05王露
王 露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改革开放已有四十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性”社会已经受到了现代化强力的冲击,社会变得更加陌生化。广场舞群体通过释放天性、锻炼身体的群体活动与生人社会的现实相对抗,将作为公共空间的社区广场私人化为自己的社交活动空间,在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因空间权利的争夺导致了群体的“污名化”。不少学者聚焦于广场舞引发的空间冲突,孙高峰、王炳炎[1]认为广场舞给公共空间带来摩擦,引发了物理空间、道德空间和审美心理空间三重冲突。黄薇诗[2]则关注到广场舞扰民纠纷的背后是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碰撞;广场舞空间是广场舞群体在公共广场上重新构建出的一个小型熟人社会,更是具备诸多功能的社会空间。杨君[3]基于个体化的视角对广场舞进行分析,认为广场舞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它既能实现身体展示与审美追求,还能帮助个体找寻空间位置并在主体互动中增加群体归属感。目前学术界针对广场舞现象的研究着重于社会治理层面,如何在广场舞空间治理中缓解日益尖锐的空间冲突,改善广场舞群体的负面形象已经成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广场舞群体的空间实践
广场舞群体是指多在公共广场之中聚集、进行集体舞蹈的一群人,他们多以中老年妇女为主,通过多样化的集体舞蹈进行自我表达。他们在公共广场上进行日常生活实践,建构出群体所有的广场舞空间,并且在空间碰撞与互动中调适社会关系、生产新的空间意义,在现代社会中重塑熟人空间尺度。
(一)广场舞群体的空间生产
广场舞群体的空间实践以一种集体性娱乐的方式进行空间再生产,为社区居民再叙“熟人社会”的生产生活逻辑。人们在单位空间离场后进入到工具理性化的“陌生人”社会,正如齐美尔曾言,一个特定的空间往往是一个具有边界确定性的地域范围,包含着在此范围内生活的人们人际关系的亲近和空间距离的统一,陌生人从这个地域空间之外介入[4],而广场舞空间就起到了调节人际关系、缩短人们交往的空间距离的作用。它凸显了公共空间的平等进入性,以低标准的空间准入门槛将众多陌生人容纳进来,在共同占用与利用空间的过程中消减他们的异质性,他们的社会关系经由集体性活动从“陌生”变为“熟悉”,打造出现代城市中的新型人际交往范式。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空间是社会性的,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生产[5]。广场舞群体不仅生产与再生产了群体凝聚力、地方认同感和亲密社会关系,个体也作为再生产单位重新嵌入公共空间中寻求精神慰藉与身份表达。他们的集体欢腾萌生了共同的情感体验与归属认同,居民从私人生活中进行暂时性抽离,投身于广场再生产出现代“熟人社会”。
广场舞以其互动形式的在场性、即时性实现了区域化,达成了空间的扩展与延伸。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包含着三重过程:空间实践、空间的表现和表现的空间。空间生产了社会关系,带来日常生活的变化。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凝聚[6]41-42,广场舞空间中的互动实践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延续传统社会关系并拓宽新人脉关系,这种“圈子”文化可以积累更多社会资本;通过广场舞群体约定俗成的空间符号与秩序,群体成员构想出“概念的空间”控制着每个人的知识与意识形态,空间将无形的规则具象化到人们的身体活动上,个体共享着广场舞文化并受到规则的约束与支配;表现的空间亦是社会草根群体进行空间争夺的场所[7],广场舞空间作为服从于符号化的舞步和指令的表现空间,是广场舞群体利用广场舞这种“草根文化”传递自身需求与声音的一个文化世界、日常生活空间,他们将草根性带进公共空间来寻求群体性的身份认同。广场舞空间形塑着广场舞群体以及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进入广场舞空间后的陌生人主动参与空间内的实践活动并感知一系列符号象征与价值意义,在与他者的交流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
(二)广场舞群体的空间形塑
已有文献皆把广场舞当成一种时兴的社会现象,从女性主义、社会转型、体育运动、伦理健康、公共空间等视角对这种全民性娱乐活动加以分析。广场舞群体的空间性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从广场舞带来的强身健体作用到人际交往再到空间冲突,广场舞空间的研究也逐渐从身体空间转向社会空间最终落脚于空间治理。由于人群的集聚性与活动的集体性,广场舞群体形塑出独特的广场舞空间。老年人是广场舞的主力军,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了传统家庭结构的断裂,广场舞空间以一种新的空间维度让老人们“老有所依”“抱团取暖”;妇女则是广场舞群体的领头羊,她们可以在这种不同于家务劳动的身体实践中更充分的展演自己,重建主体身份与个体生命价值的生活场域[8],以新的社会角色定位对广场舞空间进行主体性建构,使其成为传达诉求与身份认同的社会空间。
中国自从进入了“去集体化”的时代后,集体主义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远离,难以接受“生人社会”现实的老人伴随着对集体主义下“熟人社会”的回忆,试图通过广场舞这种新的集体活动来复制曾经属于他们的集体时代,用新生的社会关系将公共空间重构为新的“熟人空间”,以此来减轻对当今匿名社会的无所适从感。社会变迁改变了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传统联合家庭的分解让老年人大多隐于家庭空间中,他们可以以广场舞产生新的情感依恋和新的社会关系附着的表象空间;广场舞空间使脱离家庭空间后的广场舞群体重温社群生活,开始新的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既弥补了单位空间离场后留下社交空间空缺,也为外来居民融入城市建构了地方认同空间。广场舞群体表现出了在城市原子化生活方式下对再集体生活方式的向往[9],以集体主义情怀与传统社交倾向在公共空间中生产出新的空间实践。他们将公共空间作为舞台化的场域进行了新的使用与体验,相较于空间外的陌生人而言,广场舞群体犹如演员一般将作为社会剧场中自我展现 “前台”的广场形塑为“表演空间”。广场舞群体将众多身体空间整合为广场舞空间,通过身体运动把自己的位置关系投射延伸到身体之外的广场上,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他们通过身体的空间性实现了对广场空间的占有,这种位置关系不会带来“情感上的不协调以及生存意义的缺失”[10],反而在“生人社会”里能够让他们获得一种本体性安全。
二、 广场舞空间的“公私”碰撞
广场舞空间既是休闲空间也是凝聚群体成员的情感共同体,但“地盘之争”等空间冲突和社会矛盾让广场舞群体被“妖魔化”。广场空间的“公共性”与空间占有活动的“私人化”相对立,给公共生活带来了一定的道德恐慌,更有非广场舞群体的误解与反对加深了广场舞群体的“污名化”程度。
(一)空间紧张引发空间冲突
不少社区认为广场舞活动侵入了居住空间,为了保证社区环境从而对广场街道等公共空间进行挤压,仅留给广场舞群体碎片化的局部空间;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存在着供需不平衡,公共空间的稀缺性带来的空间用地紧张让草根阶层开始了空间争夺。在对H市FX社区六位老人的随机访谈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住进回迁小区后感受到了空间的逼仄感,他们更喜欢到宽敞的社区广场上活动,广场舞是他们最喜爱的娱乐休闲活动之一,但是社区因为居民投诉他们扰民而禁止了广场舞活动,他们多次与上面交涉无果后不得不转战阵地。社区也曾因广场舞带来的噪音与交通问题爆发过肢体性冲突。年轻一代更多沉溺于手机网络所带来的流动空间,由于时空压缩减少了空间障碍与时间花费,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使空间流动起来,人们可以共享不同时空内的行为实践,他们对广场等公共空间的需求自然没有老年人那么迫切;而老年人多不善于网络媒体的使用,在他们所代表的熟人文化逝去后其自身价值困境急需一个突破口,与其“压缩”在家庭空间中,他们更愿意“压缩”在广场上近距离化与他人的交往,以此来消弭他们在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断裂后的孤独感。
社会空间出现了“消费转向”,空间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消费,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成为商业用地,现代化消费逻辑充斥于公共空间中,导致进一步的公共空间资源配置不平衡。消费性公共空间以经济地位作为准入门槛,衡量进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不仅将大量草根阶层“挤压”排斥出去,也挫伤该群体的公共意识,催生了他们对公共空间消费话语的反抗与抵制。而商业用地的大量增加、不合理的社区建设规划和不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让广场舞群体无处可去,碎片化的公共空间已经难以满足群体需求。空间紧张导致空间冲突的加深:一方面私人意识上升的广场舞群体模糊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开始对公共空间进行私人化占有;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有限性对上居民需求的无限性,多方利益主体进行博弈争夺后激化了“空间冲突”。在空间紧张的背后,是社会转型带来的代际断裂、文化断裂和价值观的断裂。独居的空间增加了空巢老人的空间焦虑感,而非广场舞群体只看到了噪音扰民等负面影响,年轻一代在个体本位取向下更对广场舞这种活动形式持鄙夷与嘲笑的态度,不少人认为广场舞这种生活实践与年轻化的娱乐活动相对立;广场舞群体与非广场舞群体的对立涉及到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升级到具体空间中后不可避免的爆发了“空间冲突”。
(二)广场舞群体的“污名化”
网络的发达吸引更多人们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互动,弱化了现实情境下人际交往的情感交流功能,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广场舞群体的对立面。机械团结社会中的集体意识逐渐湮没于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工具理性下,个体主义对集体主义式的广场舞活动表示难以认同和接受。新的一代崛起意味着年老一代落幕成为了相当一部分人心中的共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期望是回归家庭,年轻人能接受老人退休后在家庭空间中不事生产,却对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空间再生产活动抱有微词。人们忽视了广场舞老年群体自我价值与主体意识的显现,认为他们与时尚化、年轻化的广场不相匹配,妨碍了广场公共价值的发挥。在快速的城市化中,广场等公共空间上的地理集中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循环使用,哈维在其空间经济学中认为地理形式上的集中产生剩余价值,城市广场作为环境景观以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为目的促进资本积累,加速空间经济的产生;而广场舞带来的老年群体的集中并不能为空间经济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在空间中的占用也妨碍了其他人口的流动,由于群体中消费力不强的老年人多,公共广场附带的资本消费作用也难以体现出来,导致广场舞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广场的利益创收。
部分公共意识缺乏的人忽视了对他人公共权益的维护,群体占有活动将广场上的公共空间“私人化”为自身社交平台,给他人的正常娱乐休闲带来了不便。2017年洛阳公园篮球场广场舞大爷围殴篮球少年的新闻引发网友激烈讨论,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广场舞群体的占地行为进行挞伐;成都居民每5分钟报警一次、北京市民鸣猎枪放藏獒驱赶跳舞者、温州小区住户买来高音炮与广场舞音响对抗等行为皆显示了广场舞对部分居民来说已经成为了“扰民舞”。如今人们愈加重视自己的私人空间体验感,对任何入侵到私人领域内的行为都表现出极大的抗议,公共场所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居民反对高分贝的广场舞音乐蔓延进家庭私人空间中。带有引导性的报道放大了广场舞的负面影响,广场舞群体背上了“扰民”的污名,在2017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中提到了有关广场舞产生的噪音扰民、抢地冲突等问题更加加深了人们对广场舞的刻板印象。被“污名化”的广场舞处在不被人理解的尴尬立场上,却也因为自身问题让非广场舞群体更加反感。
三、 广场舞群体与社会治理
广场舞群体的“再熟人化”空间实践重塑了现代社会城市空间价值意义,群体的多种积极功能在个人、社会、社区三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空间伦理与公共生活规范的缺失仍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治理来进行引导和培育。
(一)广场舞群体承载的正向功能
被“污名化”的广场舞群体背后所具有的正向功能不容忽视。社交功能既是该群体的首要功能,也是促使群体发展延续的内在驱动力。广场舞空间作为社区中的主要社交中心以信息的高流动性和人群的亲密性实现了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的脱域化联结,正式与非正式信息的传播与获取都在这个空间中进行。人们通过“在场”于广场舞空间实现了自身的社会化再生产,融入广场舞大军也就嵌入于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休闲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作为休闲文化的广场舞如同现代忙碌生活中的“减压器”,缓解了过快的节奏感给人们带来的生活压力;而这种休闲文化是人们通过长久以来的共同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凝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也具有情感功能。该群体活动能够满足人们爱与归属感的需要,在工具交往中为情感性行为开辟一条道路,将广场舞群体凝聚成情感共同体。有学者认为“社区情感共同体”是指社区空间内部人与人之间以情感、信任为基础相互联结形成的社会群体,个体对于社区空间具有主体间性、积极正向的集体记忆和共享情感[11]。人们的社会行动使社会时空成为社会的意义与象征,广场舞群体也处于一个有意义的直接经验世界内,群体成员之间是一种面对面的“我们关系”(We-relationship),具有直接性、熟悉和内缩的时空特性[6]87-88。广场舞群体共享着这个时空,基于情感的沟通与交往与他人建立直接的情感联系,完成“去陌生化”的个体开始在情感上亲密熟悉起来。广场舞不仅满足了处于情感孤独状态中的老年人的休闲与社交需求,还以一种“再集体空间”容纳了他们的情感宣泄。
在社会层面上,广场舞群体可以发挥社会“安全阀”作用。现代社会中高强度的工作与压抑的生活环境滋生了人们心中的敌对情绪,在社会秩序的规范约束下敌对情绪引起的冲突不容易爆发却容易累积,广场舞空间以其开放性、自由性等空间特性成为了一个微型的社会安全机制,作为宣泄个人不满情绪的正当渠道引导人们进行合理的情绪释放。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向全体公民开放的,是人们可以自由讨论公共事务进行政治参与、发表公共意见的一种场所或空间。广场舞空间也承载着政治功能。国家权力规训未曾略过广场舞空间,不断增加的国家财政投入与不断完善的公共空间制度体系在逐步解决广场舞社会问题。广场舞空间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空间,它将公民政治生活与社区居民生活政治相融合,赋予了空间以政治文化表征,并通过纪律权力影响空间互动方式,将国家权力渗透进公民日常生活,在广场舞空间中传递国家声音与政治话语,对焦群众文娱活动塑造公共文化空间。广场舞群体作为社区文体组织,在整个社区社会空间中也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形成了“政府(社区)——广场舞群体——居民”的社会空间良性生产机制(见图 1)。

图1 广场舞空间的良性生产机制
该机制整合社区中可利用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建设力量,有助于打破疏离陌生的人际壁垒,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它既吸引了社区居民参与,满足了居民活动需要,又能整合社区休闲资源凸显社区的文化个性;而且它可依托其空间特性成为连接政府与居民的桥梁,实现公共信息的双向传播并加深居民的认可度,促进社会和谐,抑制个体化趋势。广场舞作为一种社区草根文化能够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强化群体的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展现公共空间的别样社会文化价值。
(二)空间治理“内+外”模式
1.秩序化的广场舞队
广场舞队不同于一般由成员主动组织的广场舞群体,通常是社区组建的团队。由于外部规则制度的明确以及群体成员处于同一个话语体系内,成员熟悉亲密更有凝聚力,参与感与责任感更强。例行的社区表演与群体活动,不仅动员了广场舞群体,也调动了其他居民的积极性,既强化了空间内的社会关系,也将集体本位价值观念辐射到其他居民身上,促进了社区内的社会交往,增加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秩序化的广场舞队可以使人们改变对广场舞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可使情感的共享拓展到整个社区加强社区整合。广场舞队也是权力生产之重要场所,权力的产生与存续主要表现为一种垂直的控制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施加影响与接受影响的关系[12]。由社区组建的广场舞队受到社区的管理与控制,社区决定其组合方式与集体行为,其中的行为主体都会接受社区为其制定的制度性规定,这种支配权随着时空的转移会内化为个人内心的自我监管,使广场舞群体更加规范化、秩序化。一个有着良好秩序与内部整合的广场舞队,更能将群体社会实践与主观情感认同连接起来,建立成员间更亲密的社会关系,也“生产”出 “再”熟人社会,对于增加社区居民情感交往、带来积极的空间情感体验、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性方面也有很大助益。
汉娜·阿伦特强调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表现为公共生活的关联[13],秩序化的广场舞队代表着社区形象、体现着社区文化,它的活动联系广场舞群体与非广场舞群体,即可让前者体现自身价值,也让后者发现广场舞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消解其他居民对广场舞群体的敌视态度,获得他人的认同与尊重。当广场舞队代表社区进行演出时,社区居民会意识到广场舞队对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态度会更加包容。秩序化的广场舞队脱离了无序性与私人性,凸显公共性使得空间权利明确化,群体成员公共意识提高的同时也减少了与非参与群体的空间冲突,有助于社区的公共管治与文化建设。
2.规训化的广场舞空间
福柯从其“权力—知识—身体”视角出发,认为通过空间的分配与区隔可以形塑人们的社会行动与思想观念,以及建立一套符合权力逻辑的社会秩序[14]。权力塑造空间,从而确保社会秩序平稳运行。社区(政府)无需构建一个新的“全景畅视监狱”,广场舞空间本就是公开、开放的。秩序化的广场舞队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则,使公共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明确,但是非社区组建的、大量自发组织的广场舞团队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的边界,他们的无序性是导致空间冲突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广场舞群体作为空间使用者尚缺乏对空间价值的认同以及合理的空间伦理与规训。广场舞空间的规训需要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眼睛”,需要行为主体感受到纪律权力的束缚,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要应该依靠外在行政权力的法治与空间内群体的自治。政府和社区应该考虑到广场舞参与者以及非参与者对活动空间的实际需求,对社区公共活动场所进行合理的地理规划,既需要制定实施相应的规章措施支持合理有序的空间活动,也对非理性的扰民、抢地的广场舞行为进行惩罚。国家对于公共空间的法律规定尚需进一步的完善,社区也需要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优化社区公共空间结构,发扬积极的休闲文化;积极开发并充分利用社区闲置空间,向社区居民开放;鼓励一些商用空间在非工作时段向社会开放,提高空间使用率;政府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将公共空间进行功能划分,为广场舞群体营造便捷且不扰民的广场舞空间。空间内部规训则依靠群体成员公共意识的提高,不少人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在城市化浪潮中迷失“自我”,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使人们进入了新的社会化与价值观形塑阶段。要引导正确的空间价值观,构建和谐融洽的话语体系,从群体中具有“奇理斯马(charisma)”式魅力的成员着手,引领健康有序的公共舆论,稳固良好的社会关系,提升群体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提升他们的责任心与公共意识,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广场舞群体与其他居民的冲突。法治为主,自治为辅,外有强有力的法律监督体系的控制,抑制群体的道德失范与越轨行为,向内提升空间内行为主体的自律与自控能力,把外在的规训内化于心、监管自身,才能在不过度放纵自我的前提下合理休闲。
结语
长久的“污名化”使得人们并未注意到广场舞群体的社会空间意义,负面性空间冲突掩盖了广场舞空间的正向功能。在“社会—空间”视角下,广场舞群体通过他们具有情感性、主体间性的社会交往实践,促成了群体日益亲密的关系,“生产”出一个具有共同情感与集体记忆的社会空间,而广场舞空间也“再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广场舞群体的空间特性彰显着积极的社会功能,其生产出了“熟人社会”般的广场舞空间,缩短居民社交距离并延续传统社交逻辑,在整合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的空间治理合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去污名化”需要在有效的社会治理下构建出有秩序、有规则又不失活力的公共空间,建立起该空间的内外规训模式,规范化、秩序化群体行为,有利于发挥好该群体在社区中的社会纽带作用,促进社区的治理与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