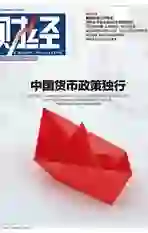最优秀的人,并不必然强于众生
2020-06-01沈联涛

沈联涛
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旧有的模式和价值观已失去效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称“美国第一”之时,何曾想到美国会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感染确诊(超过120万)和死亡人数(超过7万)全球居首。也几乎无人能想象到,拥有最优秀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大学的最强大的经济体,短短几个月内就从近乎完全就业堕入“ 90%的经济”,逾3000万人失业。
美国式资本主义能顺畅运作,建基于所有人可以不受阻碍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最优秀、最有竞争力的人可借此途径攀升以至登顶,进最好的大学学习,成为第一流人才。竞争自由是精英治理、技术官僚领导下的社会的要义。只要治国者是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些人,更幸福、更自由的世界便来日可期。但是历史告诉人们,外表光鲜亮丽的那些人,可能并不比我们其他人强到哪里去。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于1958年出版《精英统治的崛起:1870年-2033年》,发明了“精英统治”一词。他预见,精英阶层的崛起将把社会分为精英和非精英的民粹主义这两个阵营,而后者会逐渐意识到,精英治国并不以社会公益为目标,而是旨在护持他们自己狭隘的利益。
此种滥权之舉的最佳例证便是公司治理中的股东价值模式,依照这套说辞,则公司应向管理层支付高额费用,以保证股东收益最大化。表现最佳的管理人才将被授予股票期权,以使其与股东们的利益保持一致。这种思路认为,高盈利和高效率的公司将不仅为股东创造价值,也将有益于社会。但在现实中,许多经理人将宝贵的公司现金用于股票回购,以支撑其股票期权的价值,同时变卖有价值的资产以维持季度收益,一旦盈利前景不妙便解雇员工。
当那些最优秀的人才视自己的利益优先时,他们就不再是为多数人效力。
地缘政治战略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在其新著《平静之前的风暴》(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中正确地指出,自1980年以来,新技术已让美国社会判然两分,一方是技术专家,这些人都拥有最优秀大学的教育经历;另一方则是剩余的大众,他们大多在旧式产业经济中谋生,所在行业的市场份额和价值都在缩减。
如今,全球疫情暴露出残酷的断裂带,一边是富到流油的“最优秀”技术官僚阶层,另一边则是余下的大多数生计岌岌可危者。应对疫情的社交封锁之举,将经济也分成了不受此影响的线上部分,和不堪一击的线下部分。后者既是主流,也容纳了最大多数劳动力。新冠病毒疫情结束后,大型科技公司将蓬勃发展,而依赖高密度人群收益的工业时代企业(例如大型商场、游轮、航空公司和旅游业)将遭受损失。不幸的是,许多小企业和工人对在线技术仍是门外汉。
这就产生了一个社会公平的根本问题。当银行的盈利能力已经不那么依赖于公众存款,而更多仰赖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时,我们还应否付高昂薪水给金融工程师?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者们,在疫情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为何收入却远不如软件技术人员?市场无法为不同工作的社会价值定价。如果社会主义者要求执行最低工资(当然是公平的),那么可否考虑对不具社会价值的工种设置工资上限?
疫情结束后的最大赢家将是大国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这是因为政府将依靠技术来应对未来的四项主要支出。第一项紧迫支出用于保障封城期间,公司能够正常运营和劳动力就业稳定;第二个是进行必要的注资和投入,让某些艰难生存下来的企业在疫情结束后转型为更具盈利能力;第三项支出用于弥补那些难以为继的企业的损失;第四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为濒临破产企业的员工提供教育、培训,赋予其新技能,以便在疫情结束后重新就业。但运营最佳的科技企业,可能并不需要这么多新劳动力。
所有这些表明,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将消耗非常庞大的政府支出,产生的赤字将远远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赤字(GDP的5%-10%)。除非奇迹般地开发出疫苗,否则企业何时可走向复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推进卫生防疫和社交隔离方面表现如何。欲适应环境以求生存,就意味着我们的重建工作要预留空间,要有强于必需的实力,以备未来遭受冲击时有所余裕。既然有所余裕也就不能强求效率。在前行的路上,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疫情大流行告诉我们,最优秀的那些人不可不利于公益,最优秀的必须看顾余下的大多数人。这呼唤合作、同理心和以人为本。为了证明“美国第一”的政策正确无误,成千上万的人将付出生命代价,他们的不幸将得到我们的同情。
如果这就是最好的结果,那我完全不接受这种做法。
(翻译:臧博;编辑:袁满)